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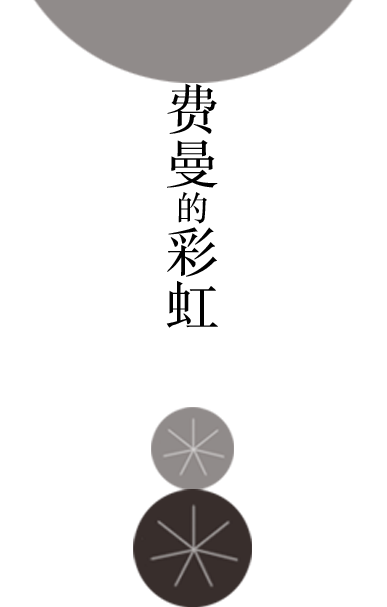
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加利福尼亚林荫大道(California Boulevard)上,橄榄树成排的加州理工校园一幢灰色的水泥建筑里,一位瘦削的长发男子走进了他简朴的办公室。一些年纪还不及这位教授三分之一的学生停下脚步,在走廊上望着他。即使他今天不来上班,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只是,任何事都无法阻止他前来,尤其是手术,他再也不允许手术的影响去破坏日常生活。
户外,明亮的阳光洒在棕榈树上,但是已不再如夏日那般酷热。群山拔地而起,山上的棕色渐退,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更适宜植被生长的冬季就要来临
 。这位教授不知道自己还能再亲眼见证多少次季节的交替变化;他深知自己患上了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他热爱生命,但同样尊重自然法则,而不是盲目相信奇迹。1978年夏天,当他首次发现自己身患罕见癌症时,就查阅了文献资料。根据记录,这种病的五年生存率一般不到10%。实际上,没有人能存活十年。而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第四年。
。这位教授不知道自己还能再亲眼见证多少次季节的交替变化;他深知自己患上了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他热爱生命,但同样尊重自然法则,而不是盲目相信奇迹。1978年夏天,当他首次发现自己身患罕见癌症时,就查阅了文献资料。根据记录,这种病的五年生存率一般不到10%。实际上,没有人能存活十年。而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第四年。
大约四十年前,在他跟这些学生差不多年纪时,就给著名期刊《物理评论》(
Physical Review
)寄过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一些新奇的小图
 ,它们虽不及物理学所使用的标准数学语言正式,却带来了思考量子力学的全新方式,当时鲜少有人相信他的方法,但是他暗在心中揣度,如果有一天,期刊上登载的全是他的图,那该多有意思啊。事实证明,这些图所表示的方法不仅准确无误、颇为实用,而且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1981年底,《物理评论》中随处可见他的小图。它们几乎可以媲美那些名垂青史的经典图例。他完全可以与那些知名人物并驾齐驱,至少在科学界是这样的。
,它们虽不及物理学所使用的标准数学语言正式,却带来了思考量子力学的全新方式,当时鲜少有人相信他的方法,但是他暗在心中揣度,如果有一天,期刊上登载的全是他的图,那该多有意思啊。事实证明,这些图所表示的方法不仅准确无误、颇为实用,而且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1981年底,《物理评论》中随处可见他的小图。它们几乎可以媲美那些名垂青史的经典图例。他完全可以与那些知名人物并驾齐驱,至少在科学界是这样的。
过去几年里,教授一直在研究一个新问题。他学生时代即已提出的方法在应用于量子电动力学(Quantum Electrodynamics)的理论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理论研究的是电磁力控制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的行为。这些电子赋予原子化学性质和光谱特性(它们发射和吸收一系列的光)。因此,研究这些特殊电子及其行为的物理学分支就被称为原子物理学(Atomic Physics)。自从这位教授的学生时代以来,物理学家早已在核物理学(Nuclear Physics)这一新领域中取得了伟大的进展。核物理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原子的电子结构,还涉及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之间可能产生的更加剧烈的相互作用。尽管质子同样受到控制原子中电子行为电磁力的作用,但这些相互作用主要由一种新的力来控制,并且它的强度远远超过电磁力。它有一个贴切的名字叫作“强核力”(Strong Force)。
为了描述这种强核力,人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这一理论与量子电动力学在数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的命名也反映出了这一点—量子色动力学(Quantum Chromodynamics,尽管名字中带有“色”字,但是它与我们所认知的颜色无关)。原则上,量子色动力学精确且定量地描述了质子、中子和相关粒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如何相互结合,或者在碰撞中如何表现。但是,我们应该怎样从理论中提炼出对这些过程的描述呢?教授的方法大体上适用于这一新理论,只不过存在一些实际困难。虽然量子色动力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教授本人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如何利用他的图或者其他方法从理论中获得精确的数值预测。理论学者甚至无法计算出质子的质量—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物理量,很早以前就被实验人员精确测量出来过。
教授想,在仅剩的几个月或者几年光阴里,或许他还将继续与量子色动力学,这一当时公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打交道。为了积蓄研究所需要的精力和意志,他告诉自己,多年来无法成功攻克这一难题的人,都缺乏他所具备的某些特质。至于这些特质是什么,理查德·费曼本人也不太确定:可能是一种古怪的生活态度。不管这些特质是什么,它们都功不可没—他曾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不过,如果考虑到他整个职业生涯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突破,那么或许再颁给他两三次奖也不为过。
与此同时,1980年,在伯克利以北几百千米的地方,一个年轻人发表了几篇论文,用自己的新方法解决了原子物理学中一些古老的谜团。他的方法为一些难题提供了思路,但是依旧存在一个问题。他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无穷多个维度的空间。在这个世界里,不仅有上/下、左/右和前/后,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方向。研究这样的宇宙,对我们生存的三维空间真的有用吗?是否可以将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研究,比如更加超前的核物理领域?事实证明,这一方法的前景不可限量,这位年轻人还因此获得了加州理工的初级教职,而且和费曼在同一层办公。
在收到这份工作邀约的当晚,我回想起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我曾经躺在床上,想象第二天初中开学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体育课—课后要在其他男孩面前洗澡。其实我真正惧怕的是别人的嘲笑。到了加州理工,可能我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在帕萨迪纳,没有指导教授,没有辅导教员,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困难问题。对我来说,无法提出卓越见解的物理学家和“活死人”差不多。在加州理工这样的地方,他同样会遭到排挤,并且很快就会下岗。
那么我到底有没有卓越的见解呢?还是我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呢?于是,我便去找同层办公室里那位瘦骨嶙峋、即将不久于人世的长发教授聊天。他所告诉我的,正是本书所要传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