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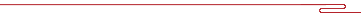
票拟是前明的一项政治制度。明朝由内阁大学士代替宰相,处理朝政。奏折均由大学士先行拆阅,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裁夺,这就叫票拟。清朝皇帝大权独揽,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将内阁大学士虚化为一个荣衔。臣子章奏由皇帝亲阅,做出决定后再交军机拟旨,所谓军机中枢,仅是一个上呈下达的跑腿班。广招上书后条陈泛滥,皇帝无论如何看不及,不得已新设军机四卿,代阅代批。这从形式上讲,的确有点像“票拟”,然小军机怎能等同于大学士!
慈禧初时隐忍不言,今日为何敲山震虎?
光绪小心翼翼:“儿子交片谕旨,即着总理衙门议奏。”
慈禧面孔一板:“要皇帝亲来纠正,章京所做何事?你们看看,都是怎么应付的。七月二十二日,军机处给我的奏片称:本日户部奏代递主事宁述俞折一件、王凤文呈二件、彭谷孙呈一件、陶福履呈二件、宗人府代奏主事陈懋鼎折一件,现在酌拟办法,拟明日再呈慈览。这就是说,本日有七件未能阅签。到了二十三,恰好没有别的上书,四章京赶办昨日遗留,共有十一件,有四件上书昨日漏报了!就说他们是生手,我不苛责小臣,可是老这样,就没法原谅了。凭什么呀,放着好些熬白胡子补不上缺的,偏偏便宜他们?”
这话指东打西,闹得人心发毛。世铎这个军机处老大,伸头出来挨这一刀:“奴才疏于拘管,失于检点,请皇太后、皇上治罪。”
慈禧很干脆:“不是你。”裕禄连忙接上:“是奴才有罪,奴才奉派收呈条陈,没有尽到职分,奴才该死。”慈禧戗他道:“我倒说你活该呢,你能不能活泛一点,叫老章京教教新章京,或忙不过来时帮一把?我说这只是比喻,意思是当差不能死板,非要扳倒树捉老鸹,结果把事耽误了。总之,上书人的身份虽然低,谈论的事情并不小。比如刑部主事洪汝冲,在条陈中提出三大策,第一便是迁都,他要迁都荆襄;第二则要借才,借日本旧相伊藤来游之机,求皇上予以重用,叫他来摆治中国;最后轮到联邦,不用说是联合日本,你都把国家交到伊藤手中了,你想自主,也做不到。听听听听,这都是什么馊主意,心肝肺是怎么长的,能把计想得这么歪!这就是变法么?与其这么糟,不如变回去,也叫大家安然些。”
“变回去”三个字,出其不意地冒了出来,使得全场一惊。话是由上书引起的,光绪便尽量就事论事:“军机处要谨遵太后圣训,监督章京,勤谨当差。对所上条陈审慎处理,虽说言者无罪,对那过于出格的,有司也当加以限制。”
太后既已发话,刚毅岂肯放过机会:“上书不乏奇谈怪论,也有仗义执言者。户部主事苗润土,便说变法有十忽三误八可议,把祖宗之法变糟了。”听到刚毅附和,慈禧嘴唇一抿,显然有所不满。几位军机同僚暗忖,这就叫过犹不及。太后给热昏的上书泼冷水,刚毅这一戗,把太后和皇上推到面对面,就没有回旋余地了。王文韶是户部尚书,世铎示意他来打圆场。王文韶犹豫一下道:“苗润土跟我说过,他立意在于稳当求变,所谓可议,是在事前集议周详,以免招人议论。”
慈禧语带讥讽:“话说周全了,免得有人插嘴。我不是要过问政务,只想交代你们,当今庶务繁多,山一般的重量压在皇帝肩上,你们要尽量分担。不要事不关己,争着缩头——”刚毅贸然叫了一声:“太后,国子监助教曾廉——”慈禧瞥了他一眼:“国子监?你是说姓崔的助教吧,他进呈算学书和水道图,签语请交总理衙门。这处置还算妥,没让皇太后和皇上学算学。皇上年轻学得动,我可怎么办?好了,记着我的话,你们下去吧。”
军机大臣们领命退出,刚毅心里还在嘀咕,怎么那么巧,就有个姓崔的混了姓曾的?或许老人家避而不答,另有深意?看见裕禄耷拉着脑袋,落在后面,刚毅站住等他走近,问:“你见到曾廉的上书么?”裕禄仍然蒙着:“什么曾廉?”刚毅道:“国子监助教,湖南举人。刚才我应该说举人。”裕禄莫名其妙:“举人什么?”
刚毅啐道:“好了,我把你个揣着明白当糊涂的!你把曾廉上书弄哪里了?”裕禄眨着眼睛:“曾廉上书?不是混在堆里,就是捡在篮里,你查查《随手档》不就得了。”《随手档》是军机处处置奏件的记录。
刚毅被他提醒,回到军机值房,便从领班章京处要来《随手档》。找到七月二十七日这一栏,他一字一句仔细念:“都察院折代递条陈由:一、笔帖式联治,一、广西试用知县章国珍,一、候选州同谢祖元,一、浙江举人何寿章,一、陕西举人张先,一、湖南举人曾廉……”
曾廉之后还有八件上呈品,之所以称“品”,因为其中有三份图样,还有一杆气枪!找到了曾廉上书的下落,刚毅松一口气。不料接看二十八日记录,军机处给慈禧的奏片称:“又二十七日,都察院代递谢祖元、郑重、胡元泰、张先、何寿章、诚勤、联治、宋汝淮条陈,均俟筹议奏明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里便没有曾廉其名,不知被何人毁尸灭迹了!
刚毅拉来裕禄,叫他对比两条看。裕禄满是看不懂的样子,刚毅恨得咬牙:“是哪个抽出几件,莫非是你?”裕禄道:“我抽出来做何用,好吃还是好喝?这不是说清了么?待办理后再陆续恭呈。”刚毅无奈地想,皇上选派裕禄,正是因他爱和稀泥。那么太后为何同意?她想把裕禄当作长线,去钓一条大鱼?刚毅已经猜出,皇上把曾廉上书压了下来。这没什么稀奇,以前于荫霖弹劾翁同龢,潘庆澜揭发保国会,他都没把奏片进呈太后。既没当面揭破,那就将错就错,让皇上继续作吧,等到作不下去,会有人算总账的。
为了这件条陈,曾廉使出搏牛气力,只是给康有为挠了痒痒,这让他又惊又恼。不过他没有发慌,文悌和黄桂鋆等攻康前辈,给他出主意说,告不成天状,就去告地状。曾廉请国子监学生帮忙,将他的条陈抄写上百份,在衙门和官宅间广为散发。这一手很厉害,康有为的罪状,腾播于人口,流传于民间。
皇帝开恩不杀,大家愿意代行天讨,把康有为放在口间杀一杀。士林的敌意长出了牙齿,康有为似也感受到疼痛,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少一套护身铠甲。他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别人改变了招数,他不得不跟着变。可他手无寸铁,如何动得起来?
几天来苦苦思索,总在转一个念头,这是与谭嗣同谈话时冒出的。这想法他多次推翻,又一次次油然升起,终于觉得应该一试。他又去烦请徐老先生,徐致靖便叫儿子徐仁镜找来王照,用老年伯的口气跟他说话。王照由六品主事,骤升为四品京堂,他承受的皇恩比徐致靖还大。而今新政受阻,皇上独立无援,缺乏左辅右弼,尤其需要领兵大将出来拥护。环视京畿,手握重兵而又身负重望者,首推驻扎芦台的聂功亭军门
 。恰好你跟他渊源甚深,这是天意要你建功啊,不知小航意下如何?
。恰好你跟他渊源甚深,这是天意要你建功啊,不知小航意下如何?
这段说辞,王照越听越慌张,惴惴地探询老年伯的意思。徐致靖含糊其词,要王照回一趟老家,探探聂军门的意思。王照按捺不住:“什么意思?恕小侄无礼,年伯此说甚悚听闻。以往耳提面命,小侄无不听从,因为那全是君臣大义、忠孝廉耻。蓦然听到个‘兵’字,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以为走错门庭了。”
这话说得不轻,徐致靖意态不变:“没听说胶多不粘,话多不甜么?我们空话说得太多,都没有挪步力气了。你说君臣大义,且说这君,君贤不贤?为救国而变法,为变法而招怨,不惜以一身与天下顽人相抗,做臣子者,能无视乎?你这臣子又不同于他人,你犯颜上书,声震天下——”
王照抢过话去:“小侄上书是想调和两宫。自诏定国是以来,外间传言,总说太后守旧,守旧诸臣也乐于趋附怂恿,离间两宫。小侄私心揣摩,太后并不守旧,因为若依旧礼,她根本不该垂帘!此时退居园廷,不得干政,才愿与顽固诸老接近。为皇上计,应将变法之名归于太后,用亲情化解小小嫌隙,使旧派失去依靠,何能死水翻波?小侄苦心,与年伯用心不同。”
徐致靖竭力辩说:“看你误会到哪里去了。我有几个脑袋,胆敢不利于太后?变政要一变全变,军营岂能例外,你去芦台宣传朝廷德意,这是光明正大的,谁能说个不字?”
徐致靖说不服王照。王照回去后心思沉重,似看到一场灾难,在阴暗处待机而发。康有为是固执的人,不会因拒绝而改变,王照将不胜其扰。由康有为想到张荫桓,王照眼前一亮,自以为找到了办法。
近日张荫桓上《保举将才折》,举荐署通永镇总兵李大霆,通州协副将龙殿扬,已革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张上达等。这张上达曾任河工总办,私吞工银,克扣桩料,被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参奏革职。张荫桓明显是卖折,王照敲一敲张荫桓,也可向康有为示意。他当即拟折参张,光绪当日下旨,着山东巡抚张汝梅查明具奏。对于这种情况,康有为尚无所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约梁启超、徐仁镜来寓,打算叫他们二劝王照。徐仁镜晚来了一步,梁启超对老师吐露疑虑,我们一帮文人,突然打武人的主意,恐怕此路不通。
康有为尚未回话,徐仁镜匆匆走进“汗漫舫”,右手捏着一册邸抄。他尊了一声“康先生”,就把邸抄递过去。康有为接过翻看,眼光被绊了一下,仔细读完,顺手交给梁启超。康有为目视徐仁镜:“莹甫对此有何意见?”
徐仁镜忧形于色:“家父刚刚请他劝聂,他立马上参折扫到了聂,这是冲着先生来的。”梁启超轻轻放下邸抄:“莹甫说得有理,王小航另有玄机。他也许不扫聂,借此表明态度,倒也不失其巧。”
康有为了不介意:“什么态度,不让我们饶舌?我们偏偏不解其意,卓如、莹甫,你们现在就去。”徐仁镜急扯白脸:“家父,家父不让我去。”康有为反而笑了:“好好,听风就是雨,这就叫见几。卓如,我跟你一起去。”
康先生亲自来拜访,叫王照又是高兴,又是别扭。康有为开门见山,他说看到了邸抄,本应有所避忌,可是转念一想,有话说在当面,方为朋友之道。对于张荫桓其人,他向来有褒有贬,其长处是知洋识时、善于办事,短处是不学无术、贪污赃私。康有为加重语气:“这件事不用说,是樵野得钱卖折。张上达来京撞木钟,有一回竟摸到我门上,被我赠一打油诗:木钟撞到宣尼家,蹭倒牌坊磨掉牙。营穴何如树上鸟,笑你没修吃杯茶。宣尼者,至圣文宣王孔仲尼也;没修者,没羞也。张上达后来巴结上张樵野,以同门叔侄相称,孝敬三千金。”
王照听得咂舌,康有为话锋一转:“我常跟弟子们讲,小航性勇,眼里揉不进沙子。这不算恭维吧,一本参倒六堂官,试问本朝有几人?你的勇还得借天恩,请看今日,维新之局,危如累卵,皇上之孤,人所共见。张樵野之受宠信,恰好说明无人可用。皇上明诏广招人才,我等无资格保举,却有义务考察,以备皇上选用。”
王照听不下去:“选用?聂功亭位从一品大员,他正得到重用!先生要考察什么,看他有没有忠心?”
康有为不慌不忙:“不错,多少一品或极品,并不能保证忠诚。聂功亭向强学会捐过款,他热心于新政,倒是我们懒于联络,整日在笔墨上费心思,把极要紧的方面疏忽了。究其实际,这才是关键,到不得已时救得性命的。”
王照越发不安:“先生说得吓人,你要干什么,鼓动兵变?”
康有为笑了:“那不连我也变了进去?康有为的锦囊中,除了忠字还是忠字。我要聂功亭也如此。”他的口气很满。梁启超怕王照不高兴,出来转圜道:“小航生怕造次前往,惹起误会,彼此都不利。可以转着弯去,譬如向军营送书,为官兵授课,或者宣讲新政诏书。皇上原有令各衙悬挂的诏旨,没有提及军营,这倒应该补上。”
康有为被学生提醒了:“对对,就从这里入手。张元济日前奏请,令京外大小各官一一表态,愿行新政与否,均须立字为据。此策暂未披露,聂功亭最好先行一步,为外官做出表率。这样一来,全国督抚都将依他为准。聂功亭的职任,还会限于提督么?”
话说得如此露骨,王照索性明问:“你想让他怎么做?”康有为道:“他只要愿行新政,我们就可奏请皇上,召聂觐见,待时机成熟,即可委以直隶总督重任。这个要害位置,不能由太后的私人把持。”王照心中骇然:“总督之位,恐怕皇上也无力挪动吧?”
康有为胸有成竹:“所以就要变。变法就是变权,没有用人行政之权,一切都无从谈起。”王照再也按捺不住,立起大呼:“王小航能当狄仁杰,不能当范雎,先生打错算盘了!”狄仁杰是唐朝名相,他劝谏武则天顾全母子天性,不要危害太子;范雎是战国时秦国名相,他建议秦昭王加强王权,废黜太后,放逐争权的母舅与兄弟。王照是力主和合两宫的,他怎会迎合康有为之意,做此挑拨离间之事!
康氏师徒无功而返,梁启超在路上向先生进言,这有行险侥幸的意味,还是少做为妙。
康有为不禁叹息:“如能安步当车,谁肯铤而走险?我们步步艰难,以至恶煞环伺,有刀剑加颈之势。若不有所预备,难道束手就擒?当然也可隐退,但那等于开溜,将隐约可见的胜果,拱手让于他人。卓如,让你滞留在京,我知道拘囿了你,才华不得抒发,情愫不得表露,前程亦无寸进。然而你要明白,为师所求者大,区区一二品官阶,入不得夫子之眼。前明于谦诗云: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于清白之外,还要有万紫千红,使山河为之易色。此等境界,狄仁杰、范雎安能想望!”听先生表白心迹,梁启超非常感动。不过,想不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又是一回事。老师万事纯任主观,弟子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尊师。梁启超遵从老师的意愿,去见徐致靖之侄徐仁録,要他再次赴津,游说新军首领袁世凯。
徐仁録曾经名列强学会,与袁世凯有同会之谊,他上个月便以联谊为名,做军中之游。他的一位姻亲言敦源,由翁同龢荐入袁世凯幕府。有这两重关系,袁世凯对他颇显亲热。时隔不久,故友重来,不会是专为酒食征逐的,袁世凯岂能不明白。新旧两党水火不容,北京城如同一口铁锅,被烈焰烧煮得趋近沸腾,袁世凯早就感到灼痛。他是热衷之人,一直未置身事外。
回想往事,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间,原在小站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升任顺天府尹,李鸿藻荐袁世凯接掌练兵。练兵事宜隶属于督办军务处,因无专人主管,遇事互相推诿。袁世凯上书军机处,请由督办军务大臣、兵部尚书荣禄专管。恰有御史参劾袁世凯,“性情虚妄,扰害地方”,旨令荣禄查办。荣禄到津视察袁部,见其军容壮盛,部伍严整,大加赞赏,复奏时对袁多方开脱,并称“一二年后定成劲旅”。德占胶州湾后,荣禄上《请广练兵团以资防守折》,要求新建陆军添募兵额,与聂士成军互为犄角,扼守北洋门户。朝廷准令添招三千人,这是一个喜讯,袁世凯为此数次赴京,因为户部无款,迄今尚未落实。此中隐秘,外人不知,上次徐仁録来津盘桓,便拿这事当幌子。徐仁録称,翁同龢曾想为袁世凯增兵,被荣禄阻止。近来徐致靖、谭嗣同疏荐袁世凯,皇上意欲召见,征询直督意见,荣禄的复言不利于袁世凯。袁世凯并不戳破,反而迎合着说话,使这个谎言能够扯下去。双方都想拉拢他,这样对自己最有利,为什么要把底牌亮出来?
徐仁録一到小站,便又如鱼得水,幕友徐世昌、言敦源,袁府长公子袁克定,都来陪他聚谈。这也是天津官场的风气,天津是北京的后花园,由于不知道哪朵云彩会下雨,便对每一片京云都欢迎。直到天黑,袁世凯才从兵营脱身,回到公馆会见客人。陪着饮了几杯酒,大家便早早散去,让徐仁録跟袁世凯说“正经的”。徐仁録确有正经事,他请袁世凯看一份奏折草稿。这是胡景桂的手笔,他就是参袁的那位御史。御史可以风闻言事,他那次参奏便得之传闻,事后通过亲自查证,才知那是诬参,因此打算自劾,并推许袁世凯才堪大用。
这样的折子很罕见,袁世凯当然看重,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徐仁録这才说起事情缘由:新建陆军成立不久,津门官绅便找李鸿藻告状,称袁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节制。李鸿藻生怕自己清名有玷,示意同乡胡景桂纠弹。今李公仙逝,康有为跟其子李宗侗有交情,从他那里得知这段纠葛,便去奉劝胡侍御,要为朝廷珍惜人才。
兜了这么大圈子,就为了推出康有为。袁世凯肚里好笑,嘴上慷慨激昂:“南海先生,那是我最佩服的人物,可惜我对他有二憾在心。一憾去冬,他晋京过津,本想来会我,却又怕我人一阔脸就变,竟未辱临。二憾今春,我上京办事,一进城先去南海馆拜望,不巧恰值先生外出。原期办罢事必拜晤,不料事到中途,小站营中急电呼归,我不得不走。以至他回京半年多,我竟与他咫尺天涯!嗐,阴差阳错,愧对故人哪。”
明知他多次进京,都对康有为避而不见,徐仁録不去揭穿:“康先生也有此恨,不过他说彼此心照,在非常时期,不见反比见了好。”袁世凯故作疑问:“非常时期?”徐仁録道:“是,京中风声甚为凶险,都说九月将有大变。”袁世凯浓眉挽起:“九月?”徐仁録道:“九月,那是两宫赴津阅兵之期。所谓大变,便是废立。”
这回袁世凯真正惊讶了:“胡说八道!谁敢造此大逆之言?”
徐仁録道:“欲行大逆之人造的。他们憎恶皇上,只因他推行新政,叫顽固之徒如丧考妣。京中谣言如海,从皇上病危到宫中内乱,无所不用其极。天津废立虽是谣言,的确有人企图废帝。请勿误会,这不是太后,而是心怀鬼胎之人,欲借太后之名,实行篡弑之事。”
袁世凯沉吟良久,语含悲怆:“时局如此,岂不令人悲恸欲绝。世凯不才,从朝鲜之役到小站之军,惟思为国倾此热血。谁料蝇营狗苟之辈,不惜挖掉国家柱脚!”
徐仁録道:“慰庭兄说到根儿上了。他们阴谋犯上,在京尚不易行,因此寄希望于津。”
袁世凯顺着话音儿说:“在津也休想!有老袁之军,还有老聂、老马之军,这些都是吃素的?”徐仁録频频点头:“吃皇粮,保皇帝,方是小站好男儿。小弟此来,康先生交代一句话:强学会乃忠君之会,请慰廷记取忠君二字。”袁世凯声如洪钟:“先生之教,世凯明白!”
天津之行功德圆满,弥补了芦台的缺憾。约下一支援军,用以防备急难,便可定下心来应付繁难了。当下急务仍在军机,通过文悌之手,刚毅看到了曾廉条陈全文。条陈已经上递,手中没有证据,刚毅考虑将曾廉条陈重新上呈,又怕用意过于明显,反把事情闹得更糟。只有亡羊补牢,刚毅吩咐几位领班章京,要对杨、刘等人注意监视,以防他们再做手脚。
章京房的气氛又紧张起来。林旭告诉康有为,杨、刘都想打退堂鼓,他和谭兄也感到差事难干。好不容易插进一根针,哪能轻易抽出来?
不抽就需要鼎力支助,谁能入军机当靠山?李端棻,徐致靖,与中枢的距离都太远。康有为突然想到一个人,黄遵宪。黄的官位,与李、徐相差甚远,然其眼界与学识,却是当今达官无人能及的。他能不能入军机主持新政?他此时远在上海,得到的任命是驻日公使,入枢之途尚待描画。最现成的一个人,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可惜这湖南陈与湖北张,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需要动手修一修。
康有为在这里运计筹,也有人在别处转心思。数日来接连有人上书,均建议以张之洞为首相。在这些人看来,新旧两党势如水火,而康有为一派还在玩火,釜底抽薪之策,便是请一尊菩萨镇着。杨锐对此颇有同感,他找刘光第商量,能不能重拾旧议?刘光第有些犹豫,目前之局,非有大魄力者无以挽回,香帅有此力否?推而广之,哪一位有此力?即使是一位真神,置身于此也能熔化,同毁俱损,于事何补?
这么说,没救了?两人切磋一番,杨锐不甘心,仍要试探一下,他将这些议论函寄武昌。对这种危险的推举,张之洞一点也不喜欢,很快电示杨锐,不要扬汤止沸。湖北眼下的烦心事,是黄钦差追杀汪进士,京卿们能否设法救汪?黄钦差就是黄遵宪,他离鄂前口头答应张、梁的要求,让汪康年将报馆旧账交与张之洞,张之洞再转交黄遵宪,《昌言报》照常出刊。“身”当其冲的汪康年,并未就此放下心来。他找到在上海办《汉报》的日本人宗北平,双方商定合作方式,各自在对方的报端署名。
汪康年向武昌报告说,这比挂洋牌体面些。汪康年正打如意算盘,黄遵宪到了上海,着手处置汪、康争端。他先去到报馆,派人投进名刺,馆内回复汪康年不在。这都是面子上的做法,按照惯例,接下来应是汪康年回拜。黄遵宪等了一天,那边无声无息,他派随员前去传话:遵旨查报,令馆方将人欠馆款、馆欠人款,清列账目,全盘交付官报接收。
这与武昌传来的讯息迥异,汪康年慌了手脚,复函分辩:一则称等待南洋公文到沪,报馆即上禀交接细目;二则称此馆系集捐而成,有所变动,捐款诸公皆应与闻,断非汪某一人所敢擅行。这是拖延之术,黄遵宪不跟他饶舌,又派员去催。汪康年反请黄遵宪将报馆实情上奏,待有明旨,立即交报;一面又向武昌告急,央求大帅与钦差论理。
未等张之洞发话,黄遵宪先给他发电。电文很长,首先简述与报馆交涉经过,然后说:汪先刊《告白》,称系己创,今又称馆系集捐,交收难作定议。遵宪所奉电旨为,是谁创办,查明原委。查此馆开办,宪自捐一千元,复经手捐集一千余元,汪以强学会余款一千余元,合四千元,载明《公启》,作为公款,一切章程帖式,系宪手定。《公启》用宪及吴、邹、汪、梁五人名,刊印万份,布告于众。是此报系公报,以公报改作官报,理应遵办。且宪系列名倡首之人,今查办此事,不遵议交收,宪即违旨,此宪所断断不敢者。如汪能照交,即行电奏,自可妥结。如汪不交,宪只得将核议各节,电奏请旨办理。宪自问所以尽友道而顾大局者,一则改为《昌言报》一事,绝口不提;二则所列结账,即有不实不尽之处,断不纠问;三则所存各项,倘不能照账如数交出,当为通融办理,此为宪心力所能尽者。为汪计,理应交出;倘或不然,结局难料。再,宪有密陈者,汪在沪每对人言,此报改为《昌言报》,系宪台主持,惟宪实不愿此事牵涉及于宪台,流播中外。总之,此事系将公报改作官报,非将汪报改作康报。倘蒙宪台鉴宪微衷,求宪台将宪遵旨核议交收之法,电汪即行遵办,免旷报务而误程期。
此电到达武昌,张之洞看后倒吸一口凉气。黄遵宪是《时务报》的真正发起人,他若打定主意,谁能跟他辩理?梁鼎芬气不忿,直后悔没有亲去上海,为汪康年做后盾。张之洞摇头说,谁去也不行,黄遵宪今非昔比,腔调大变,即为明证。北京有讯,皇上有意让其做尚书衔使日钦差,而康党正大肆活动,留黄在京做军机、入总署,当新政的主心骨。情势变方法跟着变,湖北何必出头硬抗?
张之洞委婉回电:报事与阁下在鄂晤谈后,曾劝汪交出,不必系恋。兹当更劝其速交,但不知肯听劝否。至此事恭绎电旨语意,并无偏重一面之词。阁下如何办法,自必能斟酌妥善,上孚圣心,下洽公论也。附致汪一电,请转交汪穰卿:报事速交,最为简净,千万不必纠缠。《昌言报》既可开,若办得好,亦可畅行,何必恋此残局,自生荆棘哉。张电软中带硬,称电旨并未偏重一面;同时抓住黄电“绝口不提”四字,强调“《昌言报》既可开”。张之洞又给长驻上海的赵凤昌发电,令他转嘱汪康年,向汪康年的同乡王文韶求助,最好能在京断康后路。
黄遵宪十分清楚,他把老宪台得罪了。由于长期驻外,对于东洋和西洋,他看得比任何达官都透彻。张之洞以洋务领袖自居,但他的洋乃是“羊皮”,只能做双皮靴隔痒而已。他还要用这靴束别人的脚,比如湖南新政,就被他拘得举步维艰。在人矮檐下,黄遵宪不得不削足适履。现要出洋了,他至少应拿出一点留洋的做派,使事情回归本来面目。这放在张之洞眼中,就是忘恩负义,而且是小人得志。这也是中国的“本来面目”。
思索至此,黄遵宪心中隐隐作痛,有一种彻骨生寒的感觉。梁鼎芬骂他“欲行康教”,这一回他更是得寸进尺,跟康有为站在一条船上,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实则究其内心,康有为的躁进偏激,他也不以为然;当前的京中情势,他也望而生畏。康有为们的谋划,他认为不会成功。即使他真能高升入枢,在那个荆棘场中,他又能做成什么?这正好表明,书生之见与谋国之略,中间隔着无形的天堑,康有为永难跨越。因此,黄遵宪不愿急急进京,他倒希望康有为出京。他硬起头皮追讨《时务官报》,便是为康有为预备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