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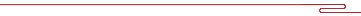
这一下就像飞蛾扑火,康广仁被几个人扭住,推来搡去。马老三吩咐:“不要打他,冤有头债有主,咱们去逮那最大的。”便有一群人往前拥。眼看躲不过,康有为索性上前迎住:“诸位缠着我闹,不觉得没意思么?”马老三笑道:“有意思,我们跟大名士闹一闹,也能沾光出出名。”他像将军一样下令,分成几拨去抓人。康有为、杨锐、宋伯鲁,各被五六个人围住。
岑春煊这时却往后缩,溜到刚走出门的陈炽身边。他小声问:“陈兄,怎么办?”陈炽白着眼不吭声。岑春煊故作惊慌:“老兄若无奇招,只怕无法免祸。”陈炽大喝一声:“我有奇招!”手一伸攫住岑春煊,将他双臂反剪,推到众前:“我擒了你们的首领,咱们走马换将!”
全场惊愕之时,岑春煊哈哈大笑:“称我首领,诡计已破,兄弟们不要玩了。”马老三等人也都笑着,请罪告饶,给大人们压惊。原来这一出是岑春煊闹的,他听说康有为只要露面,必有人闹场,便耍着把戏给他助兴。这家伙顽皮得过了头,朋友们拿他没办法,笑骂着分了手。
岑春煊兴尽回寓,所谓宅寓,其实是一处相公堂子。岑春煊放荡不羁,正跟一名男妓打得火热。他哪里知道,他引燃的野火正在冒烟,要把他和同党烧成灰烬。
从天未放明时起,便有人沿着蛛网般的胡同,奔向长安大街,辐辏至宫城南端。等到晨光熹微,午门前的开阔地上,已有上百人聚集。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城门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筑有三丈六尺高的城台,犹如巨人张开双臂,将方形广场揽于胸前。城台正中门楼面阔九间,重檐黄琉璃瓦庑殿顶,左右城台之上,有东西庑房各十三间,雁翅般向南伸展,俗称雁翅楼。在东西雁翅楼两端,各有重檐攒尖顶阙亭一座,四亭拱一殿,三峦环五楼,故又称作五凤楼。午门威严,显示的正是紫禁城之禁。只有出兵打了胜仗,班师回朝行献俘大典,皇帝才亲临午门受献。近年皇朝连吃败仗,在午门施行的典礼,便是每年十月初一的颁朔之礼,即是将历法颁行天下。
今天,麇集在五凤楼下的,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官员,一个个身着朝服,顶戴花翎,神情比举行典礼还要凝重。这种情形非同寻常,守城护军火速报给参领。参领也不明就里,一边监视防范,一边飞报有司。
此时朝霞满天,红日初升,给五凤楼顶的黄瓦镀上亮眼的金色。楼前众官却是满面乌云,比丧礼上的吊客还要阴沉。立在最前面的一位,是太仆寺卿靖勋,他身旁有几位少卿,分别来自大理寺、太常寺和太仆寺,还有詹事府少詹事,通政司参议,宗人府宗丞等官。不用说,这都是此次裁撤之官,追随他们而来的,是各寺寺丞、光禄寺署正、通政司知事、大理寺评事,还有数不清的主簿、典籍、司库、读祝官、赞礼郎、协律郎、满洲鸣赞等等名头。靖勋吩咐下去,叫大家分别衙门,按照品级,顺序排列,不准嘈嚷。官有官派儿,排在前面的府寺卿贰,都低眉顺眼做恭顺状。
这时只见左侧门启,一名将官骑马出了门洞,来到靖勋面前。此人为护军统领,正二品的大员,奉领侍卫内大臣之命,询问众官来此何干。靖勋答称,向皇上奏陈下情。统领说,皇上不在这里。靖勋说,此乃禁城,皇上正位之地。统领说,既是禁城,各位大人理当遵禁。靖勋说,只禁奸邪,不禁正人。
统领有些着恼:“靖二爷,我敬你这条黄带子,所以不愿使蛮。也请二爷看兄弟薄面,不要误禁军差使。”靖勋不为所动:“你满可扯断我的黄带子,不过,那要皇上下旨。本人伫候。”统领不再跟他纠缠,面朝众官发话:“各位吃皇家饭,遵朝廷法——”靖勋夺过话头:“各位无饭可吃,有法可依,这法便是准司员士民上书,无人敢扼住你的喉咙。”无数喉咙放开声量:“讨饭啦,讨饭啦!皇上可怜可怜吧!”
统领气得回马便走,要派护军下城驱赶。靖勋哪能让他使出这一招,回身使个眼色,立即带头跪下。众人忙都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靖勋直挺挺地跪着说话:“太祖太宗、列祖列宗、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今上皇帝万岁爷呀!奴才祖上随旗起兵,从龙入关,九代二十三门八百六十号人丁,流血流汗效犬马劳,守鹰隼职,无时无刻,不敢稍懈。皇天不吊,国运式微。皇上奋起变法,力矫衰世之弊,凡在臣列,皆当欣从。惟小人怀奸,妖鬼作恶,康有为鼓吹邪说,诬孔蔑圣,称王改制;梁启超传播康教,崇洋媚夷,趋步学舌。更有岑春煊拾其余唾,擅上条奏,变乱祖制,败坏朝纲。撤衙即撤清国藩篱,裁官即裁皇家爪牙,削我之根,孤我之本,妄言之害,莫此为甚。皇上不察,一旨颁下,千家泪出,不仅为己伤,而且为国悲,诚恐忠良丧尽,奸谋得逞,宗社沦落,悔之晚矣。今日奴才冒天下之大不韪,非为独抒孤愤,乃是贡献愚衷,愿拼一死以除奸佞。恳求皇上鉴察下情,收回成命,翦灭祸患,斩康、梁之首以安民心,斩奴才之首以谢康、梁,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靖勋说罢,放声大哭,匍匐其后者跟着号啕。这就叫伏阙痛哭。护军统领何曾见过这种阵仗,驱也不是抓也不是,急忙报告领侍卫内大臣。
内大臣不敢怠慢,赶往西苑见驾。首先来到军机值房,世铎听罢一惊,刚毅听罢一喜,裕、王、廖三人面无表情,各怀心思。靖勋这老小子挑得真准,地点和时机都恰到好处。明知两宫住在西苑,他不来西苑告御状,以免给太后老佛爷添堵。跑到五凤楼前伏阙,那是天家和民间接壤处,谁也休想把消息隐瞒住。那也是明白告诉太后,错事是皇帝干下的,她老人家进可施法捉妖,退可闭目养心,无论如何手都是干净的。
领班王爷世铎,引着领侍卫内大臣,进入涵元殿,奏报光绪帝。
光绪怒火中烧,直想冲口说出:着将靖勋等为首人员拿交刑部,按阻乱新法治罪!可他忍了又忍。靖勋等人希望的,正是把乱子闹大,以显示皇帝性情之鲁莽,手法之粗糙,对满洲老人之冷酷,对浅薄小儿之偏听。光绪下了几句口谕,要军机处据此拟旨。世铎退出令章京拟稿,然后呈交御览。光绪阅后批准,即令世铎、裕禄,会同领侍卫内大臣,赍旨前往午门,晓谕遣散众官。
世铎与内大臣来到军机处,刚毅听罢大笑:“这样的美差不派刚毅,专派裕大福将,真是能人多吃四两豆腐哇。”裕禄也笑:“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要是你去撒泡尿,不把一锅豆浆浇坏了?”三大臣离开西苑,驱车直奔天街。
距午门还有一里路时,遇上了左翼总兵英年。原来,内大臣赴西苑前,通知了步军统领崇礼,崇礼派英年率兵来迎。马队沿街开道,来到五凤楼前,但见广场上人头攒动,像赶庙会一般热闹。英年下令驱赶,赶场的大多是旗人,他们跟兵士打牙斗嘴:今天打掉官老爷的吃饭家伙,明天就割旗大爷的铁杆庄稼。要让大爷离场,你就请皇上下旨,给旗人增加钱粮。英年不跟这些混蛋纠缠,保护三位天使,到午门前与崇礼会合。崇礼令兵士排队入场,将众官与乱民分开。然后与三使一起,来到众官面前。靖勋依然跪着,埋头不看来人。世铎在他的头前站定,鼻子里哼出一声:“靖勋。”靖勋没有应声。世铎又叫一声,仍未得到回应。
世铎突然发怒,抬起一脚踢到靖勋肩上,将他踹翻在地。世铎边踢边骂:“你这王八羔子!老子不按国法,只行家法,打死你这混账行子!八旗里没有孬种,宗室中更无浑球,你他妈瞎搭一条黄带子,还有脸充人五人六!”一时满场屏息,掉一根针也能听见响。靖勋却无声息,像一摊破布丢在地上。
世铎拍一拍手,掸一掸衣,从裕禄手中接过谕旨,向众宣读:“维新始启,新政肇开,官制为致治之本,尤须剔其弊端,而增其生力。卿寺诸官,冗散者多,叠床架屋,重沓无谓,任其事者亦啧有烦言。此次裁撤,即改制应有之义,亦众论可行之举。虑及所裁人员废弃可惜,前旨即有明示,听候另行录用。尔等在官多年,皆当善体上意,岂可违逾规纪,致干不测之咎?其速各归清结,以备甄别简用。”世铎念罢,跟崇礼和英年对对眼色,与裕禄一起回身便走。
清场官兵大声吆喝着,半哄半撵,将哭阙的官吏驱离大街。靖勋鼻青脸肿,被一群兵丁簇拥着,以为要被押往刑部。谁知转入一个胡同,兵丁便抛下他风一般卷走。看来他只是挨了一顿揍,揍他的是王爷,犟不得的。这位王爷回涵元殿复旨,光绪听罢无语,只示意召见岑春煊。对岑春煊的任用,明发当日即叫起请训,这是为了赶岑快走,更是对太后有所交代。
然而怎能交代过去,午门之乱堪称奇闻,慈禧会作何反应,想一想都叫他怵头。岑春煊应召叩见,君臣不再谈裁官,开始讲剿匪。“匪”指的是广西会党,近来广西会党猖獗,使得朝廷很是忧心。因为先前的太平军之乱,就是从广西发端的。光绪谕令岑春煊,到粤后注重剿办桂匪,同时察考总督谭钟麟,若其年老误事,便当如实奏报。
岑春煊叩头退出后,早朝便告结束,光绪要去仪銮殿侍应。想一想慈禧的脸色,他真怕去见她。他不知道,慈禧也不想见他。慈禧耳目众多,宫城的要害讯息,她总是转瞬即知。午门的这场乱事,要报却得掂量一下。因为此乃咸丰忌日,她处于哀痛之中,按礼需要斋戒,谁敢拿坏消息去触霉头?
可偏偏有人早早来报,这个人是怀塔布。自从黜革旨下,怀塔布蛰居西山,“一心闭门思过”,这六个字是他向朋友表白的。昨晚大理寺卿和太常寺卿夤夜造访,告诉怀塔布,靖二爷要纠合众官,哭阙诉冤。怀塔布深表赞同,却不主张几位正卿全部到场,以为那会让太后难过。正卿们乐得缩进黑影中,只怕靖勋不同意。怀塔布同二位正卿一起进城,说服靖勋独唱黑头。
到了早晨,怀塔布专程经过午门,目睹了苦辣酸涩的众生相,赶至仪鸾殿,先找着太监总管李莲英。二人算是心腹搭档,一个打里,一个打外。李莲英告诉他,太后进过早点,饮了半杯茶,吸了一管烟,正想有个人来说话,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李莲英代他通报,慈禧果然很高兴。怀塔布应召进殿,跪拜请安。慈禧瞧瞧他那张苦脸道:“这一向没见着你,躲哪里去了?”怀塔布再磕头:“奴才在西山修省,只因身负重罪,不敢污老佛爷之目。”
慈禧微微撇嘴:“西山可是福地,你倒会挑地方。修出什么来了?”怀塔布道:“回太后,奴才初时不服气,认为上头不分青红皂白,处置过当。这些天细思深究,才知臣等之失,就在以寻常习惯,应非常事态,没能体会皇上急求自强之心。”
慈禧想了想,轻声叹息:“这是真心话,能够转过弯,算你没有白跌一跤。皇帝好就好在急字,如果臣子有误解,也误在急字上。他为九五之尊,完全可以安享洪福,把难题推给臣下。现在反成了他推你们,拍胸口问问,亏不亏心?我最生气的,是那改不掉旧习惯的,把恶水缸扣到我头上,好像是我指使的他们。我一辈子改改改改,怎会喜旧厌新?真是的,嘁!”怀塔布连连应是。
慈禧瞅他一眼:“当面说是,背地算计,我还不懂你们?”怀塔布慌了道:“奴才的小心思,都是为了效忠……”慈禧不让他往下讲:“罢了,忠奸只有天知道。你好像还有事?”怀塔布舔一舔口唇:“奴才怕惹老佛爷生气,可是该死,这事叫奴才撞见了。”
觑觑慈禧的脸色,怀塔布讲述了午门前的情景。
慈禧静静坐着,足有五六分钟,嘴角浮出冷冷的笑意:“开国以来头一遭,这可丢人现眼了。我记得靖勋蛮沉稳的,他为何当出头鸟?”怀塔布道:“奴才从一位亲戚处听说,靖勋早就想辞职,还要出家当和尚。”慈禧皱起眉:“当和尚?为什么?”怀塔布道:“他觉得国家没希望,不是败在洋人手,是要坏在自己家。前些时市间风传,朝廷要废六部九卿,开鬼子衙门,用日本人和英国人做客卿,入洋教,穿洋服。这当然是没影的事,可霹雳一声裁官旨下,谣言成真,奴才揣摩,靖勋拼死的心思都有,这才演了那么一出。他是要哭庙啊!”
慈禧不安地动了动,似要发怒,最终只是说了句,你跪安吧。驱走这只丧气的老鸹,慈禧的怨气在胸间积聚。明天就是七月十七,那是她追悼咸丰、怀念旧恩的日子,她应当心境安恬,神思宁谧,偏偏闹得鸡飞狗跳,像要亡国似的。就是再紧迫,难道不能熬过这两天,等她回到园廷再动手,她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这哪是心急,这叫成心!
她坐着看到皇帝进殿,跪下请过了安,立起身垂着手,现出局促的样子。她故意没让他坐,听光绪说广东匪患吃紧,已着岑春煊请训出京,加紧剿办。这又是个躁急事例,看来他已骑上虎背,非到撞死停不下来。慈禧不接这个话题,转问一句:“京城修路已经开办了?”光绪回道:“是。近日共收到有关奏折九件,涉及铺设铁轨、开自来水、架电气灯、改良街车等项,儿已批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和街道厅筹办。”
慈禧道:“修桥铺路,这是正办,可也要避免骚扰百姓。听说有商民呈文,恳请体恤,怎么回事?”光绪忙道:“大清门至正阳门一带,商贩众多,占道塞路,多有抢摊斗殴者。监管衙门为了修路,令各贩迁至城根儿摆设,既利商也利行——”慈禧道:“这也利那也利,他们为何诉苦?好事办不好,那还不如闲着,省得鸡争鹅斗。”
本要顺口应是,光绪想想改了口:“有多少人只图自己方便,不惜予人不便。迁移几天后,商贩也感到买卖便利了。”他是皇帝,对此琐屑知道得那样详细?慈禧不愿显出挑毛病的样子,把语气放缓:“我希望再回来时,看见城中路平河清,百姓安乐。不过也许不回来了。”光绪心里一紧:“皇额娘回城佛光普照,男女老幼都很欢喜。”
慈禧正面瞅着光绪:“怎么个欢喜法,能说说么?”听这口气,那桩乱事她已知道了。只是可惜话赶着话,没给他合适的上言时机。光绪深吸一口气:“还是那句话,有多少人只图自己利益,勾群结伙顽抗朝命。靖勋等人不满裁官,在午门闹事,儿已派世铎、裕禄晓谕遣散。”
这话听起来轻飘飘的,慈禧懒得给他留脸:“两伙人都会‘只图’,要怪有人只图自己痛快,没替别人留下一条活路!就说这个靖勋,他若当甩手大爷,岂不逍遥自在,硬要出来当差,图到了什么利益?好心不得好报,忠臣无尽忠处,再不哭上一哭,只有活活憋死。我不替他开脱,只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而已。”句句都在理上,可又好没道理。分辩的话涌到口边,忽然万分灰心,光绪抽一下鼻子:“额娘教训得是。”
慈禧狐疑地打量他:“你似乎有些委屈?”光绪神情木然:“儿不委屈。儿不止一次后悔,儿不该勉强,不该自苦,不该做费力不讨好之事。安分易,逆势难;认命易,抗争难;守旧易,图新难。儿之避易就难,只为不忍之心,不忍见祖宗江山沦于敌手。儿不惜叫靖勋他们哭庙,就因怕最后那场哭庙,找不住地方去哭。”
句句沉痛,字字扎心,慈禧怒气陡升,话却憋在肚里。她站起身道:“我回园去!我在这里没有坐处!”光绪扑通跪下:“儿子不孝,请额娘责罚。”慈禧向内走几步,又倏地转身:“你做得都对,做娘的都不对,我给你认错,行不行?”
光绪泪流满面:“气着了额娘,儿子万死不足蔽辜!只要额娘能够消气,儿子愿意收回成命。”慈禧心中乱马交枪,要打要杀,可有四个字十分清晰:覆水难收。发出的谕旨不能更改,没迈出的那一步不能轻跨。她哀叹一声:“罢了,再气也是自家母子。不该的是我多管闲事,给你平添无穷烦恼。以后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娘儿两个总算和好,光绪又过了一关,打叠精神侍慈禧进膳。次日辍朝,皇帝奉太后去到太庙,在咸丰神位前祭献如仪。慈禧没再过问政事,光绪也未顾及他事,尽心尽意地陪侍太后。七月十八,慈禧不让光绪陪同,独自摆驾回园而去。
光绪照常视朝,并就裁官事宜再发谕旨:前经降旨裁撤詹事府等衙门。应再申谕大学士、六部尚书及各省督抚,遵照前旨,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迅即切实筹议;外省道员及通同佐贰等官,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严加甄别淘汰,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这道申谕传至武昌,张之洞看罢不由咂舌。谁不知道,湖广总督好大喜功,大局名所数不胜数,铁厂煤矿开了又开,名位虽是一方诸侯,实业却占半壁江山。要创业就得有人,当初梁启超莅鄂,他要放炮恭迎,便是突出的一例。后与康、梁分道扬镳,那叫道不同,大包大揽收罗人物,这叫谋相从。正担心人不够使,哪有余力裁减?然而不裁不行,皇上电责谭、刘,镇唬荣禄,不会单单放过张之洞。何况张氏劝学曾蒙表彰,他应再获一次奖。好在他的局厂多,先把公所合并一下,名目变更一下,再把东局委员调西局,南厂匠师挪北厂,走马换将,移花接木。除了节流,还要开源。这件事他交给恽祖祁办。此人为湖北按察使恽祖翼之弟,张之洞委任其办理宜昌盐厘局等肥差。最近由于陈宝箴的保举,恽祖祁获得光绪帝召见。在召见中,恽祖祁奏述了湖北办理民团,鄂督为此艰难筹款的情况。召见后,为了遴选军机章京,军机处拟交名单中原有恽祖祁,光绪恰未选中他。而他稍后补授福建实缺道员,在赴任前上一条陈,内称鄂中八省通衢,水陆云附,各业皆可设团练兵。
光绪采纳此议,寄谕张之洞:“兹既据该道筹度鄂省民兵及预计饷源一切事宜,所有矿团、农团、岭团、滩团、堤团、客团六事,是否能于办团之内兼谋兴利之方,实有兴练民兵之效。着张之洞斟酌该省情形,先行试办。”
这样一来,张之洞的摊子铺得更大了。他这里顺风顺水,同城为官的谭继洵却正在霉运中。谭为裁撤三巡抚之一,还在谕旨上首当其冲,好像专门要他难堪。而其子谭嗣同荣任军机,此中隐曲耐人寻味,并且引起不少谣言。有人说嗣同乃新派急进,久与其父水火不容,得势之后昧心反噬,凸显康党无君无父之本来面目。有人说嗣同倾挤张之洞,要为其父谋总督之位,不料打虎不成反被伤。
种种传言荒诞不经,张之洞付之一笑,对谭继洵更加同情。谭继洵以守旧著称,共事九年中,与张之洞时起龃龉。然公义不碍私谊,值此危难时刻,他不会落井下石。有关此事的电旨是:“湖北巡抚关防着交张之洞收缴,谭继洵来京听候简用。”
张之洞接旨后,即亲往汉口抚慰,谭继洵却想得开,要尽速办理移交。移交过后,张之洞设宴款待,席后促膝谈心,问及谭兄何时北上。谭继洵笑了笑:“不北上了,我要南去,回家乡浏阳了此残生。”张之洞颇感意外:“电旨谆谆,进京简用,吾兄正可施展抱负,怎能萌生退意?”谭继洵道:“抱负云云,距我太远。我生性迂拙,抱残守缺,备员于汉滨,尚且对督宪多所掣肘。若去京师是非涡中,势必动辄得咎,进退失据。”
张之洞诚恳道:“兄弟愚见与老兄有异。督抚同城对巡抚确有局限,变动看似不利,实则为兄解脱。此去京师,即不升用,做一侍郎,也能办事。”谭继洵摇着头:“别说侍郎,就是尚书又有何用?在这一点上,我愿认同孽子的看法,他说我朝各官皆不办事。我比你痴长五岁,对于功名,安于淡泊。放不下者惟有孽子,托请贤弟代为设法,能把他逐出京师才好。”
张之洞沉吟道:“你的心思我明白,然而恐怕做不到。军机进用,如日中天,连刚毅辈都敛手屏息,谁能逐之?”谭继洵哼了哼:“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懂?四卿只有皇上信用,皇上有谁信用?所谓孤立无援,何待明眼人洞见。我给孽子连发三信,要他速归。回信顾左右而言他,当然,无人施以援手,他也无力挣脱。所以我才求你帮忙,如今有力者,除你无二人。”
张之洞不能无所感动:“有可怜父母,无可怜儿子,信哉斯言!请老兄假我以时日,看其中是否有可通融处。不过,我不敢许以诺言,你得有落空的准备。”谭继洵千恩万谢,一边上奏请假,待准假后再行返湘。
湘中的陈宝箴,也正陷身于烦恼中。自从皮锡瑞被挤赴赣,黄、谭奉命晋京,熊希龄也应召离湘,湖南的诸般新政,已被王、叶等人打消大半。时务学堂长期放假,南学会不再开会,对《湘学报》的管束也更严格,以免贻人口实。他自知居于守势,暗中咬紧牙关,能保住一块是一块。可是处于三方挤压中,如何能够立定脚跟?所谓三方,一是张之洞,二是康有为,三是湖南的卫道士。新与旧争,旧为新敌,而对于陈宝箴,新党嫌他旧,旧党怪他新,各方都挑他的毛病。邵阳举人曾廉大举攻康,将湖南党争引入北京,他也被隐约指为罪魁。宋伯鲁参劾谭钟麟,光绪指派他去查办,更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不过,派邻省长吏调查参案,结果多是不了了之。
陈宝箴想起一桩先例:几年前,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指责他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架设电报线引发民愤。朝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彻查。刘坤一的彻查法,就是派遣属吏到湖北走了一趟。其间收到时任湖北按察使陈宝箴的来信,替张之洞剖白辩护。然后又有一湖北知府因公去南京,刘坤一与其亲谈一次。该知府说张大人光明磊落,所有开矿等事,银钱都在本地方用,百姓个个沾光。铁厂规模宏大,工程结实,连洋人都为之惊叹,公评为超过北洋。刘坤一也说了实话,我不派人细查,并非要讲客气,只因公事面子如此。若欲逐件考求,则谕旨并非派我验收工程;欲逐款查账,则谕旨并未派我办理报销。公事只问是非,煤铁为中国开自有之利,立自强之基,香帅勇于任事,力为其难,若再苛求,岂不寒任事者之心。我此次复奏,只就大处着墨,决不令香帅为难。
刘坤一上奏为张之洞开脱,只将罪责推到一名小官身上。候补知州赵凤昌因此被革职,随后摇身一变,成为“坐沪”探子。这一回,陈宝箴也得如法炮制,不仅“公事面子如此”,还要顾邻省的里子,粤与湘哪能老死不相往来呢?陈宝箴派员去广东走了一趟,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奏复。
陈宝箴很清楚,他办的这趟差,会叫康有为不高兴。他不去迎合康党,只因他不喜欢康有为的做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国家大事,岂能以口舌了之,以皮毛附之?皇上对康有为言听计从,固然由于身边无人,可也失于轻躁,狃于偏执。康有为百方谋求进用,迄无寸进,据传他改弦易辙,打算推举黄遵宪入枢。而黄遵宪查办《时务报》,已经得罪了张之洞,在此危险当口,怎敢贸然进京,去做飞蛾扑火?为今之计,应该搜罗人才,作为皇上羽翼,改变孤立之势。
陈宝箴上奏两份保单,其一保举本省官员,其二保举京外贤员。本省的且不说,他举荐的外省官员共有十七名,大多出自张之洞门下,如杨锐、刘光第、王秉恩、恽祖祁等。名列第一的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本是张之洞的清流好友,与张佩纶同时获罪革职,张之洞屡保而未获起用。光绪一向重视陈宝箴的保荐,此次两单三十二人,下旨宣召十五人,陈宝琛也在其中。张之洞特意致电祝贺:“福州陈阁学:奉旨赐对,欣喜无可言喻。鄙人屡请不获,今竟得之于义宁,快极。何日北上,务电示。”义宁是陈宝箴的籍贯。“义宁”此举,令张之洞欣庆,却让康有为失望。
陈宝箴与张之洞沆瀣一气,常常有意无意地与康党作对,已使康有为忍无可忍。一气之下,他便要找人揭参陈宝箴。梁启超劝告老师,不管论品行,还是论见识,陈宝箴都堪称大吏中的贤者。对其痛下辣手,不仅树一新敌,更将失一后盾,恐非我党之幸。他说得很有道理,然若听之任之,则张党将取代康党,在皇帝耳边絮叨。清流健将之笔,比旧派的陈词滥调利得多啊!恰在这时,户部小京官邢汝霖,由本部堂官代递条陈,参陈宝箴滥保欧阳霖,称欧阳霖前在河南做官,为河南州县中贪酷最著之员。同时附片参欧阳霖的,还有工部主事暴翔云。由此可见,陈宝箴的保举确有可指摘处,适宜康有为借题发挥。
康有为拟定《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新进甄别宜严折》,请杨深秀代为递上。接连有人参劾欧阳霖,则此人操守可想而知。欧阳霖无足轻重,陈宝箴为柱石之臣,为何轻率作保?光绪览奏生疑,久久难下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