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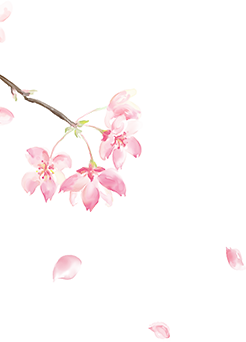
 国子监与《石鼓记》
国子监与《石鼓记》
康熙十年(1671),十八岁的成德学术生涯与人生经历都迎来一个极大的转机。
在这一年,成德“补诸生,贡入太学”。
所谓诸生,指经考试录取,进入中央、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所谓太学,在清代指国子监。
国子监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是国家管理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也是国家最高学府。关于清代国子监,《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道:
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
国子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可谓藏龙卧虎,成德可以学习、交往的对象,自然比在八旗官学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成德入国子监,其时,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为昆山人徐元文。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系清初著名大儒顾炎武外甥,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名。其兄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其弟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探花,顺治帝称徐元文为“佳状元”,赐冠带、蟒服、乘御马等,授翰林院修撰。康熙九年(1671),升任国子监祭酒。
徐元文对国子监的教学抓得很严。康熙皇帝称赞他说,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人人敬畏,其后祭酒不能及。
徐元文对成德印象颇好,按照徐元文兄长徐乾学的说法:“余弟立斋为祭酒,深器重之,谓余曰:‘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

之所以称成德的父亲明珠为“司马公”,是因为至康熙十一年(1672),明珠已经改任兵部尚书。徐元文对长兄称此,当在十一年。
“贤子”“非常人”五个字道尽徐元文对成德、国子监诸生的印象,成德之能卓尔不群,固然早露迹象。
国子监戟门内陈列石鼓十个,大小径尺,系先秦时代遗物,石鼓上刻上古文字,内容多写狩猎事情,故亦名《猎碣》。
成德在国子监学习,每每见之,心多感慨,遂考其历史、争议,并加以辨析——宋以后,学人重金石,以佐证历史研究,久而成风,作《石鼓记》一篇,云:
予每过成钧,徘徊石鼓间,辄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仅存者。”
远方儒生或未多见,身在辇毂,时时摩挲其下,岂非至幸?
惜其至唐始显,而遂致疑议之纷纷也。
《元和志》云:“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史籀之所为作也。”
自贞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议者;迨欧阳文忠,则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难独存。
夫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以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而宣王未必远狩丰西。今搜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传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一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校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抚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至国学。”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俱存无伪焉。
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百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陇田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胶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奇目异之玩者哉?!
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人嗜古者。
文中涉及人物颇多,稍加注释。
史籀,周宣王时为史官,善书。苏勉,唐贞观时人,曾任吏部侍郎。虞永兴,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因功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褚河南,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因功封河南郡公。欧阳率更,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曾任率更令。李嗣真,唐代著名书画家。张怀瓘,唐代著名书法家,生活于开元年间。韦苏州,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韩昌黎,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署“昌黎”郡望。欧阳文忠,北宋著名散文家、金石家欧阳修,谥“文忠”。
岣嵝,南岳衡山72峰之一,为衡山主峰,故衡山一名岣嵝山。古代传说,禹曾在此得金简玉书。岳麓,南岳衡山72峰最后一峰。
程大昌,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累官至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温彦威,宋代诗人。马定国,金国诗人。刘仁本,元末诗人。皆曾著文论石鼓真伪。
斯、冰、邕、瑗,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李斯(秦)、李阳冰(唐)、蔡邕、崔瑗(东汉)。郑夹漈,南宋著名学者郑樵,居夹漈山。王顺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字顺伯。向传师,北宋金石学家。
由此,可见成德之读书丰富并头脑之清晰。
实际上,清代康雍乾时代的学术风气即是如此,即博学、考据、辨析。知识二字,固然先知后识,不可或缺。
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风气,既是清初知识界反思明末士人束书不读、空谈误国带来的弊病,又是宋明理学以思辨代替考据学术发展的必然返归,因而,清代学术界力图回到原典、回到圣人原意,成就自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