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人一定有的。不一定叫荷马,但这个人就是荷马。
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最伟大的诗人是瞎子。上帝的作品: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
说到这儿,要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
很静。一点声音没有。好像天然习惯,每次迟十五分钟。
今天介绍希腊史诗。史诗又牵涉神话。诸位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读史诗。西谚曰:人人知道荷马,谁读过荷马?
这层象征很有意义: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在座谁读过《伊利亚特》?《奥德赛》?(座中只有王纪凡举手,二十岁,薄茵萍女士的公子,在美国受教育)。大陆来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读过。中国有极好的译本。
荷马是被架空的诗人。世界四大诗人,荷马为首(Homer,古希腊)、但丁(Dante Alighieri,意大利)、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英国)、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德国)——现在我们假定有荷马。荷马留下两部书:《伊利亚特》( Iliad )(阳刚),《奥德赛》( Odyssey )(阴柔)。
《伊利亚特》——漫长的战争。
《奥德赛》——漫长的奇迹。
到后世成了经典。
在中国,《诗经》本来不是“经”,后来成了经典。《离骚》,后世称“离骚经”。西方也如此。
中国常有“诗曰”,其诗本来写的是爱情,然而后世奉为“经”。皇帝听说是“经”,也得买诗的账。《圣经》也是一些故事,后来成了经典。
古希腊人称荷马是诗人,诗人就是荷马。中国人称孔丘为“子”。开口“子曰”,“孔”也不称。欧洲人称新旧约为“书”。
诗人、子、书,是最高尊称。
荷马位置这么高,有缘由的。西方人说,如果没有荷马,此后不会有但丁、维吉尔(Virgil)、弥尔顿(John Milton)。这两部史诗的影响,永久,伟大。试想,如果荷马瞎了,一时恼火,跳海死,既谈不上壮烈牺牲,也没留下诗。
所以说,不死而殉道,比死而殉道,难得多。
希腊史诗中的奥德修斯(Odysseus,拉丁名为尤利西斯)代表智慧、谋略,海伦(Hellen)代表美。
古代有游吟诗人、行吟诗人。可能不识字,能唱,能弹,唱的都是历史故事。景象仿佛天造地设,非如此不可:荷马,多胡子,瞎,一村一村游唱。当时游吟诗人多极了,荷马最优秀,其他诗人被历史淘汰了。
晋书法家不知凡几,历史唯剩王羲之。
而最伟大的诗人是瞎子。上帝的作品: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
《伊利亚特》,叙特洛伊战争的故事(Trojan War)。
话说帕琉斯(Peleus)与忒提斯(Thetis)结婚时,大宴众神,唯独没有请女神厄里斯(Eris,聚合与分离的主宰)。厄里斯大怒,出毒计报复,以阳谋出:在金苹果上刻“献给最美丽的人”,投向宴席。众人抢,三女神(朱诺、雅典娜、维纳斯)相争。宙斯说,女人之美,得由男人评。当时最美的男子是王子帕里斯(Paris,一译作巴黎)。三女神前往接受评价,朱诺对王子说:然,给你荣耀;雅典娜说:然,给你财产;维纳斯笑而不答,最后说:然,给你情人。
王子大悦,指维纳斯最美,维纳斯得金苹果。从此,朱诺、雅典娜成了王子的敌人,长期争斗开始。
维纳斯既允王子得情人,就请王子去斯巴达国,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不知来意,盛情款待。王后是海伦,绝美,与王子一见钟情,私奔,同归特洛伊(Troy)。墨涅拉俄斯大怒,与其兄阿伽门农(Agamemnon)征集希腊各邦军队,兴师讨伐特洛伊,誓言夺回海伦。义师既发,各邦将领如阿喀琉斯(Achilles)、奥德修斯(Odysseus)、狄俄墨得斯(Diomedes)、阿琪克斯(Ajax)等都率领军队前来参战。希腊军的统帅是阿伽门农,率军团团围困特洛伊。特洛伊方面的首领是帕里斯的哥哥赫克托尔(Hector)。
天神也分两派:朱诺、雅典娜,帮希腊一边;战神玛尔斯(Mars)等,帮特洛伊一边;宙斯、阿波罗,中立。
战争持续九年。九年后,起内讧——史诗自此而始。
这一构思非常巧妙:希腊军内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起了冲突,奥德修斯的故事以此开始:史诗凡二十四卷,是二十四天之间的战争纪实,叙述中心,是阿喀琉斯的愤怒——九年切开,仅写这一层。
战争是兽性的暴露。
希腊军围困特洛伊城时,纷纷掠劫财宝和女人。其中抢到阿波罗庙祭司的女儿,给了墨涅拉俄斯的兄弟阿伽门农。祭司请阿波罗降瘟疫给希腊军。抢女人不均,最高将领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起冲突。阿喀琉斯退出战争,无人可替代他。他要求母亲向女神求力量,对情敌阿伽门农报仇。宙斯请梦神托梦阿伽门农出阵。王子帕里斯出来观战。
墨涅拉俄斯、帕里斯单骑争斗,两军退息,观战,决胜负。
海伦也上城头观战,双方士兵首次见到海伦,惊为天人,都觉得九年战争值得。
(插叙:但丁往选美,出六十多美人,编号,最后说:不要排名,最末一名放到第一名,也一样美——这是诗人的说法)
王子败。希腊要求海伦复归,王子赖账,战争复起。
阿喀琉斯退战,希腊方面缺将而弱。阿伽门农礼请,奥德修斯说项,阿喀琉斯均不允。其中一席话,是荷马演说的极峰,在史诗中最有名。
中国古代名将乐毅《报燕王书》,响当当,也是退将拒绝之词。
但阿喀琉斯出借自己的铠甲战车给战友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us),友上阵后,旋败。阿喀琉斯闻知好友亡,战车失,狂怒而起,其母求伏尔坎连夜铸做新铠甲,叙写铠甲的文字,也是荷马诗最著名的一段,极富考证价值。在古代,盔甲、战车、盾牌,极重要。希腊史诗中大量篇幅描写当时的武器。出土文物证明是对的。
阿喀琉斯披戴新盔甲,以“哀兵难敌”之慨,冲向特洛伊城。起初赫克托尔避而不战,后与之交锋,不敌,奔逃,阿喀琉斯紧追,绕城数匝。天上众神俯瞰战局,在金天平放砝码两枚,一代表阿喀琉斯,一代表赫克托尔,眼看赫克托尔砝码下沉,必败无疑。果然,赫克托尔死,阿喀琉斯不退还其尸,置战车后拖拽,耀武扬威。赫克托尔妻安德罗玛刻(Andromache)在城头看见,悲痛欲绝,跳下,死。死者父亲哀求,尸体终于运回。阿喀琉斯为其战友帕特罗克勒斯办葬礼——至此,史诗结束。
荷马高超。起篇奇,收束也奇——到底有没有荷马呢?如果没有荷马,又是谁写的呢?
(提要——王子抢海伦,丈夫开战,众神参战,希腊军内讧,阿喀琉斯退战,请战,阿喀琉斯请其友出,死,为战友复仇,阿喀琉斯亲往战,胜,回来葬友)
其中以海伦上城头,阿喀琉斯回拒,王子赖誓,都是精彩的部分。
特洛伊木马,不在《伊利亚特》篇,阿喀琉斯战死,也不在《伊利亚特》篇,而在《奥德赛》篇。《伊利亚特》阳刚,是写给男性看的,类《三国》、《水浒》。如有人能以诗的形式改写《三国演义》,或不输《荷马史诗》,但改写者必须具有荷马的天才——世界各大国、各大族,历史都很丰富悲壮,然而伟大的诗才太少了。以此,中国没有史诗。
《奥德赛》叙述特洛伊城陷落,希腊全胜之后。海伦回来了,其他英雄陆续回归。独有奥德修斯在归途中历经各地,多年后,漂流回家。
没有暴烈的战争,没有震撼人心的描写,《奥德赛》是女性的,温和的,富人情味。因此有人判断《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写于两个时代,后者在较后的较文明时期;但也有人坚称二者皆出于荷马,前者是诗人生活颠簸激烈时所作,后者是静穆的晚年所作;又有人认为,《伊利亚特》是男性写的,《奥德赛》是女性写的。
我都不太信服。这两部史诗都是二十四卷。《奥德赛》分得更细致,六部,每部四卷,共二十四卷。
首部,叙奥德修斯家,妻子久等,丈夫不归,求婚者纷至,难以应付,儿子出往寻父。
二部,叙述奥德修斯离了仙女卡吕普索(Calypso)到海王国(Sea Kings)。
三部,写在海王国,奥德修斯讲述从前的冒险故事。
四部,回到伊萨卡(Ithaca)地方,与子相会。
五部,奥德修斯假扮乞丐,回家,使人不识,可用智谋。
六部,与子联合,杀求婚者,与妻复合。
鉴于大家都忙,且要忙到老,不能详谈荷马史诗,只略述一遍。
众神聚会,波塞冬不在。奥德修斯曾杀波塞冬之子,故波塞冬不来。雅典娜求情,请他让奥德修斯回,但问题是奥德修斯在仙岛上与卡吕普索仙女爱,不舍他回,故先得说服仙女放奥德修斯。
其时,奥德修斯家求婚者不绝,在他家饮酒欢乐,几耗尽家产。雅典娜神变成奥德修斯家老友,怂恿奥德修斯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寻父。子问父友墨涅拉俄斯,墨涅拉俄斯款待忒勒马科斯,见海伦在场,谈起当年战争,是一美妙段落。墨涅拉俄斯告诉奥德修斯之子其父在何处。
其时仙女已放走奥德修斯,奥德修斯造木筏,出海,上归途,眼见中途必经海王国,被海神波塞冬遇见,波塞冬怒其不归,使木筏碎,奥德修斯落海,两昼夜后浮到海王国。
雅典娜又求海王国公主救奥德修斯,公主救,善待,国王看重奥德修斯,款待,饮酒,听歌,唱到特洛伊战争(写法高明),唱到木马攻城(此时点出奥德修斯当时用木马计),奥德修斯感动下泪。王诧怪,问何故,奥德修斯告知自己是谁,趁此说出十年漂泊经历(手法高明,收放自如)。
奥德修斯说,他和他的同伴被风浮到某地,国人仅食莲花,外人吃,即失记忆。奥德修斯不食。又到塞力斯国(Cyclops),国不耕种,互不相助,食野果。奥德修斯又到一岛,岛无船,岛中人从未到过异地。又遇一独眼巨人,食人,巨人实为波塞冬之子。奥德修斯以酒灌醉巨人,盲其另一眼,抱羊逃出。
巨人求其父报仇。
奥德修斯至埃俄洛斯(Aeolus)所住的岛,四周铜墙围,岛主好客,临别有礼,皮袋,容世间各种风。主称:仅留西风,送汝归。
数日,祖国在望,奥德修斯喜。略松神,瞌睡,随从好奇,想看袋中何物,风乃出,船乱,奥德修斯醒,已不可控。
到女神喀耳刻(Circe)所在的地方,女神有魔法。奥德修斯留船上,其余随从上岸,观女神屋,周围有百兽,驯良。女神好客,以酒待客,饮酒后,皆成猪,唯领队慢饮,未成猪,逃回,告奥德修斯。奥德修斯设计救,找到赫尔墨斯神(Hermes),神给奥德修斯黑茎白花,使奥德修斯持往女神家,不会变猪。奥德修斯往,喀耳刻知,善待,以二十一猪返人形,还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索性住下,一年,或与女神有爱。
奥德修斯往死国。该国有先知。奥德修斯见了已死的母亲,又见特洛伊战争中死去的诸将,又谈战争。
后奥德修斯又离开死国,回喀耳刻处,女神告知旅途,别。途中遇岛,有歌者,闻歌而不思归。奥德修斯越歌岛而去,遇窄谷,一边有漩涡,另一边有海妖斯库拉(Scylla)住着,入漩涡,船没,不入漩涡,被妖吃。奥德修斯自知不敌漩涡,试敌妖。可是六个水手被妖逮,越逮,奥德修斯越逃,听身后六水手呼唤其名,奥德修斯以为所有艰难中此处最悲伤:见死而不得救。
过海峡,至美丽岛,有神牛,奥德修斯同伴饥饿,宰神牛食。宙斯要惩罚杀牛者,雷电交加,众人淹死,唯剩奥德修斯。
漂流十天,到卡吕普索岛(仙女岛),直到后来仙女使他走……国王听完故事,造船送奥德修斯回家。
奥德修斯回家前,先已从儿子处得知家中求婚者众,闹,于是装扮成乞丐,无人识。仅家中老狗嗅出,兴奋,狗死。乞丐受百般凌辱,然奥德修斯明白其妻忠诚,乃团圆,同往拜老父,从此和平——《奥德赛》故事至此结束。
我的观点:
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古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好的,用这种手法看其他文学,凡大品,都无赘述——近世的文学描写,太赘——所谓“大手笔”、“史诗式”,就是这个意思吧,希腊传统正是最佳典范。
其次,荷马史诗的“神”与“人”,既有性格上的相通,又有凡尘和天庭的差异,这差异分明是诗人设计的,然而极令人信服。这是希腊传统又一个好典范,至今值得体会、借镜。
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
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荷马喜用“Similes”(简洁的比喻),极直接,不深奥,不暗示,也成了传统。后来的维吉尔、弥尔顿等史诗家都袭用简洁的比喻。有人统计《伊利亚特》的直喻共一百八十多处,《奥德赛》四十多处。
如形容希腊奔赴前进,如大火吞没森林;匆忙的声音,如群鸟噪音;军队聒噪时,如苍蝇飞鸣;军败退时,如羊群奔散。以狮比猛将(三十多次),如此,史诗显得辉煌。
荷马史诗不仅是文学,而且是文献。近世,希腊与周边国家发现荷马所写的城邑、器物,均分批出土,迈锡尼(Mycenae)发现了城墙与城门,还有国王的寝陵。殉葬器中,竟有《奥德赛》所记奥德修斯用过的金胸针,都与史诗所载相符,可见真实性。连阿喀琉斯的战车、盾牌,都找到了。特洛伊所在的海边发现了《奥德赛》所写的海王国,有弘丽宫殿的残迹。由此断定,史诗非虚构,而是实迹记载。荷马,是根据人类的世界而创造了一个荷马的世界。
扯远一点。
西方有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被我们称为唯心史观。克罗齐提出历史与艺术有相似性。他说:
一,艺术不是抒发官能快感的媒介。
二,也不是自然事实的呈现。
三,也不是形式关系系统的架构与享受。
他说,艺术是个体性的自觉的想象。艺术家观察并呈现这种个体性。艺术不是情绪的活动,而是认知的活动。科学和艺术相反,科学要认知的是“普遍”,要建构的是一般性概念。科学之间,概念之间,要厘定它。
历史关心的是具体个别的事实。所以,要仔细对待事实,叙述事实,找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找出事实之间的关系。根据克罗齐的说法,历史并不在于理解它的客体(对象),而仅止于凝想那个客体,这种凝想、凝视、凝思,正是艺术家命定要来从事的活动——重复我的意思:就是那耳喀索斯的活动——唯物史观要把历史归入科学概念,连串“事实”似乎专为辩证法推论存在,完全无视“个体性”,只要普遍性,而历史、艺术要具体性、个别性。
历史不属于科学的概念范畴,属于艺术的概念范畴。
历史是要对客观思考、凝视,非旨在理解。这也正是艺术的课题。
我不完全同意克罗齐的观点,但部分是对的。唯物史观把历史拉到科学,克罗齐把历史拉回艺术。唯物史论把历史看成规律性,不看到个体性,起初即错。历史的个体性只可做凝视、观照,不可做成规律性。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回到荷马,是对历史细碎性的凝想,故史诗成为历史与艺术的理想结合。克罗齐之说,近乎荷马史诗。
是否因荷马的方法,历史、艺术两个概念可以等同起来呢?
对于太多艺术家气息的历史学家,我遗憾:何不去弄艺术?反之,考据气盛的人,我也反对。最理想是司马迁。他是历史学家,有文学才能,但不多用,他知道。
鲁迅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好!
“史家之绝唱”,即历史真实性,是对客体的观察、凝想。“无韵之离骚”,即艺术的真实性。《史记》中最上乘、最精彩的几篇,恰好合一,双重连接了这个标准,如《项羽本纪》。
说到这儿,要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再看鲁迅之评,过誉一些。
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
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
考证《红楼梦》,错,是当历史学家去了。然蔡元培以“想当然”考证,又大错了。历史与艺术,追求真实,但追求的方法、表现的方法均不同。
克罗齐的科学概念,是常识。但他对历史与艺术的见解,还有待说。普遍性还是要有,但不是苏联说的“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产生公式化)。我既不认同历史和艺术的纯个体性,又反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克罗齐的“个体性”不能完全排除“普遍性”。史家、艺术家,一定要从不可分的普遍性的东西中分出来。史家分出个体性,还得放进普遍性。艺术家分出个体性,不必再到普遍性。
这是我的意见。
回到史诗。荷马不用文字,是口传,是有人记载加工的。直到公元前500年,乃正式成为文字记载。此事不知是谁做的。
“伊利亚特”,当然是音译,意思是:一系列的战绩。
“奥德赛”,意思是:漫长而曲折的旅程。
荷马,是“零片集合者”的意思(Piecer-together),如此,荷马的形象不见了。殊憾。四大诗人中,老大不见了。我很伤心。正伤心,英国有人说,荷马真有其人。直到德国,歌德、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都坚信确有荷马其人,正合我的心态。席勒脾气大,骂了胡尔弗(Wolf),因为胡尔弗认为荷马只是个口头的初稿者。席勒说,你不认,是野蛮人!
他们论据何在,不得知。
我们直接读原书,巧妙的连续,完美的结合,实在像出于一个人。这人一定有的。不一定叫荷马,但这个人就是荷马。
你们以后读荷马史诗,悄悄注意:每次战后,都描写大吃大喝。希腊人真是健全、诚实,吃饱喝足才能打仗呀,打九年哪,不吃不喝怎么打得动。假如中国也有史诗,恐怕不会像荷马那样去写吃喝的。今天我们讲课到薄家、丁家,课中休息,有吃喝,此乃“史诗风格”。
美术史,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

民国版《希腊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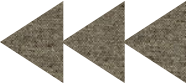
再想下去,那时候地球上出现许多天才,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思想,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压根儿不知道老子、孔子、释迦牟尼。
以相貌、风度论,老子、释迦也比较漂亮潇洒。可怜老子、释迦,当时也一点不知希腊神话,没有读过荷马史诗。
他离开宫殿,是伊卡洛斯之始:他的王宫,就是迷楼,半夜里飞出来,世界又是迷楼,要飞出世界,难了,但他还是飞了出来,最后发现生命本身就是迷楼。所谓三藐三菩提。他伟大,悟到生命之轮回,于是他逃避轮回。
我们出自老子故乡,又和乔达摩的故乡印度为邻,为什么还是视希腊为精神故乡?
最了不起的,是希腊将“美”在人道中推到第一位,这是希腊人的集体潜意识。这种朴素的唯美主义,不标榜的。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而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
想和前几次来个颠倒。此前先说文学,再说观点,今天一反,先说观点。
文学与绘画的艺术家,小时候听到希腊,都震动着迷。这是艺术家精神上的情结,恋母情结。
希腊伟大,但希腊是个小国家,人口少,面积小。然而,产生了至今无与伦比的伟大艺术,弘丽,高洁。文学、雕刻、建筑,可说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数学、哲学,是人类文化的奠基。西方评价:除了基督教,希腊文化是世界文化可以夸耀的一切的起始。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说:希腊是人类的永久教师。
希腊小,但有相当长时期酝酿文化。荷马生于纪元前八九百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死于公元前三百余年,荷马是开山祖,亚里士多德是集大成,共历五百年。
我们是中国人,一定会想,那时候中国如何?那时中国也正伟大,天才降生——公元前八百年,世界是这样的!
中国呢,李聃(聃,音丹)比荷马迟一百年出生,约纪元前七百年(一说纪元前五百余年)。孔丘比耶稣早五百五十年出生。墨翟比孔丘小几十年。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生于公元前五百余年,比孔丘大几岁。
当年希腊正在造宇殿,起塑像,唱歌,跳舞,饮酒,中国正在吵吵闹闹,百家争鸣,而印度正在吃食,绝食,等等。他们彼此不知道,在这同一个世界还有另外的辉煌文化。
在座今后称文化名人,要有分寸。老子、孔子,是尊称,也可称其名。该有尊称。
这时代,地球上出现那么多人物、天才,彼此不知道。所以古代的智慧毕竟有限。我以为所谓智慧,指的是现代智慧。再想下去,那时候地球上出现许多天才,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思想,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压根儿不知道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到晚期,好像有点疯了,到处去问:世上谁是最智慧的?因此获罪而死。如果他问到李聃,他的智慧我以为不如李聃。李聃、乔达摩,论智慧,应在苏格拉底之上。苏格拉底以希腊之心,问世界之大。他再问,只能问到希腊。
以相貌、风度论,老子、释迦也比较漂亮潇洒。可怜老子、释迦,当时也一点不知希腊神话,没有读过荷马史诗。谈到李聃,李聃是非常自恋的,是老牌那耳喀索斯。但不是如那耳喀索斯以泉水照自己,而是以全宇宙观照。他照见的是道。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乔达摩,他是非常伊卡洛斯。他是王子,宫中美人多。他上街,看见人民,方知人生有病、有孕、有死亡。如此快乐的王子,看到生老病死,明白人生无意义。夜里看见宫女睡态之丑,他离开宫殿,是伊卡洛斯之始:他的王宫,就是迷楼,半夜里飞出来,世界又是迷楼,要飞出世界,难了,但他还是飞了出来,最后发现生命本身就是迷楼。所谓三藐三菩提。他伟大,悟到生命之轮回,于是他逃避轮回。
我对古人的崇敬,世界范围说,就是这两位。第三位是晚七百年再来的。他是老三,他是耶稣。
老子大哥,乔达摩老二,耶稣是小弟。这小弟来势非凡,世界都被他感动。
然而希腊的酒神精神,最符合艺术家性格。我们出自老子故乡,又和乔达摩的故乡印度为邻,为什么还是视希腊为精神故乡?
讲希腊三次了。希腊是我心中的情结。这情结,是对希腊的“乡愿”。
我是个宿命的唯美主义,瞧不起英国黄皮丛书派的唯美主义,认为王尔德是纨绔子弟,不懂美。春秋战国的血腥和混乱,我受不了,印度人不讲卫生,脏不可耐。而中国的思辨,印度的参悟,还不及希腊的酒神精神更合我的心意。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希腊的得天独厚,是正确、有力、美妙的文字,表达了不朽的思想。从前有一说:诗人不宜多知世事。希腊整个文化艺术像是一个童贞的美少年。想起希腊,好像那里一天到晚都是早晨、空气清凉新鲜。整个希腊,是欧洲觉醒前的曙光,五百年光景,是西方史上突然照亮的强光。当时,周围的波斯、土耳其,还很野蛮。
我的老调:希腊是偶然的希腊、空前的希腊、绝后的希腊,希腊的现在,已糟糕。
希腊神话、史诗,匆匆讲过,今天说一说希腊悲剧,然后罗马文学也趁势交代一番——再下去就是“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要和耶稣在一起,很兴奋,也有点难为情,大家有这种又高兴又害羞的感觉吗,下次要去见耶稣。
正式观点:
多神→泛神→无神
此中规律,世界如此。而一神,很难通向泛神,因此不可能无神。所以,希腊诸神今已消失了。叔本华说,泛神论即客客气气的无神论。
而基督教(一神)至今不灭,不可能通向泛神。
即此说明,希腊精神是健康的。一开始,他们的诸神之上就有命运。从国君到国民,心照不宣地将命运置于诸神之上。希腊的潜意识,是无神。我的公式,再挑明如下:
多神(命运)→泛神→(观念)→无神(哲思)
希腊之所以活泼健康,是他们早在神的多元性上,伏下了无神论的观念。此所以尼采无比向往希腊。文艺复兴,似乎复的是基督教之宗教,其实复的是希腊精神。希腊精神是他们在宗教画中大量夹带的私货。
希腊悲剧的通识与基调,是一切都无法抵抗命运。
为什么希腊悲剧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中国人不知此。
我的看法:希腊人承认命运后,心里在打主意,怎样来对抗命运。希腊教育的总纲、格言,是殿堂门楣所刻:你要认识你自己(也可说是:尊重你自己)。这是伦理总纲,是认识论。
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既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此之谓“净化”,中国人说“通达”。“通”是认识论,“达”是方法论。“通”是观照,“达”是自为自在的。
相比,希腊人还是比我们优秀。希腊对死是正视的,对命运是正视的。正视之后,他们的态度是好自为之——人道。拿人道去对抗天道,很伟大。他们聪明,认为人道可以对抗天道。
中国人想天人合一。
最了不起的,是希腊将“美”在人道中推到第一位,这是希腊人的集体潜意识。这种朴素的唯美主义,不标榜的。他们高尚。希腊是最早的唯美主义。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华而不实。
现在来谈偶像崇拜。
在中国、印度、埃及、玛雅、波斯,众神像代表权威,恐怖,要人害怕、慑服。只有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恶的众神。维纳斯、阿波罗,为什么美?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美,最后带来人格的美:勇敢,正直,战死不丢盾牌。
为什么美好?美就是快乐。
希腊没有历史负担,没有传统风俗、习惯、教条约束他们。这美少年不梦想上天堂,也不想到下地狱。多舒服。
希腊文化是现世的、现实的。他们天然地没有伤感情调。希腊的一切艺术,真实、朴素、单纯。奇怪的是,经历了那么多繁华,留下这朴素。
希腊由诸多城邦组成。城邦即国家。每一城邦数千人,临海,或是岛。雅典是最重要的城邦,不及我住的琼美卡大,城邦里上演悲剧,全城免费观看。
希腊文学,百分之八十已失去。留下的百分之二十,现藏雅典亚历山大图书馆。
希腊与波斯大战,胜。欧洲后来的爱国主义皆以战胜波斯为标志。当时,文明战胜野蛮,赞美生存,即爱国主义。
所谓希腊悲剧,即雅典戏剧。纪元前484—前431年,在这五十三年中,产生了希腊悲剧。
对照: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也就三十余年的光荣。
早期希腊戏剧,发源于崇拜神的舞蹈(祭神,每春葡萄发叶时祭酒神),再转化为悲剧。此后出大戏剧家,丰富了戏剧,名义上仍借春祭。雅典剧场:圆形,第一排是教士、祭酒的座位,酒神(似教父)在正中有特别座位,背高,大,曲臂椅。
剧场可容三万人,所有希腊国民都可以到剧场,由国家付钱。当时国君认为这是对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
剧目竞赛,演员由富翁供养,作家以剧本参加竞赛。每个作家必有自己的合唱队。赛有胜败,然在希腊不会失败。他们认为,在酒神庆典上怎能失败,故参赛三人都得奖。
当时最有名的悲剧家:
老大: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525 BC—456 BC)。
老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496 BC—406 BC)。
老三: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480 BC—406 BC)。
演出情况:最早,所有优伶在舞台与观众间的空地上表演,化妆在幕帐内。当时合唱队是全剧的灵魂。演员扮相庞大,不好看,动作慢,以说为主。面具起扩音器作用。有引子、序曲,剧中有人出来预告剧情,剧末有人扮神出来讲安慰的话,大家听候“净化”(Catharsis),散回各自生活。
埃斯库罗斯,生于公元前525年,当过兵,参过战,以战争生活入剧。首著作于二十六岁。像莎士比亚那样,在自己戏中当演员。据说共有九十多种作品,留下比较完整的有七种。
人类不能逃脱命运,不能逃脱复仇之神的追逐——这是剧的中心思想。剧情都是神话与民间传说。
据说,他少年时在葡萄园中睡熟,梦酒神,指令他写悲剧。
他的作品特点是恐怖、有力,没有恋爱故事,剧中音乐是他自己配。
他自称其作品是荷马大宴会上的几口菜。
仅存七剧本。以“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为最有名。共三篇:一,《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the Fire Bringer );二,《被囚的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Bound );三,《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Unbound )。其中以第二篇最动人(第一、第三部仅存片段),是普罗米修斯被伏尔坎囚于山顶,向天地哭诉他本是神。受刑,以鹰啄普罗米修斯胸膛,食尽五内,翌日复长成,再被鹰食。
另一本称《阿伽门农》( Agamemnon ),三联大戏。
埃斯库罗斯死于公元前约456年。相传死于在剧本竞赛中失头奖。
索福克勒斯是三者中最著名的,小埃斯库罗斯三十岁,大欧里庇得斯十五岁。他是世界文学史中最快乐的作家,形象壮健、美丽,精于体育和音乐,十六岁被选为少年歌唱队领班。歌唱时裸体,戴花环,执金琴。
成长于爱国主义热情,雅典人以伟大的光荣与喜悦对待索福克勒斯,称他为“小蜜蜂”(Attic Bee,苏格拉底的绰号是“牛虻”)。后入政界、晚年被封为大将,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福将,生在讲究道德又不主张禁欲的希腊时代,如天才一样,懂得逃,逃出热情。
产一百多种剧本,仅留七种。有《俄狄浦斯王》( Oedipus the King ),等等(古代的书名多是人名)。
索福克勒斯比前人更为人性化、人间化,从宗教热情转化到人间的合理化。他改进了演员的戏剧服装,使其华美,改进了合唱,使其丰富。不像埃斯库罗斯剧那么暴狂,比较文雅。他的晚年生活快乐,自称不知忧愁。别人称,他的冥国一定如生前般快乐。
埃斯库罗斯是刚毅的士兵,索福克勒斯快乐健康,是参与国事的名士;而欧里庇得斯是个隐士,厌恶城市、群众,在艺术上是个改革派。他生于公元前480年,二十五岁首次参加悲剧比赛,出处女作。十余年后得第一奖。后离雅典,到马其顿(马其顿最早的国王是亚历山大),终其生。马其顿国王宠欧里庇得斯,为众臣所嫉,死于谋杀,被一群野狗咬死。
欧里庇得斯生时,雅典人已不太信神。埃斯库罗斯时代神话题材正盛,索福克勒斯综合之,到欧里庇得斯,写人间普通人。后世称他为浪漫主义开山祖。
他认为神的传说是不道德的。如果真有神,不必崇拜;如果没有,希腊道德观岂非崩溃?他认为道德即美,不应赏罚是非。道德的好,乃因为美。他以性格分析见长,敏锐,尤对女性心理分析为高。
欧里庇得斯一生大概写有七十五种剧本,约十八种传世,得过五个第一奖。恶行会得恶报,这是他剧中的思想。
落落寡合,不与官方接近。而得奖多,留作品多,可见当时为人热爱接受。欧里庇得斯死时举国哀悼,名声很大。其时索福克勒斯也近死。此后,希腊悲剧时代告终。
文学史是文学家的事。
喜剧不仅引笑,还加入讽刺,对公众的愚蠢加以批评。喜剧也比赛。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生于纪元前448年,相传作品有四十四种,传世十一种——现存最早的希腊喜剧,就此十一种。
他是保守派,与革新的欧里庇得斯等是对头,责备欧里庇得斯派,不赞成英雄化。政治家、哲学家、法律家,他都讽刺。最著名作品《蛙》( The Frogs ),文笔锐利。卒于约纪元前385年。此后新喜剧起,远不如前,合唱队已失去赞助人。
现在来介绍希腊的诗人和散文家。
荷马史诗盛行期,有一位诗人叫赫西俄德(Hesiod,生卒年不详),迟荷马生一百年,不很为人知。所谓贵族、平民,在艺术家不是指出身。所谓贵族,指少数主张超人哲学的人。历史上评荷马为贵族,然荷马出身寒苦,而评赫西俄德为平民。后世有贵族化、平民化之说。
赫西俄德在取材与观念上不同于荷马,不写英雄,写农民、平民。有作品《工作与时日》( Works and Days ),反映农民生活的情景、人事,诗歌八百多段,有教训劝导,也有占卜内容。诗风滞重,时有好片断,属现实主义。荷马是浪漫主义。
赫西俄德不如荷马出名,但对后来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影响很大。另有九位诗人,其中女诗人萨福(Sappho),大名鼎鼎。一说其美,一说其矮、丑。一说其乃最早的女同性恋,一说其死于失爱。
她代人写情书:“当你打开我的信,不看到最后的名字你就不知道了吧?”
萨福与荷马齐名,但留下诗作极罕。
她出生于三位悲剧家百年之前,纪元前600年左右。被推崇为第十位缪斯(Tenth Muse),也称为“格莱女神之花”(Flower of the Graces)。评者称其每一句诗都完美。
如为渔夫写墓志铭:“将这篮,这桨,放在某某墓上,这么少啊,这个人的财产。”又如:“好像甜蜜的苹果,在最高的枝端好像有人忘了它,不,是他们采不到它。”
不过,韵事越多,名越大。我的公式:“知名度来自误解。”
没有足够的误解,就没有足够的知名度。
另两位诗人:品达(Pindar)、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他们见称于文学史,是由于后期抒情诗人的翘楚,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全希腊的。
其诗作歌颂奥林匹克的竞技者。当时的胜者,有诗人献词歌颂。所颂者,包括神或死者。品达擅长此类颂词,很坦率,很现代,称:我为自己生活,别人我不管(十足个人主义)。又如:“时间的房门开了,美丽的植物看到春天。”
西摩尼得斯比较富有原创性,写挽歌、墓志铭、凯旋歌、颂歌(颂歌向来是诗体,中国的大雅、小雅,也是颂体诗)。他也写神话,如佩耳修斯的母亲在海中遇风暴,抱婴儿哀,但心里想:风暴,黑暗,海危险,婴儿不知。心遂稍安。
会写诗。美的。
希腊散文,表现在言说、历史、哲学。
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雅典人。生于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卒。其时希腊各邦势力衰弱,马其顿虎视眈眈。德摩斯梯尼到处游说,说辞有力,激使人民抗敌(时腓力二世统治马其顿)。
历史学家,三者最有名: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484 BC—425 BC)。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460 BC—400 BC)。
色诺芬(Xenophon,约427 BC—355 BC)。
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他之生时,正是雅典战胜波斯(他本人出生于小亚细亚)。少时好旅行,著作《历史》共九卷,前六卷叙波斯、希腊国史,后三卷写希腊、波斯战争,溯及埃及史。他的史书多想象,史实有误,文笔生动。
修昔底德写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衰落),亲历战争。他不依神的观念,重事实,保持客观见解。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包括当时许多大人物的讲演。
色诺芬写过苏格拉底,不敢恭维。柏拉图写过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忙,色诺芬帮苏格拉底的倒忙。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我最赞美的传记作家(所谓传记作家,就是以史入传,如司马迁)。用希腊文。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一称《希腊罗马伟人传》(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此后影响甚巨。莎士比亚的悲剧,即多以普鲁塔克的作品为蓝本。
后世大人物多从其作品中汲取力量和灵感。他本身伟大,故写的人物光辉灿烂,又重事实。
纪元前四五世纪,雅典出三位大人物:
苏格拉底(Socrates,469 BC—399 BC),口才。
柏拉图(Plato,约427 BC—347 BC),文才。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384 BC—322 BC),全才。
这三位,长话不能短说,单是苏格拉底,我可以从现在起谈,谈到明天早上,信不信由你,谈不谈由我。由我,就暂时不谈。
生在后现代的人,如何研究这三位,实是在找真理。至今,还有真理埋没在他们身上。我不忍盗墓,愿代客盗墓,不取分文。
这三位大人物以血肉之躯去想,现代人以方法、仪器思想——苏格拉底思想时,无人敢惊动。立至天明,不动,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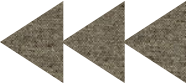
实实在在说,我之所以读佛经、读《圣经》,继之考察“禅宗”六祖,又泛泛而论探索了经院哲学,命意大致有二:一,真理有无可能;二,精神上的健美锻炼。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她字迹秀雅,文句优美。她坚持以上的论点,我则力主《新约》的文学性、思想性胜过《旧约》。
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后来我们在苏州东吴大学会面,幻想破灭。后来她转入南京神学院,信也不通了。《旧约》没有能使她爱我,《新约》没有能使我爱她。现在旧事重提,心里忽然悲伤了。毕竟我们曾在五年之中,写信、等信二百多次,一片诚心。
最符合平常心的,是个人主义。超人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升华拔萃。然而超人哲学只宜放在心里,闷声不响,超那些庸人恶人。尼采堂而皇之提出“超人”,真替他不好意思,越想越难为情。
他真正是一位绝世的天才,道德与宗教的艺术家。读四福音,便如见他立在面前。我随便走到哪里,一见耶稣像(画或雕刻)一定止步,细细看,静静想。尼采是衷心崇敬耶稣的,尼采反上帝,而奉耶稣为兄长。
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我左右为难,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本章的题目,就可看出我不可告人而已告人的心态,此人是无神论?有神论?当然,是个想信仰又信仰不了的异端,呼叫“宗教事小,信仰事大”的“假先知”。
是。我是个拙劣的、于心不忍的无神论者。
上次讲“希腊悲剧”,列过一个公式:
有神→泛神→无神
(信仰)(观念)(哲理)
今天补释“泛神”:
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讲“科学”,把宗教定性为“迷信”、“精神鸦片”。
后现代,知识界最高的代表人物悄悄主张有神论了。有神论才算时髦呢。在座没有教徒吧?恐怕对宗教不敬而远之,对任何一种教的经典,都没研究过。
回想起来,我从小最着迷两件事,你们猜猜,是什么?
是艺术和宗教。
艺术是世界性的,随便什么艺术我都接受(绍兴戏、歌仔戏不接受),宗教,只读《圣经》和佛经。我小时候曾做过和尚,法号常棣,有芒鞋袈裟,模样是非常fashion。后来又在修道院生活了一阵子,真的想研究“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抱有好奇心。
如果“文革”不发生,门户开放早二十年,我不会来纽约,而是去法国偏僻地区的修道院。
史家称中世纪为“黑暗时期”,教皇教廷对知识分子是极端仇视。宗教裁判所是迫害狂的发泄机关,但历史最俏皮、最富幽默感。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精英分子为了逃避迫害,躲起来了。躲在哪里呢?修道院里。
修道院是旋风的中心,最安静。他们读书、研究学问,最好的啤酒、葡萄酒、香水、香料,最精美的
 浆,都产于修道院。上次不是讲到“快乐主义”吗,我很想以“快乐主义者”的身份挤进修道院,和知识精英谈谈,然后,吃好菜,喝好酒。
浆,都产于修道院。上次不是讲到“快乐主义”吗,我很想以“快乐主义者”的身份挤进修道院,和知识精英谈谈,然后,吃好菜,喝好酒。
实实在在说,我之所以读佛经、读《圣经》,继之考察禅宗六祖,又泛泛而论探索了经院哲学,命意大致有二:一,真理有无可能;二,精神上的健美锻炼。
前后约计四十年,有话可说。(笑)仿孙中山辞令,易为:“余致力宗教探索,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我个人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申请出国,并联合世界上的真诚待我之朋友,共同努力,以求贯彻。”
好,现在开始讲正文。
Bible 是书,是经,是古书的总集,记载了纪元前千余年的人类史(真实性是大有问题的,也不好说是文明进步史)。而影响人类精神的势力,遍及全世界,欧洲的道德,就是宗教道德。
《圣经》全书只是一个主旨:人寻求上帝。历史、诗歌、预言、福音、书翰,都蕴着对上帝的爱。
《圣经》不是神学的总集。它没有被清理、被规范,所以庞杂,像人类生活本身,忍耐、懦弱、胜利、失败,像一个老实人的日记。作者们的热情是忠恳的,被高扬纯洁的信仰所激发,呼号哭泣,相信自己为神所派遣,来世上完成伟大的使命。
他们正直、善良、真诚、热情,所以文字明白简朴,思想直接有力,有一种灵感、一种气氛,笼罩你。我少年时一触及《圣经》,就被这种灵感和气氛吸引住。文字的简练来自内心的真诚。“我十二万分的爱你”,就不如“我爱你”。
总之《圣经》不是一部书,而是许多书的总集。
接着来分《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希伯来民族在千年间所产生的最好的文学;《新约》,不限于一国一族,而是从开始就预示着通向世界的伟大文学。从既成的论点看,凡研究历史与宗教思想者,认为《新约》较《旧约》重要,凡爱好文学者,则认为《旧约》比《新约》更可宝贵。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 Paradise Lost ),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都依据《旧约》。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她字迹秀雅,文句优美。她坚持以上的论点,我则力主《新约》的文学性、思想性胜过《旧约》。论证,是法国纪德他们一批文学家,作品的精粹全出于《新约》。
后来我们在苏州东吴大学会面,幻想破灭。再后来她转入南京神学院,信也不通了。《旧约》没有能使她爱我,《新约》没有能使我爱她。现在旧事重提,心里忽然悲伤了。毕竟我们曾在五年之中,写信、等信二百多次,一片诚心。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我的朋友认为在耶稣那时,犹太人说的希腊话已不纯粹,“四福音书”的作者虽然热诚忠恳,到底不能形成文学。《旧约》的文字与思想,天然和谐,是由于希伯来人的语言,而《新约》作者似乎都是犹太人(除了一个圣·路加),以犹太人的思想注入希腊的范畴,这种和谐就不能再有了。
我的论据:耶稣是天才诗人,他的襟怀情怀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所能限制的,他的布道充满灵感,比喻巧妙,象征的意义似浅实深,他的人格力量充沛到万世放射不尽。所以他是众人的基督,更是文学的基督。
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信里各自节引《圣经》,她引《旧约》,我引《新约》,这样倒使她也仔细读了《新约》,我也耐心把《旧约》弄清楚。现在她如果活着,已经是祖母级了,大概早已告别文学。我呢,坚持文学,坚持《新约》的文学价值高于《旧约》。纪德、王尔德,大概与我观点相同。
现在来介绍《旧约》。
我的几个家庭教师中,有一位是新潮人物。他教我读《圣经》,简称“读熟五记、四福音,就可以了”。五记是“创出利民申”,为此,当年我凑了一首五言绝句:
旧约容易记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创出利民申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新约更好办
一同四福音
到目前为止,《旧约》不敢说读过几遍,读《新约》,无论如何超过一百遍。这不是故意求纪录。比如你与一个杰出的人物交朋友,几十年交往,谈话几百次,有什么奇怪呢?而《旧约》好比是外公外婆家,我不常去,去也是为看看舅舅的儿子女儿(即《旧约》中“诗篇”“雅歌”),和外公外婆礼貌性说个三言两语而已。
埃及与巴比伦是两个文明强盛的古国,从两国的艺术、文字、思想之不同,可知其种族之不同。
在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的两大帝国之间,有一小国迦南(Cannan),即今之巴勒斯坦(Palestine)。迦南最初是归化巴比伦,后来埃及扩张领土,征服迦南。埃及衰败后,乱世中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希伯来(Hebrews)的,大受灾难,由摩西(Moses)带领,逃出埃及,回到迦南南部的沙漠间。
这些同属闪族的以色列人(Israel),占据了迦南山地,迦南人坚守平原,双方长期战争。到以色列王大卫(David)出,迦南人和以色列人才合为一个民族,希伯来文化,尤其是希伯来宗教,发旺起来,那是纪元前一千年之后。
希伯来人从什么启示了宗教观念,无法推想,凭借《圣经》,认定这个以耶和华为至尊的一神教,是经摩西传来。摩西必是极伟大的人(米开朗琪罗雕摩西,头上有角,杰出到非人),他是天然的领袖,独创了一神教(埃及人是多神教的)。摩西《十诫》( Ten Commandments )没有多神教的影响,他是个道德家、立法者,他的教训不提到死后上天堂,也不提最后审判,都是面对世界和人性,直接感发。
《旧约》五记,“创出利民申”,向来称为“法典”(The Torah),传说为摩西所作,故又称“摩西五书”(Pentateuch),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改变解说,认为是许多宗教衍变改革的结果,即许多教士相继编定的。
五记中,以“出埃及记”与摩西关系最大,故事性强,读起来有兴趣。包括摩西《十诫》,民事法律,显出古人的正直宽厚。
“创世记”是历代画家的脚本。作神话看,很壮观,但要重视其中永恒的象征意义,艺术家必须读“创世记”。
其他三记是叙祭祀献礼、民事讼诉、人际关系,你们大概没耐性读。我从前读,觉得古代人也难对付,愚蠢而复杂,行为不讲理,口头最喜欢讲道理。“利未记”有一句:“你要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整个基督教真谛,就在这句,但正是这句,问题最大。
你的邻人是什么人?他利用你的爱,损害你(佛家还要糟糕:“舍身饲虎”)。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逼人弄虚作假。
最符合平常心的,是个人主义。超人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升华拔萃。然而超人哲学只宜放在心里,闷声不响,超那些庸人恶人。尼采堂而皇之提出“超人”,真替他不好意思,越想越难为情。
说了一阵《旧约》的坏话,其实不是心里话——《旧约》是很值得读的,以色列民族是伟大的。他们经识的痛苦太大,信仰上帝是因为实在疲乏了,绝望了。
“士师记”中写,“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下面隔几节,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显得何等的混乱,笔力强极了!这是个元气淋漓的民族,亡于巴比伦四十年,被掳去的人回来时,已经老了,在故土重建圣殿,年轻人欢呼:看哪,圣殿造起来了!年老的哭号,因为他们见过被毁前的圣殿。这时有别族的人经过,取笑他们,以色列人答道:你们晓得什么,你们到这里来,无分、无权、无纪念。
另有“列王纪”中有一节绝妙,现代文学家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先知骑驴出城去,被狮子咬死了,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立在驴子旁边,人死在驴子脚下,随从者进城去报告,于是许多人赶来了,看哪,狮子立在驴子旁边,人死在驴子脚下。
狮子咬死人怎么不走开,等人看?那么多人赶来,不怕么?狮子不再咬人吗?——超现实!真正高手!古代画战争,伤的、死的,姿态优美,古人就是懂得一切讲姿态。你要永垂不朽,无穷魅力,必得讲究姿态。那只狮子、驴子、死的先知,都是姿态。
“传道书”我也特别爱读。常常文章里节引几句,好像蛋糕上的樱桃,特别性感:银链折断,金罐破裂,日色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
都是空虚,都是捕风,日光之下无新事。
我偏爱的当然是“诗篇”和“雅歌”,尤其是“雅歌”,一共只有五页。
(诵“雅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
“雅歌”美丽幽婉,温柔沁人肺腑。所罗门是一位大诗人,我写情诗就喜欢用这个调子。现代人只要忘掉现代,同样可以肝肠如火、色笑似花。“雅歌”纯粹是文学,而且异端,压根儿忘了耶和华,所以教会中人否认它们是恋爱诗,曲解为耶和华对子民的爱——谁相信呢?
“路得记”是一篇很可爱的牧歌。“约伯记”是讲人类痛苦。“箴言”、“传道书”谈智慧。其他的篇章,总称“杂著”,还有所谓“石经之书”(Apocrypha),就是《圣经》的编外作品十四篇,从略。
现在讲《新约》。
《新约》都用希腊文写的,作者马太(Saint Matthew)、马可(Mark the Evangelist)、路加(Luke the Evangelist)、约翰(John the Apostle)都是犹太人(路加可能不是),他们用的希腊文与荷马、柏拉图所用的不一样,已是纪元后通行的白话文,即希腊人谈话、写信所用者。而当时的文士仍用古典的美文。
《新约》作者采用口语化的文体,很明智,得以广为宣传。信徒都属中下层阶级,耶稣的信徒也多数来自这个阶级。他们虽然用通俗的希腊文著书,却不是大老粗。圣·保罗(St.Paul)受过完全的神学教育,类似高干子弟。
圣·路加与圣·约翰也有文才知识。其他的《新约》作者都能使用非本土语言,表白清楚完美。他们确信负有伟大使命,写得自然、直捷,保罗尤善雄辩,读他的书札,如见其人。约翰又漂亮又聪明,耶稣最宠喜。他的希腊文不纯熟,但第四福音书却最有灵性、最有爱心。“路加福音”是《新约》的最佳篇,平易、庄重、美丽。
“四福音书”的伟大,是耶稣的伟大,而恐怕耶稣也没有料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根本不是专业作家,平时从来不写文章,却创作了千古不朽的篇章。而且总起来形成一个体裁(风格),后世曾称为“圣经体”。
我的体会是,每当自己写出近乎这种体的文辞,心中光明欢乐,如登宝山,似归故乡。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文字趋近《圣经》风格会莫名其妙地安静、畅快?神秘的解释是:圣灵感召。实在的解释是:归真返朴。
《新约》弥漫着耶稣的伟大人格。他的气质、他的性情、他博大的襟怀、他强烈的热情,感动了全世界——耶稣是个奇迹,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另一回事,全世界持续两千年的感动,足够是奇迹。而且一直崇敬他,很可能将来更加崇敬,如果真有“第三波”(The Third Wave)的实现,那么钟声还是耶稣基督的钟声。
《新约》的写作,至少是在耶稣离世大约三十年后,耶稣的实际生日约是纪元前六年,上十字架的日子,有说是纪元后二十九年,有说是三十一年,总之没有到四十岁。他说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玛克(Aramaic)方言,又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
最古的“马可福音”,约在纪元后七十年,当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都死了,马可动手写。那时耶路撒冷陷落,“马可福音”的最后一小部分是失落的。现在的印本谅必是后人补了结尾,但看得出是匆匆而止。
耶稣真正是一位绝世的天才,道德与宗教的艺术家。读四福音,便如见他立在面前。我随便走到哪里,一见耶稣像(画或雕刻)一定止步,细细看,静静想。尼采是衷心崇敬耶稣的,尼采反上帝,而奉耶稣为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