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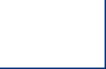
从今天的视点来看,苏联50年代上半期的文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俄苏文论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在给苏联50年代的文论定性时,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俄苏文论自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19世纪以来俄苏文论的必然发展,因此简略地回顾俄苏文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倾向及其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表明,俄苏文论的发展始终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共性,把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重内容,认为内容才是文学的本体,甚至把这种共性和关系绝对化,完全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文学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特性,反对文学成为工具,强调作家的个性,看重形式,认为形式才是文学的本体,甚至把文学形式绝对化,完全割断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上述两种倾向从19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和以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自由派为代表的“纯艺术论”的两种倾向的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从俄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认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式的哲学基础不同底结果……美学问题在双方看来,主要不过是一个战场,而斗争的对象却是对智的生活底一般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车氏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命题,并且判定“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现实比起想象来不但更生动,而且更完美。想象的形象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而且几乎总是不成功的改作”,所以,他认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
基于这样的认识,车氏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命题,并且判定“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现实比起想象来不但更生动,而且更完美。想象的形象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而且几乎总是不成功的改作”,所以,他认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
 在他的观念中,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替代品,是在现实不在眼前时的苍白的替代品。文学艺术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屈从于现实的附属品。文学艺术本身的特征被忽略了。杜勃罗留波夫也是强调“文学的主要意义是解释生活现象”,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原则,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而以自由派为代表的“纯艺术论”,则把文学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诲的批评”,上述车氏、杜氏的批评就属于“教诲的批评”,这是只顾道德上的教益,不顾艺术的特点的批评;另一种是“优美的艺术批评”,这是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在他们看来,诗的世界与平庸的散文式的现实生活是相互隔绝的,诗人只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原则,不应该为眼前的现实的利益服务。所以他们认为政治是“艺术的坟墓”,文学理论应着重“解释和阐释作家的魅力、艺术习惯、他的技巧和表现主题的特殊方式”,因为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文学面貌”。
在他的观念中,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替代品,是在现实不在眼前时的苍白的替代品。文学艺术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屈从于现实的附属品。文学艺术本身的特征被忽略了。杜勃罗留波夫也是强调“文学的主要意义是解释生活现象”,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原则,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而以自由派为代表的“纯艺术论”,则把文学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诲的批评”,上述车氏、杜氏的批评就属于“教诲的批评”,这是只顾道德上的教益,不顾艺术的特点的批评;另一种是“优美的艺术批评”,这是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在他们看来,诗的世界与平庸的散文式的现实生活是相互隔绝的,诗人只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原则,不应该为眼前的现实的利益服务。所以他们认为政治是“艺术的坟墓”,文学理论应着重“解释和阐释作家的魅力、艺术习惯、他的技巧和表现主题的特殊方式”,因为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文学面貌”。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缺乏明确的艺术形式,单独的人民性并不属于艺术,而属于民俗学”。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缺乏明确的艺术形式,单独的人民性并不属于艺术,而属于民俗学”。

19世纪末的学院派批评也出现过“文化历史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对立。文化历史学派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文化史文献,研究文学仅仅是为了了解作品所属的时代的世界观和风尚,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心理学派则特别重视作家的个性,认为创作的奥秘在于作家的个性中,艺术创作是通过语言的形象传达一定的生活感受、生活印象和想象的心理过程,艺术作品是心理的产物。因此理论研究要解释创作的心理过程,解释艺术作品的心理内涵,探讨艺术典型的审美内容和作家的审美态度。
应该说明的是,19世纪的俄国,社会处于激烈的斗争中,而文学又几乎成了表达思想的唯一手段,因此特别适合于现实主义文论和文化历史学派的发展。
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期,上述两种倾向的对立仍在继续,而且各执一端的情形更加严重。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派重视文学的特异性,他们提出“文学性”的概念,并从文学的语言层面的“陌生化”来规定文学的特性,而把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都看成是文学的外部的东西。但他们的观点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把文学看成是“经济的审美形式”、“阶级的等同物”、“阶级心理的投影”,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占了上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论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庸俗社会学的学者和“拉普”的领导人完全不顾文艺自身的特点和创作的规律,把文艺当作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和工具,文艺沦为政治的附庸。这里值得谈的是以沃隆斯基为代表的“山隘”派和以罗多夫、列列维奇等为代表的“岗位”派(拉普前身)之间所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岗位”派认为文艺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要在文艺领域划清敌我,进行“一场在政治领域那样的斗争”,他们否定过去的文学遗产,认为“以往时代的文学都渗透了剥削阶级的精神”,等等。“山隘”派却强调“文艺是对生活的认识”,突出文艺的客观性,注意文艺的特点。鲁迅对当时这两派的斗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即‘岗位’派)的人们。”
 “山隘”派很快被打下去。“拉普”的庸俗社会学错误则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文艺问题被混淆为政治问题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30年代初,又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就把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文学概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与文艺联姻的概念成为了苏联文学发展的“宪法”,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
“山隘”派很快被打下去。“拉普”的庸俗社会学错误则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文艺问题被混淆为政治问题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30年代初,又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就把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文学概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与文艺联姻的概念成为了苏联文学发展的“宪法”,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
影响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苏联50年代文论,基本上是上述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共性这种倾向的继续和发展,“纯艺术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继续受到严厉的批判,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本来在《共产主义与未来主义》一文中曾断言:“艺术总是离开生活而保持自由,在它的色彩中从来也没有反映出那飘扬在城市堡垒上空的旗子的颜色。”
 但后来一再检讨,直到1959年出版的《小说管见》一书中,60岁的什克洛夫斯基仍然在纠正20岁的什克洛夫斯基:“当时我在旗子的颜色上抬了杠,不懂得这旗子就决定了艺术。……在诗歌中旗的颜色意味着一切。旗的颜色,就是灵魂的颜色,而所谓灵魂是有第二化身的,这就是艺术。”
但后来一再检讨,直到1959年出版的《小说管见》一书中,60岁的什克洛夫斯基仍然在纠正20岁的什克洛夫斯基:“当时我在旗子的颜色上抬了杠,不懂得这旗子就决定了艺术。……在诗歌中旗的颜色意味着一切。旗的颜色,就是灵魂的颜色,而所谓灵魂是有第二化身的,这就是艺术。”
 从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到苏联50年代主流文论对形式主义文论压迫之深。而“拉普”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则被当作思想方法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相反,还得到像季摩菲耶夫这样的权威某种程度的肯定。把文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成为一条定律。一些纯文学问题被拿到苏共政治局去讨论,并作出决定,或反映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竟然大谈艺术典型问题,而且竟然认为典型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典型成为已经有了定论的政治问题,谁还敢说三道四呢?文学问题的政治化,是苏联50年代文论的一大特征。
从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到苏联50年代主流文论对形式主义文论压迫之深。而“拉普”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则被当作思想方法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相反,还得到像季摩菲耶夫这样的权威某种程度的肯定。把文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成为一条定律。一些纯文学问题被拿到苏共政治局去讨论,并作出决定,或反映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竟然大谈艺术典型问题,而且竟然认为典型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典型成为已经有了定论的政治问题,谁还敢说三道四呢?文学问题的政治化,是苏联50年代文论的一大特征。
此外就是苏联文论的哲学化问题。应该承认,50年代苏联有不少文论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文学现象,特别是用列宁的反映论来揭示文学的规律,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文学中确有一些哲学问题,需要通过哲学的视角才能得到解决。但哲学不是万能的,文论的哲学化带来的是理论的空洞化,许多文学的特殊问题在哲学化的过程中,被过分抽象化、一般化,结果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文学的本质通常被定义为“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典型通常被定义为“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真实性通常被定义为“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作品的构成通常被定义为“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所有这些定义都对,都正确,可又丝毫不解决文学自身的特殊问题。早在1956年苏联思想比较解放的文论家阿·布罗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一文中就谈过这类定义,他说:“由于这里没有充分揭示出艺术的审美特征(哲学的定义不会提出这个任务),所以这还不能算是美学的定义。”他认为,对美学和文艺学来说,“它不能仅仅用一般的哲学的方法论原理和概念来说明自己的对象。它必须揭示对象的内在的特殊的规律性,即制定自己的方法论和专门的术语”。
 文论的哲学化,导致文论仅仅沦为哲学的例证,而文学自身的问题则较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文论的哲学化,导致文论仅仅沦为哲学的例证,而文学自身的问题则较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第二,苏联50年代的文论不但是俄苏文论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且也是时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50年代是“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方面全方位对立,双方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互相抵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苏联的文论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自我孤立,自我称霸。他们当时在文化上提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对西方的文化和文论流派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没落颓废货色”,完全拒之门外。长期担任苏联领导人之一的日丹诺夫在1948年一次关于苏联音乐工作的讲话中断言说:“处在衰颓和堕落状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音乐,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所以对于处在衰颓状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音乐表示奴颜婢膝,是尤其愚蠢和可笑的。”他甚至把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现代主义统统说成“疯狂的胡闹”,
 这就完全断绝了与西方文艺流派和文论流派的来往。更可悲的是对苏联本国产生的一些优秀文论,如巴赫金的文论,也弃之如敝屣。然而,正是巴赫金在苏联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诗学,他既克服了形式主义只重视文学的语言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庸俗社会学把文学等同于政治的错误,把语言和它所表现的意义艺术地联系起来,把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结合起来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鲜、独到的观点,如他的社会学诗学、他的复调小说理论等,都是很有见地的。但在50年代,他处在社会和学术的边沿,直到70年代他的学说才为世人所瞩目,而且他的理论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比本国的影响还要大一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50年代的苏联文论受“冷战”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基本上是“冷战”时期的理论。
这就完全断绝了与西方文艺流派和文论流派的来往。更可悲的是对苏联本国产生的一些优秀文论,如巴赫金的文论,也弃之如敝屣。然而,正是巴赫金在苏联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诗学,他既克服了形式主义只重视文学的语言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庸俗社会学把文学等同于政治的错误,把语言和它所表现的意义艺术地联系起来,把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结合起来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鲜、独到的观点,如他的社会学诗学、他的复调小说理论等,都是很有见地的。但在50年代,他处在社会和学术的边沿,直到70年代他的学说才为世人所瞩目,而且他的理论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比本国的影响还要大一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50年代的苏联文论受“冷战”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基本上是“冷战”时期的理论。
苏联50年代的文论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1)重视用列宁的反映论来解释文学现象;(2)对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的肯定。前一点,使文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后一点使文学重视人的地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敢于写人的命运和情感的变化,这与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是相通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带有“左”的烙印的政治化的、哲学化的、封闭保守的文论形态,是缺少活力的文学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