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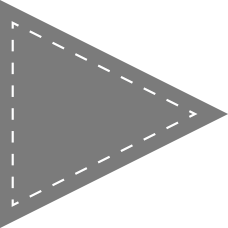 二、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
二、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
发端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模式或者文化精神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遭遇十分复杂的命运:一方面,人类理性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发达,推动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展示了文化特有的作用和力量;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人类开始遇到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即由于理性的过度发达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换言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本身开始成为问题,这也是推动文化自觉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特殊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文化在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自从人类于1500年进入近现代之后,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对于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15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虽然在这一时代,理性文化的创造性已经开始展露,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从中世纪结束到法国大革命这一“近代早期”包含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重要的内涵,但还不是人类理性精神和物质创造力充分展示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还主要体现在“市民精英的世界中”,而“在普通民众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虽然在这一时代,理性文化的创造性已经开始展露,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从中世纪结束到法国大革命这一“近代早期”包含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重要的内涵,但还不是人类理性精神和物质创造力充分展示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还主要体现在“市民精英的世界中”,而“在普通民众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相应地,近代早期技术更新和经济发展都很缓慢,“1800年前人类经济生活是一种和其他物种一样的自然经济。决定动物生活条件的因素同样决定着人类的生活状况”
。相应地,近代早期技术更新和经济发展都很缓慢,“1800年前人类经济生活是一种和其他物种一样的自然经济。决定动物生活条件的因素同样决定着人类的生活状况”
 。因此,人类处于著名的“马尔萨斯均衡”或者“马尔萨斯陷阱”,即必须依靠战争、瘟疫、灾难等手段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适应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低水平。有的经济学家断言,“1800年前,马尔萨斯均衡使得所有社会都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这似乎意味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至少自8000年前新石器革命以后的稳定农业社会以来是如此”
。因此,人类处于著名的“马尔萨斯均衡”或者“马尔萨斯陷阱”,即必须依靠战争、瘟疫、灾难等手段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适应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低水平。有的经济学家断言,“1800年前,马尔萨斯均衡使得所有社会都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这似乎意味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至少自8000年前新石器革命以后的稳定农业社会以来是如此”
 。正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自然节奏。“统治了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停滞的工业化前的世界,被1760—190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两个看似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粉碎了。其一是工业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现象源于知识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二是人口革命,也即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
。正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自然节奏。“统治了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停滞的工业化前的世界,被1760—190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两个看似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粉碎了。其一是工业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现象源于知识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二是人口革命,也即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持续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人类自觉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的理性化程度和效率空前提高、人的生活条件空前改善、人类的文化创造力和物质创造力空前展示,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程度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冲突,人类生产力并没有停滞,而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悲剧,人类还是逃过了毁灭性的劫难,并且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契约机制;匮乏状况的缓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命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等等。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自觉的理性文化的巨大创造力和自觉推动历史的作用。
但是,令我们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巨大成就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同时也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历史困境与这一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重要联系。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人类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和自我毁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欠发达和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理性文化模式时所遭遇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体验到文化无所不在的力量和重要作用。
近现代人类的文化焦虑或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它比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战争冲突、体制变革与转换都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文化合法性问题。面对具体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人们容易把它们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特别是推动近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理性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
近现代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不是人之生存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直接涉及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历史意识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危机问题。雅斯贝尔斯在公元前8至公元前2世纪找到了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轴心期”,那时形成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人性的精神化、理智、个性等“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因素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如前所述,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这种历史意识或文化精神以理性化、世俗化和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它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地位的确证。理性代表着一种善的力量,构成人的本性,因此,这是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
然而,正是这种包含着坚硬的绝对意识内核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在其自身内部就包含着冲突和张力,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和人之自由(人本精神)之间、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目的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和对立。中世纪之后所开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基本内涵是个人自由和技术理性的同步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相信两者可以同步协调发展,相信人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与自由的增强而达到自我拯救,达到完善的境界。而这一历史设计或文化信念的轴心是技术和理性。然而,就在人们的这种理解和信念中已经包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局限性,它必然导致这一文化精神或历史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裂变,导致人类行为不计后果的极端化偏向。
近现代人类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焦虑和危机,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起自身的自然性,正在并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异化和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天然联系的大都市,等等。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在最极端的形式中,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原子弹的邪恶威力、“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悲剧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之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不再简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在20世纪,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直接地、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
19世纪下半叶,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一些预言式的思想家已经以某种方式透露了人类文化精神的这一批判走向,因为他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即将到来的深刻文化危机的气息。20世纪,文化批判已不再是少数敏感思想家的独白和绝望的呐喊,而是一种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主流呼声。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人类思想和理论演进的突出标志是普遍的文化反思和批判,可以说,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批判的时代,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张力的分析,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物化现象的揭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化分析及其“生活世界”的理论药方,弗洛伊德对于现代人在普遍理性(超我)支配下的普遍的精神疾患的分析,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历史哲学家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剖析,等等。这些围绕着启蒙理性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探索构成了20世纪自觉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的重要内涵。
对于中国等后发展的国家而言,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它们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它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这些寻求现代化的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而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冲突和文化矛盾,围绕着理性主义文化而发生的矛盾和危机又以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一下子把文化问题变成了我们时代生存的焦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