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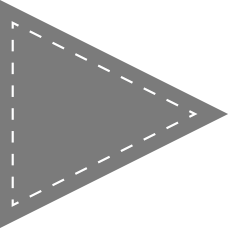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巴黎见分晓
巴黎见分晓
我讲了一个物理学的系列讲座,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Addison-Wesley Company)把它搞成了一本书。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书的封面应该弄成什么样子。我认为,因为那个讲座是真实世界和数学之间的联系,那么弄一个鼓的图画儿,在鼓的上面再弄一些数学图形——圆圈儿、直线什么的,表示从震动的鼓膜上飞出的鼓点儿,书里讨论过鼓点儿,这或许是个好主意。
书出来的时候,封面是简单的红色,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前言那儿,有一幅我打鼓的照片。我认为,他们把那照片放那儿,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想头:“作者本人希望书里什么地方有面鼓嘛。”无论如何,人人都会迷惑不解:为什么那幅我打鼓的照片出现在“费曼讲座”的前言里,因为这照片里没有什么数学图形,也没有别的点题的东西。(我喜欢打鼓,这不假,但那是另一档子事儿。)
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压力很大,没什么法子自我娱乐;没电影什么的。但我在那个以前是男子中学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鼓,于是善而藏之。洛斯阿拉莫斯在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那儿有许多印第安人的村子。因此,我就自己找乐子——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有的时候和别的家伙——只是想闹点儿动静出来,打那些鼓。我不知道什么特别的节奏,但是印第安人的鼓点儿相当简单,鼓却不错,我玩得挺高兴。
有的时候,我带着几个鼓,到远处的树林子里,免得烦扰别人。
我就用一根棍子,边打边唱。我记得,有个晚上,绕着一棵树转圈儿,一边打鼓,一边仰望月亮,假装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有一天,一个家伙来对我说:“感恩节前后,你没去树林子打鼓,是吧?”
“去了,是我打的,”
“噢!这么说,我老婆说对了!”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
一天晚上,他听到远处有鼓乐之声,就到了楼上去找另一个家伙,那个家伙也听到了。你该记得,这些家伙都是从西边来的。他们对印第安人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兴趣不小:印第安人一定在举行什么仪式,或者在做什么高兴的事儿,这两个主儿就决定过去看个究竟。
他们往前走的时候,走得越近,鼓声就越大,他们开始紧张了。他们想起印第安人多半在外围安排了放哨的,免得别人惊扰他们的仪式。于是他们匍匐在地,循迹前往,直到声音显然就在下一个山头的后面。他们爬到山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有一个印第安人,自顾自地在那儿举行仪式——绕着树跳舞,还用棍子打鼓,还唱着颂神之歌。两个家伙悄悄地屈身而退,因为他们不想惊动他:他多半是在发某种咒语什么的。
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老婆,老婆们说:“哈,一定是费曼——他喜欢打鼓。”
“别胡扯了!”两个男人说,“即使是费曼,也不会疯到那个份儿上!”
因此下个星期,他们就着手把谁是那个印第安人这事儿弄清楚。附近的印第安保留地的几个印第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于是他们就问一个在技术区当技师的印第安人,那能是谁啊。这个印第安人问了一圈儿,但别的印第安人都不知道那可能是谁,但有个印第安人是例外,没人能跟他讲话。他是个了解自己民族的印第安人:他背后有两条大辫子,头高高地昂起;无论什么时候他走到哪儿,都是高视阔步,器宇轩昂,独自一人;没人可以和他说话。走到他跟前去问点儿事儿,你会害怕的;他太威严了。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没人有胆量去跟这位印第安人打听事儿,他们断定树林子里的那位,必定是他了。(得知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位典型的印第安人,这么一位魅力十足的印第安人,一位我可能是他的印第安人,我很高兴。被人错认成他,太光荣了。)
那个问过我的伙计,心有不甘——丈夫总是乐于证明妻子不对——正如丈夫经常发现的那样,他发现他老婆说得相当对啊。
我鼓打得相当好了,有聚会的时候,我就打。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是打出点儿节奏——结果我打鼓打出了名声:在洛斯阿拉莫斯这地方,人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等战争结束,我们重返“文明”世界,在洛斯阿拉莫斯那儿的人,跟我逗乐儿说,我再也不会打鼓了,因为鼓的动静也太聒人了。还因为我想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那儿当个体面的教授,指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把我待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候买的鼓卖掉。
第二年夏天,我回到了新墨西哥州,去写报告,等我又看到了那些鼓的时候,我就技痒难耐了。我又买了个鼓,心里想:“这次我要把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可以看看它。”
到康奈尔大学那年,我的那套小单元房是在一个大楼房里。我把鼓放在那儿,只是为了看看,但是,有一天,我确实忍不住了:我说:“也罢,我只是得小声点儿敲……”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鼓夹在两腿之间,用手指头轻轻敲击:叭叭叭、叭嘟叭。然后,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儿——这也够诱惑我的了!我再大点儿声音,梆!——电话响了。
“哈喽?”
“俺是你的房东啊。是你在下面打鼓吗?”
“是;非常对不……”
“这也太好听了啊。俺能下去凑近点儿听听吗?”
从那次以后,我一打鼓,我的女房东就下楼来听。这样就无所顾忌了。从此以后,我有得玩儿了,打鼓。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比属刚果来的女士,她给了我几张为做人种学研究用的唱片。在那年头,那种唱片稀奇,上头是非洲牧牛人和其他部落的鼓乐。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牧牛人鼓手,我也经常模仿他们——模仿得不十分像,但听起来像是那么个动静——我因此也搞出了不少节奏。
有一次,我在娱乐厅,深夜,没几个人,我拿了个垃圾桶,开始敲打桶底。楼底下的一个家伙跑上来,说:“嗨!你打鼓啊!”说来说去,他才是个真懂打鼓的,他教我怎么演奏古巴手鼓(Bongo)。
音乐系有个家伙,收藏了一些非洲音乐唱片,我就到他家里打鼓。他还为我录了音,后来在他的晚会上,他玩儿一个游戏,名叫“非洲还是伊萨卡?”他放一些鼓乐,然后让大家猜,你听到的那个音乐,是在非洲大陆上弄出来的,还是本地的土产。这就是说,我那时候,相当擅长模仿非洲音乐。
等我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我经常到落日带那地方去。有一次,那儿有一群鼓手,领头的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一个大块头伙计,名叫尤卡努(Ukonu),在一个夜总会里奏的那个鼓乐,真叫妙——只有打击乐。那位副头,对我尤其好。邀请我上台和他们一起演奏点儿东西。于是我走到台上。和别的家伙们一起打了一阵子鼓。
我问副头,尤卡努可曾授课,他说,对。因此,我经常到尤卡努住处去,那地方离世纪大道(Century Boulevard)很近(那就是后来的瓦特骚乱
 发生的地方),去听打鼓的课。课上得不太有效:他四处乱转,跟别人说话,各种各样的事情时不时地来打岔儿。但等他们工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我跟他学了不少。
发生的地方),去听打鼓的课。课上得不太有效:他四处乱转,跟别人说话,各种各样的事情时不时地来打岔儿。但等他们工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我跟他学了不少。
尤卡努住处附近的舞会,白人没几个,但和今天相比,舞会悠闲得多。有一次,我们搞了个打鼓比赛,我打得不太好。他们说我鼓打得太“书生气”,他们的冲劲儿足得多。
有一天,那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给我打电话,语气严肃。
“我是技校的校长特劳布律治(Trowbridge)先生。”这是个很小的私立技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斜对面。特劳布律治校长继续官腔十足地说:“我这儿有您的一位朋友,他想跟您说句话。”
“说吧。”
“哈喽,迪克!”是尤卡努啊!原来技校的校长,不像他把自己造作的那么官腔,他非常幽默。尤卡努到那个学校去为孩子们演奏,因此他请我过去,跟他同台演出。于是我们就一块儿为孩子们演奏了:我打古巴小鼓(放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来给他的大檀巴(tumba)鼓伴奏。
尤卡努定期做的一件事儿,是到许多学校谈非洲鼓,鼓点儿是什么意思,谈音乐。他性格很好,笑容如菊: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他鼓打得摄人魂魄——他出过唱片——却在这儿学医。在尼日利亚爆发了战争的时候——或许是在战争之前——他回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尤卡努离开之后,我鼓打得不多了,除了偶尔在晚会上打打,给大家助助兴而已。有一次,我在罗伯特·莱顿(Leighton)家做客吃饭,他儿子拉尔夫和一个朋友,问我想不想打鼓。想到他们这是要我唱独角戏,我说不想。但他们接着就在几个小木头桌子上敲开了鼓点儿,这我就忍不住了:我也拉来张桌子,我们三个在这些小木头桌子上演奏,弄出好些非常有意思的声音。
拉尔夫和他的朋友汤姆·鲁提少瑟(Tom Rutishauser)都喜欢打鼓,我们开始每周聚会,即兴演奏,琢磨节奏,弄点儿玩意儿。这两个家伙是真正的音乐家:拉尔夫弹钢琴,汤姆拉大提琴。我干的,是节奏,音乐我是一窍不通,在我看来,我打的节奏不过是不同音高的鼓点儿而已。但我们搞出了许多很好的节奏,还在几个学校演奏来逗孩子们开心。我们还在当地一个学院的舞蹈班演奏节奏——我在布鲁克林工作的那一阵子,也这么寻开心——我们自称“三夸克乐队”,因此你可以琢磨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给学生讲课,他们在地下室里举办了个晚会,一个真正火辣的摇滚风格的乐队在演奏。这个乐队蛮不错:他们有一副多余的颈铃放在那儿,他们怂恿我玩这个东西。我于是就玩了一会儿,因为他们的音乐节奏感太强(颈铃只是个陪衬——你不会把音乐搞乱),我还真玩得起劲了。
晚会结束后,组织晚会的那家伙告诉我,乐队长说:“嚯!那个过来玩颈铃的家伙是谁啊!他还真能用那么个玩意儿弄出个节奏来!顺便问一句,这个晚会是为一个大人物开的——你知道,他压根儿没来,我还没看见他是谁呢!”
加州理工学院有个剧团。有些演员是学院的学生;另外一些是从外边来的。每当有个小角色,比方说,一个警察,要来逮捕一个人,他们就让一个教授来演。这总是个很有效果的玩笑——教授上台了,抓走个人,又下台了。
几年前,这个剧团正在演《男生和女生》(Guys and Dolls),有一场戏,是男主角把个女孩儿带到了哈瓦那,他们在一个夜总会里。导演认为,让我来演戏台上的这个夜总会里的一个邦戈鼓手,这个主意不赖。
第一次排练,我去了,正在导演的那个女士,指着乐队指挥说:“杰克把乐谱拿给你看看。”
哎哟,我可傻眼了。我不会读乐谱;我还以为,我做的不过是到台子上弄出点动静而已。
杰克坐在钢琴跟前,他指了指乐谱,说:“好了,你从这儿开始,你看,你弄这个。然后呢,我弹卟啷、卟啷、卟啷。”——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他翻开这一页。“然后呢,你演奏这个,接着我们俩都停下来,让他们念台词儿,看到吧,就这儿。”——他又翻了几页,说:“最后,你演奏这个。”
他给我看的这种“音乐”,是某种发疯的小×,夹在竖线和横线之间。他一个劲儿跟我说这玩意儿,以为我是个音乐家呢;要我记住这个,完全不可能。
幸运的是,第二天我病了,不能参加下次排练了。我求我的朋友拉尔夫替我去,因为他是个音乐家,他该知道那都是什么玩意儿。拉尔夫回来说:“事情不是那么糟糕。首先,在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弄得准才行——因为是你为乐队其他人定节奏的,好让他们踩着点儿跟进来。但是,等乐队进来了,那就类似于即兴演奏了,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为台词停一停,但是,根据乐队指挥的手势,我觉得我们能琢磨出什么时候该停。”
可同时我已经让导演接受拉尔夫了,这么说,我们两个都得上台了。他打檀巴,我打手鼓——这使我觉得容易得太多了。
拉尔夫告诉我这个节奏是怎么个样子。那一定只敲二十或三十下,但不可多敲,也不可少敲。我从来也没像这样玩儿过,敲准了,还真不容易。拉尔夫耐着性子给我解释,“左手,再右手,再双手,然后右手……”我干得很卖力,最后,慢慢地,我开始能把节奏刚好敲得准。这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好多天——才掌握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排练,发现了那儿有个新鼓手——一直在那儿的那个鼓手,干别的去了——我们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嗨。在哈瓦那那场上台的,就是我们俩。”
“哦。嗨。让我在这儿找找那场……”他翻到那场戏在的那一页,摸出鼓槌,说:“哦,这一场,是由你们起头儿的,这么弄……”他拿鼓槌敲鼓边儿,乒梆、梆啊梆、乒啊乒、梆梆,快得不能再快了,他眼还看着乐谱呢!没治了!我忙活了四天啊,才搞准了那个鬼节奏,他却信手就打起来!
无论怎么说,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练习,我最后也打得准了,而且真在剧里打呢。演出非常成功:人人都喜欢看这位教授在台上打手鼓,音乐也不那么坏;但是,开头那部分,不能乱改的:真是难。
在哈瓦那夜总会那场戏里,几个学生必须按照舞蹈设计来跳某种舞。因此,导演找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一家伙的妻子,那个时候,她在“环球电影厂”(Universal Studios)当编舞,来教小伙子们怎么跳。她喜欢我们的鼓乐。等戏演完了,她问我们愿不愿意为旧金山的一个芭蕾舞团打鼓。
“什么?”
是的。她即将到旧金山,为那儿的一个小芭蕾舞学校的一个芭蕾舞当编舞。她想创造这么一种芭蕾舞,音乐全是打击乐。她希望拉尔夫和我,在她启程之前,到她家一趟,去演奏一下我们知道的不同的节奏。根据我们打的节奏,她将编一个与节奏相配的故事。
拉尔夫有点儿担心,但我唆使他去冒这个险。然而,我强烈要求她不要告诉那儿的任何人,说我是物理学教授,诺贝尔奖的得主,或者什么其他的大腕儿。正如塞缪尔·约翰逊
 所言,如果你看到一条狗用两条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多么好,而是它竟然那么个走法。我愿意打鼓,但我打鼓仅仅是打而已。如果大家把我当成个喜欢打打鼓的物理学教授,我就不喜欢了;我们就是她在洛斯阿拉莫斯找到的音乐家嘛,到这儿来演奏他们作的这个鼓乐。
所言,如果你看到一条狗用两条后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多么好,而是它竟然那么个走法。我愿意打鼓,但我打鼓仅仅是打而已。如果大家把我当成个喜欢打打鼓的物理学教授,我就不喜欢了;我们就是她在洛斯阿拉莫斯找到的音乐家嘛,到这儿来演奏他们作的这个鼓乐。
于是我们就去了她家,演奏了我们编的好多种节奏。她做了记录,很快地,就在当天晚上,她脑袋里捏造出了个故事,说:“得,这一段,我要求重复五十二次;那一段,四十小节长;还有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我们回家了,第二天晚上在拉尔夫家里录了一盘磁带。我们花了几分钟,演奏了全部的节奏,然后拉尔夫用他的录音机剪剪接接,让每段长度合适。她动身的时候,带了一份我们的磁带,开始在旧金山训练她的舞蹈家们。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练习磁带上的那些东西:这一段,循环五十二次,那一段,循环四十次,等等。我们当时即兴演奏的东西(又经过剪辑),现在却不得不亦步亦趋地学会。我们不得不模仿我们自己的倒霉磁带!
节拍掐得准,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拉尔夫会知道怎么个弄法,因为他是个音乐家嘛,可我俩都发现这事儿滑稽。在我们的脑袋里,“演奏部门”也是管掐节拍的“说话部门”——我们不可能同时又演奏,又数节拍!
等我们到旧金山进行首次排练的时候,我们发现,看着舞蹈演员,我们就不必掐节拍了,因为舞蹈演员的动作是有章可循的。
因为人家把咱们当成了专业音乐家,而我不是,我们遭遇了许多事儿。比方说,有一场戏,说的是一个乞讨的妇女,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筛沙子,而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就在那海滩上,她们在这个芭蕾舞剧一开始的时候就上场了。编舞用来创造这一场景的那个音乐,用的那个特别的鼓,是拉尔夫和他爸爸在好几年前以业余手法造的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也不能让它弄出好听的声音来。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坐着椅子面对面,把这个“神经错乱的鼓”夹在我们的膝盖中间,一个家伙打,哔嗒、哔嗒、哔嗒、哔嗒、哔嗒,用手指快快地打,不停地打,另一个伙计,用两只手在不同的地方挤压这个鼓,它就会变调儿。它现在就弄出这种怪有意思的动静:卟嗒、卟嗒、卟嗒、哔嗒、呗嗒、呗嗒、呗嗒、哔嗒、卟嗒、卟嗒、卟嗒、吧嗒。
好了,演丐妇的那个舞蹈演员,希望音乐有起有伏,来应和她的舞蹈(我们的磁带上的鼓乐,和这场不搭界),于是她就进一步为我们解释她要怎么跳:“首先,我这样做这四个动作;然后呢,我这样前倾,筛沙,筛八个数;然后呢,我站起来,再这么个转法。”孙子才跟得上这一大套,于是我打断她的话头。
“你只管去跳,我随着你演奏。”
“但你不想知道这个舞是怎么往下走的吗?你瞧,等我筛了第二下沙的时候,我就这么个样子来它八下。”这没用。我什么玩意儿也记不住,我又想打断她,但是接着就有这么个问题:我看起来不像个真正的音乐家啊!
很好,拉尔夫非常圆滑地给我打圆场,他解释说:“对这种情况,费曼先生有独特的处理技巧:在他看着你跳的时候,他宁愿把这个舞蹈的动力学原则,直接地、直觉地,发展出来。让咱们像那样试一把,要是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再作修正。”
噢,她是个一流的舞蹈家,你可以预见她下面怎么个跳法。如果她要去挖沙,她会摆出个往沙里拱的架势;每一个动作,都是平滑的,都在你的预料之中,这我就非常容易用手弄出卟呲和卟啥啥和卟嗒嘶和哔嗒嘶这样的声音,和她正在弄的舞蹈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对此很满意。我们就这么混过去了,差点儿露馅儿。
这个芭蕾舞,算是成功的。尽管观众不多,那些来看演出的人,非常喜欢它。
在我们到旧金山排练和演出之前,我们对这整个主意,把握不大。我的意思是,这位编舞愚不可及:首先,这个芭蕾舞只有打击乐;其次,我们还没好到能为芭蕾舞作曲的地步,无功受禄,实在是疯了!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什么“文化”,到头来却为一个芭蕾舞当起了职业音乐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嘛。
我们原以为她找不到愿意随着我们的鼓乐跳舞的芭蕾舞演员。(事实上,就有一位是来自巴西的大明星,葡萄牙领事夫人,认为她跳这个舞,掉价儿。)但其他的舞蹈家好像非常喜欢它,当我们在第一次排练中为她们伴奏的时候,我心甚慰。当她们听到我们的节奏真正是怎么个动静的时候(此前,她们一直用一个小卡式录音机来听我们的磁带罢了),她们所感到的那种愉悦,是发自心底的;当我看到她们对我们的现场演奏是怎么样反应的时候,我信心大增。从看演出的人们的评论来看,我们意识到,我们大功告成了。
这位编舞想在第二年开春,还用我们的鼓乐搞另外一个芭蕾舞,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这个程序。我们录了个磁带,节奏更多,她也捏造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一次,背景是在非洲。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芒格(Munger)教授谈过,学会了几个真正的非洲短语,好在开头儿时唱(噶哇—巴女吗—噶哇—喔,或者类似这么一种调子吧),我练习发音,练到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
后来,我们到了旧金山排练了几场。我们刚到的时候,发现她们有个麻烦。她们不知道怎么把象牙弄在台子上好看。她们用纸糊的象牙太难看;在这种象牙面前跳舞,几个舞蹈演员都觉得尴尬。
我们没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只是静观表演家们下星期来排练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儿。与此同时,我安排好了去访问维尔纳·埃哈德(Werner Erhard)教授,我是在他主办的一个会上认识他的。我在他漂亮的家里坐着,听他给我解释什么哲学或者观念,突然之间,我一下子进入了催眠状态。
“你这是怎么了?”
我爆着眼珠子叫:“象牙!”就在他身后,在地板上,放着一些巨大、粗壮、漂亮的象牙!
他把象牙借给了我们。这些象牙,在戏台上漂亮极了(演员们松了一口气):真正的象牙,超大的象牙,谢谢维尔纳·埃哈德的好意。
我们的编舞转移到了东海岸,在那儿上演他的加勒比芭蕾舞。我们后来听说,她用那个芭蕾舞参加全美国的编舞大赛,得了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受了这一次成功的鼓舞,她参加了另一次比赛,这次是在巴黎,是全世界的编舞大赛啊。她带去了我们在旧金山录制的一盘高质量录音带,在法国那儿训练几个舞蹈演员,来演出那个芭蕾舞的一个小片断——她就是那么进入大赛的。
她干得真不赖。她进入了最后一轮,剩下的只有两个团——拉脱维亚的一个团,用正统的舞蹈演员,跳标准的芭蕾舞,伴以漂亮的古典音乐;一个美国的团,独行其是,只用两个演员,是她在巴黎训练的,跳的那个芭蕾舞,除了鼓乐,没有别的。
观众最喜欢她,可是那个比赛,不看谁最受欢迎,评委们判拉脱维亚人获胜。她后来去找评委,想知道她的芭蕾舞,弱点何在。
“哦,夫人,音乐不太令人满意,不够细腻。渐强音控制欠佳……”
如此说来,我们起码可以发现:等我们来到那些真有文化的巴黎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懂得鼓乐,我们就不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