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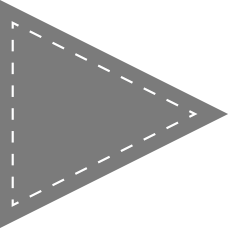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在加拿大,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物理学学生协会。他们主办会议;他们发表论文,等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要我去给他们讲话。主事儿的女孩儿和我的秘书早就筹划好了,不跟我打声招呼,就径直飞到洛杉矶。她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伶俐可爱,一个金发碧眼的妞儿。(这有作用的;不该这样,但这就是有作用。)这事儿的经费全是温哥华的学生出的,这给我留下了印象。在温哥华他们对我太好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接受人家的招待、怎么讲话的秘密了:等学生来请你。
有一次,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几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学生物理俱乐部的几个孩子,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去讲话。我说:“我喜欢去干这个事儿。我想做的,是只想跟物理学俱乐部的人说话。但——不客气地说——我从经验中得知,有麻烦的。”
我告诉他们,以前每年我都到当地的一个高中去跟物理学俱乐部讲相对论,或者讲任何他们让我讲的东西。接着,等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还去那儿,跟以前一样,没做准备,他们呢,把我树在三百个孩子面前。
那可叫一个乱啊。
这种让我害怕的事儿,大约有三四次,我成了个白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次我应邀到伯克利大学去讲物理学的什么东西,我准备了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指望像往常那样讲给物理系的人听。可等我到了那儿,是个巨大的大教室,人满为患!我知道,在伯克利大学,能明白我准备的这个水平的东西,人数没这么多。我的麻烦是,我喜欢取悦于来听我说话的这些人,如果每个人连他的哥哥都来听我说话,我取悦不了他们了:我就不了解我的听众了。
等这些学生理解了我不容易到这个地方给物理俱乐部讲话之后,我说:“让咱们杜撰一个听起来傻头傻脑的题目,再杜撰一个听起来傻头傻脑的教授的名字,那样的话,就只有真对物理学感兴趣的孩子们会不怕麻烦来听讲,那才是我们要的人,好不好?你们不必满世界张扬。”
有几张海报出现在欧文分校的校园里: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沃伦教授,将于5月17日3点在D102室宣讲质子的结构。
然后,我就来了,说:“沃伦教授有点儿私人的麻烦事儿,今天不能来给诸位讲话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能不能来给你们讲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因此呢,我就来了。”这办法,高。
但是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诡计,对学生们好一个生气。他说:“你们知道,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下来,许多人都会来听他讲话的。”
学生们解释说:“就是因为这个嘛!”可这位指导老师气急败坏了,因为炮制这个玩笑,竟然没有他的份儿。
听到学生们真有麻烦了,我决定给那个指导老师写封信,说明那都是我的错儿,说除非这么安排,我就不去讲话,说我已经告诉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非常抱歉;请原谅我,啰里啰唆,啰里啰唆……因为那个鬼奖金,我不得不搞这一套!
就在去年,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学生请我去讲话,这次很好,除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之外。我不需要接受采访;采访没意义。我是来给学物理的学生讲话的,就这么回事儿。如果满城的人都想知道那个,那就让学校的报纸告诉他们得了。正是因为诺贝尔奖,我才不得不接受采访——我是个大腕儿,对吧?
我的一个朋友,有钱——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数字开关——给我讲了一些捐钱设奖或设讲座的人的事儿:“对他们,你要时时留心,看看他们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用这个来安慰良心。”
我的朋友马特·桑德斯(Matt Sands)一度想写一本书,叫《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许多年,到诺贝尔奖快颁发的时候,我也会看看是谁得了奖。但过了一阵子,我连诺贝尔“季节”是什么时候,都想不起来了。因此,为什么有人在凌晨三点半或者四点给我打电话,我是一点都不明白了。“费曼教授?”
“嗨!凌晨这个点儿,你给我打的哪门子电话!”
“我原以为您愿意知道您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的,但我在睡觉!要是你在上午给我打电话,就好了。”——我把电话挂了。
我妻子说:“什么事儿啊?”
“他们告诉我,我得了诺贝尔奖。”
“哦,费曼,是谁?”我经常说话没正经,她也聪明得很,从来不上当,但这次,我逮着她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您听到……”
(无可奈何的声音)“听到。”
然后我开始想:“我怎么能就此打住?我一点儿也不想要这个!”因此,头一件事儿,是把电话从叉簧上拿下来,因为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我想再去睡觉,但我发现睡不成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这事儿。我怎么办?或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那会出什么事儿?或许那做不到的。
我把电话放回去,电话立刻响起。那是《时代》周刊的一个家伙。我对他说:“听着,我有了个麻烦,因此你别记录我下面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个事儿。有办法不接受这个奖吗?”
他说:“您恐怕拿这事儿没办法,先生,您不如将就着得了,免得弄出更多无谓的乱事儿。”事儿明白了。我们谈了不少,15~20分钟的样子,《时代》周刊的这个家伙从来也没发表这次谈话的任何东西。
我对《时代》周刊的这个家伙说,非常感谢你,就挂了电话。电话立即响了:报社打的。
“是的,您可以到报社来。是的,好的。对,对,对……”
其中一个电话,是瑞典领事馆的一个家伙打的。他将要到洛杉矶举行个招待会。我琢磨着,因为我决定接受这个奖,我就必得忍受这些事儿了。
这位领事说:“拟一个名单,是您想请的人,我们也拟一个名单,是我们想请的人。然后呢,我会到您办公室,我们比较一下两个名单,看有没有重复的,然后我们就写请柬……”
我就写了我的名单。大约八个人——我的街坊,我的艺术家朋友左提安,等等。
领事拿着他的名单到了我办公室:加利福尼亚州长,这个大员,那个大腕儿;石油大王格蒂
 ;某个女演员——有三百人啊!不需要说,怎么也不可能有重复现象!
;某个女演员——有三百人啊!不需要说,怎么也不可能有重复现象!
我就有点儿不安了。跟这么多达官贵人见面,这主意,吓坏我了。
领事看出我忧心忡忡。“啊,别担心,”他说,“大多数人不来。”
可好了,我不曾安排个聚会,邀请人家来,又明明知道人家不来!我不必向任何人磕头颠蒜,给他们那种可以拒绝的邀请,让他们有沾沾自喜的机会;这很蠢嘛!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真的为这整个的事儿坐立不安了。我给领事打回电话,说:“我仔细想过,我意识到我没办法去应付这个招待会。”他乐了。他说:“您太对了。”我以为他也跟我一样——为这个抽风的事儿,不得不搞这么个聚会,那还不跟犯了痔疮似的难受。事儿到最后,皆大欢喜。没人想来,连贵客也不来!主人也乐得轻松!
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有某种心理上的困难。你知道,我是我那位一贯睥睨王室和排场的父亲养大成人的(他干的是制服的买卖,因此他知道一个穿上制服的人和一个脱了制服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同一个人)。我实际上是学会了一辈子挖苦这类事儿,这种脾性如此强烈,深入骨髓,不带着点勉强,我都走不到一个国王的跟前去。这很孩子气,我知道,但我就是那么个教养,所以这是个问题。
人家告诉我,瑞典那儿有个规矩,在你接受了这个奖之后,你得倒退着离开国王,不可转身。你走下若干级台阶,受了奖,然后走回台阶上面。因此,我对自己说:“那好,等我去修理他们!”——我练习起了跳着上台阶,倒退着跳,表明他们的习俗有多么可笑。我这情绪太可怕了!那既蠢且傻,当然是。我发现那不再是个规矩了,你可以转身离开国王,你像个正常人类那样走路,朝你打算去的那个方向,把鼻子摆到前头。
我高兴地发现,并非全部的瑞典人,都像你认为的那样,把王室典礼当回事儿。等你到了那儿,你发现他们站在你这边儿。比方说,学生们为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特别的“青蛙授勋”典礼。在你得到这个小青蛙的时候,你必须学青蛙叫。
我在年轻的时候,反文化,但我父亲有些好书。有一本书,里头有古希腊的剧本《青蛙》,有一次,我在这个剧里瞥见了青蛙的叫声,字儿是这么写的:“brek, kek, kek”。我想:“没什么青蛙弄出那种动静;那样来描写青蛙叫声,是发疯!”于是我就自己试着那样叫,在练习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那确确实实就是青蛙的叫声。
因此,我偶尔一瞥阿里斯托芬的书,到后来证明是有用的:在学生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典礼上。我学青蛙叫学得很出色!倒退着跳,也派上了用处。因此,我喜欢典礼的这一部分;那个典礼进行得很好。
在得到了许多乐子的同时,我自始至终确实仍然有这种心理上的困难。我最大的麻烦,是在国王晚宴上不得不发表的“感谢您”演讲。当他们给你那个奖的时候,他们也给几本装帧得很漂亮的书,写的是前些年的事儿,你得到了以前写的全部的“感谢您”演讲,好像那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似的。因此,你就开始认为你在这种“感谢您”演讲中说的话,是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因为它是要出版的呀。我没有意识到的,是难得有什么人会仔细听这种演讲,而且没有什么人会去读它!我已经方寸大乱:我不可能说个非常感谢你就拉倒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说个感谢的话,不是很容易嘛,但不容易啊,我说话得实在。可事实是,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奖,因此,当我不想要的时候,这谢谢你,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我妻子说,我是个神经过敏的废物,竟然为演讲里说什么话慌里慌张,但我最后琢磨出一个办法,来搞出一个听起来完全令人满意却又是完全诚实的演讲。那些听过这个演讲的人,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家伙在准备它的时候,都受了什么苦。
我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在发现了我所做的事情时的那种欢乐当中,在别人运用我的研究工作这一事实当中,在什么什么当中,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尽力解释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期望得到的一切,与此相比,别的都无关紧要。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
但是,我接着说,突然之间,我收到了一大堆信——在演讲里,这个事儿说得比较好——这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那些信,有的来自童年玩伴儿,当他们读早报的时候,跳了起来,叫着:“我认识他!他就是那个和我们一块儿玩的小孩儿!”等等;像那样的信,特别鼓舞人心,表达的是我理解为某种爱的东西。为了那个,我感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顺利,但和王室打交道,我总是觉得有点儿难。在国王晚宴上,我挨着一个公主坐着,她在美国上过大学。我想当然地认为,她跟我的态度一样,但我想错了。我认为她只是个孩子,跟别人一样。我评论国王和王室全家不得不忍受这么长时间,在吃饭之前还得跟招待会上的全部客人握手。“在美国,”我说,“我们能把这事儿搞得更有效率。我们会设计一个握手的机器。”
“是的,但在此地,这机器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她不甚自在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恰相反,市场会是很大的。首先,只有国王有这样的机器,我们会为他免费提供。接着呢,当然,别人也想要一个机器。现在,这问题变成这样:谁能被允许拥有一台机器?总理得到许可,可以买一台;然后参议院议长得到许可,可以买一台,然后是最重要的老资格议员。因此,一个很大的、不断扩展着的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很快,你也不必去和一长串等着召见的机器握手了;你把你的机器派去就成!”
我也坐在那位负责组织这个晚宴的夫人旁边。一个女服务员过来,往我的酒杯里倒酒,我说:“不,谢谢你,我不喝。”
这位夫人说:“不,不。让她斟酒。”
“可我不喝的啊。”
她说:“没关系。您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八十八号不饮酒。”(八十八号在我的椅子背上。)“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有一种不含酒精。”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叫起来。
她微微一笑。“现在看看皇上,”她说,“他也不饮酒。”
她告诉了我一些他们在特别的一年遇到的麻烦事儿。其中有一件,是俄国大使该坐哪儿?像在这样的宴会上,麻烦总是谁坐得离国王近些。诺贝尔奖得主,通常比外交使团,坐得离国王近些。外交官的座次,决定于他们在瑞典任职的时间长短。在当时,美国大使比俄国大使在瑞典待的时间长。但在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肖洛霍夫
 先生,一个俄国人,而俄国大使想为肖洛霍夫先生当翻译——因此就坐在他旁边,因此,问题是如何让俄国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些,又不至于得罪美国大使以及其他外交使团。
先生,一个俄国人,而俄国大使想为肖洛霍夫先生当翻译——因此就坐在他旁边,因此,问题是如何让俄国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些,又不至于得罪美国大使以及其他外交使团。
她说:“在我得到许可把这位大使安排坐在肖洛霍夫先生旁边之前,您可不知道他们这一通闹腾——信件来往如梭,电话铃声不断,等等。最后,大家同意,那位大使,在那天晚上,将不是苏联大使馆的官方代表;他倒成了肖洛霍夫先生唯一的翻译。
晚宴之后,我们离座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大家在里面三五成群地谈着。有一个丹麦什么公主,不少人和她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我看到他们这桌子有一张空椅子,就坐了下去。
她转朝我说:“哦!您是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您在什么领域工作?”
“物理。”我说。
“噢。呃,没人知道那个,因此我猜我们没法子谈那个。”
“恰恰相反,”我回答,“正是因为有人还知道点儿物理,我们才没法子谈物理。没人知道的那种事儿,我们才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谈天气,我们可以谈谈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谈谈心理学;我们可以谈谈国际金融——可是黄金买卖,我们谈不得,因为这个事儿,人人都明白——因此,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的那种题目,才是我们可以谈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办到的。有一种方法,是在脸的表面上结冰,她就能够做到一脸冰霜!她转过脸,跟别人谈去了。
过了一阵子,我看得出来,我完全从谈话中给割了出去,于是我就站起来,要走开。日本大使,也坐在这桌子旁,跳起来,跟着我。“费曼教授,”他说,“我愿意告诉您一点儿外交上的事儿。”
他讲了一个好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去上大学,研究国际关系,因为他以为自己能够为他的国家做出贡献。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他开始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种由怀疑带来的隐痛。大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大使馆得到了他的第一个职位,直到他意识到,没有人懂得国际关系的任何事儿。到了这份儿上,他就能够做大使了!“因此,费曼先生,”他说,“下次您再举例说明那些人人都在谈没人知道的事情的时候,请把国际关系包括进去!”
他这人很有意思,我们就谈开了。我一直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民,何以会有不同的发展这一问题感兴趣。我告诉这位大使,有一件事,在我看来,一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日本是如何把自己迅速发展为一个在世界上如此现代而重要的国家的。“日本人民的什么方面和性格,才使日本有可能办成此事?”我问。
日本大使回答的方式,我喜欢听:“我不知道。”他说,“我倒可以假定某种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条前进的道路:让他们的孩子比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使他们抛开农夫的境地,而成为有教养的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家庭里,大家下了大力气,来鼓励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好,有出息。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趋势,外来思想可以非常容易地播撒到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或许那就是日本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总而言之,我必须说,瑞典之行最终是令人愉快的。我没有立刻回家,却去了在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去讲话。我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的时候,穿的是那身出席国王晚宴时穿的西服——我以前从来没有穿着西服讲话。我是这么开讲的,“事儿很可笑,你们都知道;在瑞典,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变化:我还挺喜欢这身西服。”
人人都说“啊呸!”。维斯科普夫(Weisskopf)跳起来,甩掉他的外套说:“在讲座上,别穿西服了!”
我把我的外套脱了,松了松领带,说:“我在瑞典过了这一阵子之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了。可是,现在,我回到了世上,一切事情又都顺了。谢谢各位把我弄妥帖了!”他们不想让我变。因此事儿搞得很快:在CERN,他们把我在瑞典经历的事儿都消除一空了。
我得了钱,这不错——我买得起一所在海边的房子——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不得奖金,好得多。——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在公共场合率性而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贝尔奖,从来都是一件恼人之事,尽管我起码有一段时间为此扬扬自得。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格温妮丝和我收到了巴西政府的邀请,作为荣誉贵宾,参加里约的狂欢节庆典。我们欣然接受,玩儿得很开心。我们跳舞跳得不亦乐乎,看桑巴学校在盛大的游行中,演奏他们那种奇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纸和杂志的摄影师不停地拍照片——“看哪,美国来的教授和巴西小姐跳舞哪。”
身为“名流”是一乐子啊,但把我们当名流,显然是错了。那一年,没人对荣誉贵宾大惊小怪的。我后来才发现,给我们的邀请是怎么弄出来的。本该当荣誉贵宾的,是吉娜·罗洛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
 ;可就在狂欢节之前,她说不。负责组织狂欢节的旅游部长,在“物理研究中心”有些朋友,他们知道我以前在桑巴乐队里玩儿过,又因为我最近得了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新闻上就有。在部长六神无主之际,他的朋友们就出了个馊主意:用物理学教授,代替吉娜·罗洛布丽吉达!
;可就在狂欢节之前,她说不。负责组织狂欢节的旅游部长,在“物理研究中心”有些朋友,他们知道我以前在桑巴乐队里玩儿过,又因为我最近得了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新闻上就有。在部长六神无主之际,他的朋友们就出了个馊主意:用物理学教授,代替吉娜·罗洛布丽吉达!
不用说,这位部长把狂欢节的工作搞得这么糟糕,后来丢了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