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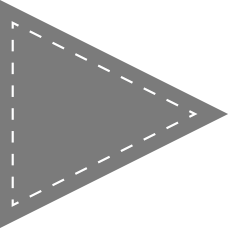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书好书坏,看看封面
书好书坏,看看封面
战争之后,物理学家常常被召到华盛顿,给各政府部门,特别是军事部门,献计献策。何以如此?我猜是这样:由于科学家已经制造了那些如此重要的原子弹,军方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在某些事情上,还可以派派用处。
有一次,有人要求我在一个委员会里当差,这个委员会要为军方评估各种各样的武器,我写了封回信,解释说,我只是个理论物理学家,我不知道任何关于军队用的武器的事儿。
军队的反应是,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已经发现理论物理学家在他们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可否再做考虑?
我又回了封信,说我实在一无所知,我怀疑我能帮他们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了陆军部长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了一个折中方案:我去参加第一次会议,我可以听听,看我能不能有所贡献。然后呢,我再决定我是否继续干下去。
我说,我去,当然。我还能怎么办啊?
我去了华盛顿,我参加的第一个玩意儿,是一个鸡尾酒会,好认识各位。那儿有将军和陆军来的其他重要人物,大家都在聊着。这很令人愉快。
一个穿军服的家伙朝我走来,告诉我,物理学家给军方献计献策,军队是很高兴的,因为军方问题很多。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坦克耗油太快,所以跑不远。因此,问题就是:怎么在坦克跑着的时候给它加油?这个家伙,当时脑袋里有个主意:既然物理学家能从铀里捣鼓出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搞出一个办法,把二氧化硅——沙子,泥土——用作燃料?假如此事可行,那么只需要在坦克下面装个小铲子,它一往前走,铲子就挖土,把土当燃料!他觉得这主意相当伟大,我需要做的事儿,不过是搞出具体的细节而已。我想,这就是我们次日开会讨论的那类问题了。
我去开会,注意到在鸡尾酒会上把我介绍给大家的那主儿,就挨着我坐着。他显然就是一个受命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奴才。我的另一边,是一个高级的将军,我以前听说过。
在第一次会上,他们谈了些技术上的事儿,我稍微评论了几句。但后来,快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讨论后勤方面的某个问题,这我就一无所知了。这问题是要琢磨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你应该有多少东西。尽管我努力想闭紧自己的嘴,但人处在那种情况中,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一张桌子,讨论这些“重要的军国大计”,你就是不能把嘴闭上,尽管你啥也不知!因此,我在那次讨论中,也发表了一些评论。
下次咖啡时间,那个跟牧羊犬似的受命不离我左右的家伙说:“您在讨论时说的那些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我沉吟片刻,思忖我对后勤工作的“贡献”,意识到,一个在商店里负责为圣诞节订货的家伙,在琢磨那种问题的时候,会比我更在行。因此,我的结论:a)如果我确实有所贡献,那是瞎猫撞到了死耗子;b)这种事儿,任何别人都做得来,但大多数比我都做得好;c)这种恭维应该让我清醒一下了,实际上我贡献不了多少。
他们迅即在会上决定,他们最好是讨论一下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比方说,科学发展应该归工兵团管还是归军需处管?)而不是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我知道,如果我有希望做出任何真正的贡献,那也只能是在某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上,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组织军队中的研究。
直到那时,我也没让这次会议的主席——就是那个邀请我来参加会议的大腕儿——知道我对这种情况的感觉。在我们收拾行囊要走的时候,他满面微笑地对我说:“你这就跟我们同舟共济了,那么,下次会议……”
“不,我不来了。”他脸色顿时为之一变,这我看得出来。他很吃惊我在做出了那些“贡献”之后,竟然会说不。
60年代初,我的许多朋友仍然在向政府献计献策。与此同时,我没什么社会责任感,尽可能拒绝到华盛顿去;在那年头,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那时我为大学新生开了一系列物理课,在其中的一门课讲完之后,帮助我在上课时做演示的汤姆·哈维(Tom Harvey)说:“你可得看看课本里的数学是怎么回事儿!我女儿带回家好多发疯的玩意儿!”
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但第二天我接到个电话,是帕萨迪纳一位颇有名气的律师诺瑞斯(Norris)打来的,当时他是“州教育委员会”的人。他问我愿不愿意为“州课程编制委员会”服务,这个委员会得为加利福尼亚州选择一些新课本。你知道,这个州有一项法律,全部公立学校的所有孩子用的课本,都必须是州教委选择的,因此他们设立了委员会来检查课本,向他们提出建议应该选哪些书。
原来,许多课本都是根据教算术的新教学法(他们称之为“新数学”)来编写的。因为通常看这些书的人,只是老师和主管教育的官员,他们认为,让一个在科学上运用数学的人帮忙评价课本,会是个好主意,这样的人知道最终产品是什么,也知道我们教数学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若不跟政府合作,一定有负疚感,因为我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
立刻,我就开始接到出版社的信和电话。他们说的是这么些话,“我们很高兴获悉您在委员会里,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位懂科学的人……”还有,“委员会有一位科学家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课本就是以科学为指针……”但他们还说这样的话,“我们愿意向您解释我们的课本……”以及“我们很乐意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您来评估我们的课本……”这在我看来是发疯。我是个客观的科学家,在我看来,孩子们在学校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课本(教师有教学指南,我也得看)。出版公司多余的解释是捣乱。因此,我不想和任何出版社说话,我总是这么回答:“你们不必解释,我相信书会自己说话。”
我代表一个区,这包括洛杉矶的大部分地区,只是洛杉矶市区除外。洛杉矶市区的代表是一位很好的女士,在洛杉矶学校系统工作,名字叫怀特豪斯(Whitehouse)夫人。诺瑞斯先生建议我应该跟她见见面,看看委员会干的是什么,怎么干。
怀特豪斯夫人开始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要谈的事儿(他们已经开过一次会,我任命得晚)。“他们要讨论数字计算的问题。”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后来知道那是他们称之为整数的东西。每种东西,他们都另有名称,所以我一开始就麻烦不少。
她告诉我,委员们通常是怎么来给课本打分的。每本书,他们会收到好些册,然后分给他们区里的许多老师和官员。然后,他们收报告,报告上有这些人对这些书的看法。因为我不认识很多老师和官员,还因为我觉得我得自己读那些书,我才能拿得准在我看来怎么样,所以我宁肯亲自读书。(我区里有些人,早就希望看这些书呢,希望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怀特豪斯夫人建议把这些人的报告,和她的报告放在一起,那样他们会感觉舒服点儿,我也不必担心他们发牢骚了。他们满意,我也没惹很多的乱子。)
几天后,书库的一个家伙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准备给您寄书了,费曼先生;总共有300磅。”
我犯晕了。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个人帮你看书。”
我琢磨不出你怎么帮我看书:你或者是自己看,或者是不看。我专设了一个特别的书架,放在楼下我的书房里(那些书摞起来有5米高),然后就开始读所有这些在下次会上要讨论的书。我们先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是个相当大的活儿啊,我一天到晚在地下室里工作。我妻子说,那段时间,她好像住在一座火山上。这火山会安静一阵子,可突然之间,“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下面的火山就会有一个大爆发。这原因是那些课本太稀松。满纸荒唐言,都是急就章。那些书倒是想严格一些,但用的那些例子(如用街上的汽车来阐述“集”的概念)是牵强的,总有些词不达意。定义不严格。一切都有那么点儿含糊其词——写书的人不够聪明,不理解“严格”是什么意思。他们胡乱编造。他们在教某种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在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对孩子们也没用处。
我明白他们意欲何为。在苏联放了卫星之后,许多人认为我们落后于他们,有人就让一些数学家出谋划策,怎么运用非常有趣的现代数学概念来教数学。这个目的是想提高那些觉得数学很乏味的孩子们的数学水平。
我给你一个例子:他们要讨论不同的进位制——五进制,六进制,等等——来表明不同的进位制是可能的。这对那些能够理解十进制的孩子来说,或许是有趣的——一种娱乐大脑的东西。但在这些书里,他们搞的那一套,结果是让每一个孩子必须学会另外一种进位制!紧接着,通常会有的那种恐怖就来了:“将下列七进制的数字,翻成五进制的数字。”把一种进位制的数,翻成另一种进位制的数,是吃饱了撑的。要是你会做,或许是个乐趣;要是你不会,就别理会它。这事儿没意义。
无论如何,我看所有的书,没有一本说过在科学中运用数学的事儿。如果有什么关于算术的用处的例子的话(大多数时候,那例子都是这种抽象的、新鲜的、现代的胡说八道),却是说的买邮票的事儿。
最后,我看到的一本书,说:“数学以许多方式运用在科学当中。我们将给你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关于星体的科学。”我翻过这一页,它说:“红色的星温度有4000度,黄色的星温度有5000度……”——到目前为止,还好。它继续说:“绿色的星温度有7000度,蓝色的星温度有10000度,紫色的星温度有——(一个很大的数)。”没什么绿色的或者紫色的星啊,但和其余的星相关的数字,大体算对。那是马马虎虎地对——但是,麻烦已经出现了!满篇都是这么搞法:一切都是由某个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些什么的主儿写的,因此总是有一些小错误!用这种课本,写课本的人又不十分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教得好啊,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书是马虎的;普遍地差劲!
话说回来,这本书还是让我高兴的,因为把数学运用到科学上,这是第一本。等我读到星体的温度的时候,我有那么点儿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它多少还算是对的——它只是例子错了。接着却出现了一串错误。它说:“约翰和他爸爸出去看星星。约翰看到了两颗蓝色的星和一颗红色的星。他爸爸看到了一颗绿色的星,一颗紫色的星和两颗黄色的星。约翰和他爸爸看到的星星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度?”——我厌恶之极,要爆炸了。
我妻子该说起楼下的火山了。那只是一个例子:那样的东西太多了。多得荒唐啊!把两颗星的温度加起来,是吃饱了撑的。没人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除非接着求两颗星的平均温度,或许是例外,但不是要发现所有星体的温度总和!可怕!它不过是个让你做加法的游戏,他们也不理解自己在讲什么。那就好像读一个有几个排版错误的句子,接着,突然一整句都印反了。这种数学与此相似。简直没指望了!
然后,我去参加我的第一次会议。别的委员已经给一些书打了某种分数,他们问我,我的分数是怎么打的。我的分数经常和他们的不同,他们就问:“您为什么给那本书打分打得那么低啊?”
我就说,那本书的毛病,是哪一页上的这个、这个——我做了笔记。
他们发现我是某种金矿:我详详细细告诉他们,在所有的书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打的每一个分数,都有根据。
我问他们为什么给那本书打分打得那么高,他们就说:“让我们听听您对这本书的想法。”我从来也没发现他们是按照什么方式来打分的。他们倒不停地问我是怎么想的。
我们检查到某一本书,它是一个公司出版的三本一套的小学课本中的一本,他们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我说:“书库没给我寄这本书,但另外两本不错。”
有个人还要重复这个问题:“您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我说过,他们没给我寄那本,所以我对它没法判断。”
书库的人在那儿,他说:“对不起,我可以解释这件事儿。我没给您寄那本书,是因为它还没写完。有个规定,就是必须在某个时间之前把书都送来,那家出版社赶不及,因此他们只把封面发给我们,里头都是白纸。出版公司写了个条子来表示歉意,并希望他们那一套三本书能够列入考虑之中,虽然第三本要晚一些。”
我却发现,某个委员给那本无字之书也打了分!他们不相信那是本空白书,因为那本书有分数啊。事实上,那个分数比另外两本还高一点儿呢。书里空空如也,这个事实竟然和分数无关。
我相信,出这种事儿,其原因在于这个制度就是这么个方式。在你把书分发到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手里的时候,他们忙;他们马虎;他们是这么想的,“哎呀,反正有那么多人都在读这本书嘛,打多少分无所谓。”他们就信手画上个分数——至少有些分数是这么打的,不是全部,但有些是这么打的。然后,你收到了报告,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本特殊的书得到的报告比别的书少——于是你就把你得到的报告上的分数一平均,你没把没给你报告的那些人打的分平均在内——就是说,或许一种书发下去了十本,这本书有六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就把写了报告的人打的分数一平均;你没有把没写报告的人的分数也平均了,于是你得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分数。这种一直在求平均数的过程,忽视了一个事实:在那本书的书皮之下,绝对是空空如也!
我之所以搞出了这么一个理论,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课程编制委员会里发生的事儿:那本无字书,十个委员中有六个写了报告;可是,别的书,十个委员中有八九个写了报告。他们把六个分数平均一下得到的分数,和把八九个分数平均一下得到的分数,一样好。发现给那么一本书也打了分,他们非常尴尬,这事儿却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原来其他委员把大量工作花费在发书和收报告上,再就是去开会。在会上,出版社在他们看那些书之前,为他们解释那些书。委员会中,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了全部的书,也没采纳从出版社那里来的任何信息,除了课本之外,而课本是最终进入学校的东西。
想搞清楚一本书是好是坏,是仔细地去读,还是从许多漫不经心的人那里收报告,这个问题和那个有名的古老问题有几分相似:没有人获准看到中国皇帝,问题是:中国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为了找到答案,你遍访全国人民,问他们认为中国皇帝的鼻子有多长,然后你把不同的长度平均一下。你以为那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你把那么多人的数据平均了。但是,要发现点儿东西,那不是个法子;你让范围那么广大的人来贡献数据,可他们全都漫不经心,通过求平均数,你是不能知道得更准确一点儿的。
起先,没人指望让我们讨论课本的价格。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选多少种书,于是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工作程序,允许许多补充课本,因为全部的新书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最严重的缺陷,在“新数学”课本里:没有应用题;用文字表述的问题,不够多。连卖邮票的事儿也不谈,换算和抽象的东西倒说得太多,却没把这些东西转化为现实世界里的实际应用。你干的是什么:加、减、乘还是除?因此,我们建议把确有一些实际应用的书当作补充课本——每个班有一两种——作为学生课本的一个补充。花费了许多讨论时间,我们把一切都搞得平衡妥帖了。
等我们把推荐意见交给教委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钱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返工重来,砍掉这个,砍掉那个,现在要把费用考虑进来,原先那个四平八稳的方案就给毁了,在毁了的那个方案中,教师有机会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的一些实例。
既然他们改变了我们可以推荐多少书的老规矩,我们就不可能把事情搞得平衡了,这是个相当平庸的方案。等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得到这个方案的时候,这个方案还在挨砍呢。现在,它可真是差劲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让我去见州参议员,但我拒绝了:到那个时候,为这事儿争来争去的,我也累了。我们把提交给教委的推荐报告都预备好了,我也认为把这个推荐报告提交给州里,是他们的工作——这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但在政治上不那么稳妥。我不该这么快就放弃,但是,为了那些书,花了那么大力气,费了那么多口舌,才搞出了那么一个相当平衡的方案,然后呢,把它从根儿上捣毁——这可不提情绪!这整个过程全是无用功,你本来应该反过来,从另一头儿做起:从课本费用为起点,你有多少钱,就买什么书。
第二年,我们要讨论科学课本,这事儿最后让我斩钉截铁,不干了。我以为科学课本或许不同,因此我就看了几本。
同样的事儿又发生了:事情乍看起来还不错,接着就让你恶心透顶。比方说,有一本书,开始是四张图片:第一张是个弹簧驱动的玩具,接着是一辆汽车,接着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子,接着是别的什么东西。每张图片下面说:“什么让它动?”
我想:“我知道这是个什么用意:他们要谈机械,玩具里的弹簧是怎么工作的;要谈化学,汽车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要谈生物学,肌肉是怎么工作的。”
这种事情,我爸爸谈过:“什么让它动?一切运动,是因为太阳在照射。”我们接着讨论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
“不对啊,玩具动,是因为里面的弹簧上紧了。”我说。
“弹簧是怎么上紧的?”他问。
“我把它扭紧了。”
“那么你怎么会动呢?”
“我吃饭有劲儿啊。”
“庄稼生长,仅仅是因为太阳在照射。因为太阳在照射,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动”。那样我就得到了一个概念:运动仅仅是太阳能的转化。
我翻过这一页。关于那个玩具,答案是:“能量让它动”。关于那个骑自行车的男孩儿,“能量让它动”。关于任何事儿,“能量让它动”。
那毫无意思啊。假定你不说“能量”,你说“老毛猴子”。那样的话,那个普遍原则就是:“老毛猴子让它动。”这里面出不来什么知识。孩子理解不了任何东西,那不过是个词儿嘛!
他们应该做的,是看着这个玩具,看清楚它里面有弹簧,了解弹簧是什么东西,了解轮子是什么东西,别把“能量”当回事儿。过后呢,等着孩子们理解了这玩具实际上是怎么工作的时候,他们才能讨论关于能量的更普遍的原理。
再说,“能量让它动”,这也不对,因为等玩具停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说,“能量让它停”。他们谈的那件事儿,是浓缩起来的能量,正在转化为稀释了的形式,这是关于能量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方面。在这些例子里,能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它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罢了。当东西停下来的时候,能量变成了热,变成了一般的无序状态。
但是,所有的课本都是那个写法:说的那些事儿,没用、混乱、含混、迷惑,以及部分地不正确。谁能从这种书里学到科学,鄙人不知,因为那不是科学。
因此,我看到这些令人作呕的课本,毛病和那些数学课本一样,这时我就看到我的火山形成过程又开始发动了。读那一堆数学课本,使我精疲力竭;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使我情绪低落。再这么折腾一年,我闻之色变,我得辞职。过了一阵子,我听说,那本“能量让它动”的课本,即将被推荐给教委的课程编制委员会,于是我就做了最后一个努力。委员会的每次会议,都允许公众发表评论,于是我就站起来,说我为什么认为那本书坏。
那个在委员会取代了我的主儿说:“什么什么飞机公司的65位工程师,都认可了那本书。”
我不怀疑那个公司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工程师,但采纳65个工程师的意见,就是相信大范围人的能力——这必然要把一些相当可怜的家伙的能力也包括在内!这又是那个求中国皇帝的鼻子平均有多长的问题,又是那个给无字之书打分的问题。先让那个公司来决定谁是比较好的工程师,然后让这些比较好的工程师来检阅这个课本,那就会好得多。我不敢自称我比65个家伙更聪明——但我比65个家伙的平均数更聪明,却是肯定无疑的!
我没办法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明白,委员会认可了那个课本。
在我还在委员会里的时候,我不得不去了几趟旧金山开了几次会,等我第一次出差回到洛杉矶的时候,我在委员会办公室停了一下,报销我的费用。
“花销是多少,费曼先生?”
“那个,我坐飞机到旧金山,因此那就是机票,再加上我在离开以后把汽车留在机场那儿的停车费。”
“您带着机票?”
我碰巧带着机票。
“您有停车场的发票吗?”
“没有,但我把车停在那儿,花了2.45美元。”
“可我们必得要发票啊。”
“我告诉过你,那花了多少钱。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么,关于那些课本,为什么还要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呢?”
这事儿焖炖了不少时间。不幸的是,我以往都是为公司、大学或者普通人上课。我习惯于这么一种搞法:“您花销多少?”——“这么这么多。”——“这是您的钱,费曼先生。”
于是我决定:不管什么事儿,我是不打算给他们发票的。
第二次出差到旧金山之后,他们又要机票和发票。
“我啥票也没有。”
“这可不行啊,费曼先生。”
“在我接受为本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会为我支付开支。”
“但我们期望得到发票来证明开支啊。”
“我没什么东西来证明开支,但是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你知道我到了这些别的城市;你以为我究竟是怎么到了那些地方的?”
他们不肯通融,我也是。我觉得,当你身处此境的时候,你要真的跟这个“制度”较起真儿来,那你就必须愿意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我心甘情愿,但我的出差费用始终没报销。
这是我玩儿的一种游戏。他们要发票?我偏不给他们发票。那么你就别要钱。那好,不要钱就不要钱。他们信不过我?见他的鬼去。他们用不着给我报销。当然,这事儿荒唐!那是政府的工作方式,这我知道;那好,去他的政府!我认为,人应该把人当人来对待。除非我能得到人的待遇,我就不想和他们有来往!他们感觉不良?我也感觉不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在下面这件事儿中,你看看,纳税人得到了什么样的保护。
在进行了很多讨论之后,有两本书,我们形成不了决定;这两本书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就把这事儿留给教委裁决。因为委员会现在开始考虑费用了,又因为那两本书半斤对八两,委员会就决定招标,取价低的。
问题接着就来了,“学校是在正常时间得到书,还是或许在新学期之前早一点儿得到书?”
一个出版社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标;我们能够在下学期把书提前送去。”
那个输了标的出版社的代表,也在那儿,他站起来说:“因为我们的标是根据较晚的期限投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按照较早期限重新竞标的机会,因为我们也可能早一点出书。”
诺瑞斯先生,在委员会里的帕萨迪纳的律师,问后面那个出版社的家伙:“你早一点儿出书,我们要出多少钱?”
那家伙出了个价:便宜了一点儿。
头一个家伙站起来:“如果他改变他的投标,我也有权力改变我的投标!”——他出价更低!
诺瑞斯问:“哦,是那样吗?——我们提前得到书,并且更便宜?”
“是的,”一个家伙说,“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别的印刷方法,我们一般不用的……”——这是在解释为什么会便宜。
另一个家伙随声附和:“你做得越快,费用就越少!”
这可真是骇人听闻。最后是便宜了200万美元啊。这种突然的变化,真让诺瑞斯七窍生烟。
结果事情当然是这样:交货日期不定了,就开了口子让这些家伙重新投标。正常的情况是,当选书不考虑价格的话,那就没有理由降低价格;出版社想定什么价就定什么价。通过压价来竞争,没好处;他们那种竞争方式,是为了给课程编制委员会留下印象。
顺便提一下,只要委员会开会,出版社就招待课程制定委员会的人吃午饭,跟他们谈书的事儿。我从来没去。
事儿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但人在当时,遇到下面这种情况,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我收到了一包干果,或者“西联公司”寄来的无论什么东西,里头还附带了一个纸条儿,“从我们家到你们家,感恩节快乐——帕米里奥一家。”
东西是从长滩(Long Beach)
 这地方的一家人那里寄来的,但我不认识这家人。显然是有人想寄东西给他朋友一家,可把名字和地址搞错了,因此我想我还是把事情搞清楚的好。我打电话给“西联公司”,得到了那个寄东西的一家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们打电话。
这地方的一家人那里寄来的,但我不认识这家人。显然是有人想寄东西给他朋友一家,可把名字和地址搞错了,因此我想我还是把事情搞清楚的好。我打电话给“西联公司”,得到了那个寄东西的一家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们打电话。
“喂,我叫费曼先生。我收到了个包裹……”
“啊,哈喽,费曼先生,我是皮特·帕米里奥(Pete Pamilio)。”他说得亲亲热热,我都认为我应该知道他是谁!我通常就是这么个傻瓜,记不住人。
于是我说:“我很抱歉,帕米里奥先生,我记不大准你是哪位了……”
原来他是一家出版社的代表,我呢,替课程编制委员会评估他们的书。
“我明白了。但这可能会引起误解。”
“只是咱们两家子之间的来往嘛。”
“是的,可我眼下正在评估你们出的书,或许有人会胡乱解释你的好意!”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事儿了,但我故意装疯卖傻。
与此类似的另一件事儿,是一家出版社寄给我一个真皮的公文包,还把我的名字用金字漂漂亮亮地烫在上边。我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不能收;我在评估你们出的一些书。我觉得你不了解这事儿!”
有个委员,做的时间最长,说:“我从来没收东西;那让我心神不宁。可一直有人送东西。”
但我真的错过一次机会。假如我脑子转得快,那我在那个委员会里的时候,真可以花天酒地。我晚上住在旧金山一家旅馆,等第二天好参加我的第一次会议,我想在城里溜达溜达,吃点儿东西。我从电梯里出来,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两个家伙,跳起来,说:“晚上好,费曼先生。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洛杉矶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带您去瞧瞧?”他们是一家出版公司的人,我不想和他们搀和事儿。
“我出去吃点儿饭。”
“我们可以带您去用晚餐。”
“别,我想一个人。”
“呃,无论您想怎么办,我们都帮得上忙。”
简直盛情难却了,我就说:“那好,我想出去找麻烦。”
“我们认为,那个我们也能帮得上忙。”
“不,我想我可以照顾自己。”我接着就想,“错了!我应该让一切运作起来,记个日记,那样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就可以发现出版社办事儿有多过分!”等我发现出入竟然有200万美元的时候,老天爷知道那好处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