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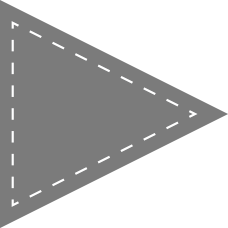 电是火吗?
电是火吗?
50年代早期,我暂时得了一种中年病:习惯于就科学发表哲学性质的讲话——科学是怎么满足好奇心的,科学怎么给你一个新的世界观,科学怎么赋予人做事情的能力,科学怎么给人力量——问题是:从新出现的原子弹这个东西来看,给人那么大的力量,是个好主意吗?我还思考过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大约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到邀请参加在纽约的一个会议,讨论“平等的伦理学”问题。
在长岛那地方,这些老人以前曾经在那儿开了个会,今年他们决定让一些年轻点儿的人加入进来,来讨论他们在另一次会议上搞出来的一些论文。
在我赴会之前,他们到处散发一个列表:“这里是一些您或许有兴趣来读的书,请告诉我们你希望别人也来读的书,我们将在图书馆里收藏这些书,好让别人也来读。”
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奇妙的书籍列表。我开始读第一页:其中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很不自在啊——我不入流啊。我看第二页:我一本也没读过。整本列表看完了,我发现,这些书,我一本没看。我必定是个白痴,一个文盲!里头有好书,如托马斯·杰弗逊的《论自由》(
On Freedom
)之类的书。其中的作者,我也不知道几个。有一本书是海森伯
 写的,一本是薛定谔写的,还有一本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像爱因斯坦的《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
)和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
),和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有所不同。因此,我觉得自己真是一筹莫展了,我不该参加这个会议。或许我可以静悄悄地坐着听。
写的,一本是薛定谔写的,还有一本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像爱因斯坦的《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
)和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
),和我以前读过的东西有所不同。因此,我觉得自己真是一筹莫展了,我不该参加这个会议。或许我可以静悄悄地坐着听。
我去参加了第一次好大的见面会,一个家伙站起来,解释说,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有点儿云山雾海的——是关于伦理学和平等的什么玩意儿,但我听不明白这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将展示一条道路,一条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之间可以进行对话的道路。”那儿还有个国际律师,一个历史学家,一个耶稣会的牧师,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一个科学家(我),等等。
好了,我的那个逻辑头脑立刻就这样转起来了:第二个问题,我完全不必在意,因为如果那行得通,它就行得通;如果它行不通,它就行不通——如果我们没什么可谈的,那么我们之间可以对话,这也用不着证明了,也用不着讨论了!因此,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个,可那个,我又不懂。
我正想举手说:“你能不能把第一个问题定义得好些。”但我当时想:“别了,我不学无术;我最好还是听着点儿。我不想一开始就添乱。”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应该讨论“教育平等的伦理学”。在我们小组的几次会议中,那个耶稣会牧师总在谈“知识的分崩离析”。他说:“教育平等的真实问题,是知识的分崩离析。”这位耶稣会牧师回顾了13世纪,其时天主教会主宰着全部的教育,整个世界都是简朴的。存在一个上帝,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井然有序。可是,今天,理解任何事情,都不那么容易了。因此,知识已经分崩离析了。我觉得,“知识的分崩离析”和“一切”没关系,但他从来也没定义什么是“一切”,因此我没办法证明他的话。
最后,我说:“这个伦理学问题,怎么就和知识的分崩离析扯上了关系呢?”他呢,只是用大团大团的烟雾来回答我,我说:“我听不懂。”可是别人都说听得懂,而且他们还努力为我解释呢,但他们没办法给我解释清楚!
因此,这个小组里的人,就让我把我认为知识的分崩离析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的理由写下来。我回到宿舍,仔仔细细地写,尽量写得好,我认为“教育平等的伦理学”这个主题或许是个什么问题,我还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例,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讨论这些东西。比方说,在教育中,我们增加差异,这是合乎道德的吗?然后,在又举了几个例子之后,我继续说,“知识的分崩离析”之所以是个麻烦事儿,是因为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理解事物,照我对这一主题范围的定义,我看不出知识的分崩离析,怎么就和任何近似于教育平等的伦理学问题的任何东西有关系。
第二天,我把我的论文带进了会场,那个家伙说:“是的,费曼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放一放,留待将来可能的时候再讨论吧。”他们完全没能理解我的主旨。我是想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表明为什么“知识的分崩离析”和我们的问题没任何关系。在那次会议上,没什么人能够说清楚任何事儿,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没有把“教育平等的伦理学”这个问题定义清楚啊,因此,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们该谈什么。
有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论文给我们大家读——这东西是他提前写的。我开始读这个鬼东西,我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简直搞不清楚它说的是个什么子丑寅卯!我琢磨着,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不曾读过列表上的那些书。我有一种颇不自在的感觉,“我学养不厚啊”,直到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得停下来,只慢慢读一个句子,那样我就能琢磨出它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我就停下来——随便停在哪儿——然后读下一个句子,读得非常仔细。我不能精确地记得那个句子,但它非常近似于这么一个东西:“社会大众的每一成员,常常是通过视觉的、符号的渠道来接受信息的。”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把它翻译成别的句子。你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人们阅读。”
然后,我过渡到下一个句子,我发现我也能翻译这个句子。结果它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空虚无聊的玩意儿:“有的时候人们阅读,有的时候人们听收音机”,如此等等,但是它写得如此花里胡哨,我开始的时候都看不明白,等我终于把它破译了之后,它却空无一物。
那次会,只有一件事儿,是愉快的或者好玩的。在这次会议上,每一个家伙在每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太重要了,他们弄了速记打字员在那儿,把每一件混账事儿都打了下来。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那个速记打字员走到我这儿说:“您什么职业?肯定不是个教授。”
“我是个教授。”我说。
“什么教授?”
“物理学的——科学。”
“哦!难怪。”他说。
“难怪什么?”
他说:“您瞧,我是速记打字员,把人家说的什么都打下来。别的伙计讲话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就打什么,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每次您站起来问个问题,或者说什么东西,我完全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明白问题是什么,您说的是什么——因此,我还以为您不可能是教授!”
到了一定的时候,有个特别的晚宴,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很好的、很犹太的人,发表了演说。那是个很好的演说,他也很会说话,因此,尽管在我现在说这事儿的时候,那演讲听起来是发疯,可在当时,他的主要思想,听起来却是完全明显而真实。他讲的是各国福利上的巨大差别,这引起了嫉妒,导致了冲突,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原子武器,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我们都在劫难逃,因此追求和平的正确出路,在于确保每个地方不存在差别,因为在美国我们有的东西过多了,我们就应该把几乎全部的东西都放弃,都送给别的国家,直到大家扯平了为止。大家都在听这个,我们全都充满了牺牲的情感,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办。但是,在回住处的路上,我恢复了理智。
第二天,我们小组的一个家伙说:“我认为昨天晚上那个演讲,太好了,我们大家都应该签字认可,它应该成为我们这次会议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平均分配一切东西的这一思想,我开始说,它建立在这么一种理论上:全世界只有X量的东西,不知怎么我们首先从比较穷的国家那儿把东西抢了过来,因此,我们应该把东西还给人家。但是,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国家差别的真正原因——即用来种植作物的新技术发展,用来种植作物和做其他事情的机械发展,以及所有这些机器需要资本的集中这一事实。问题不在于东西,而在于制造东西的力量,那才是重要的。但我现在意识到,那些人不在科学之中,他们不理解这个。他们不理解技术;他们不理解自己的时代。
这次会议使我神经大受刺激,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女孩儿不得不让我安静下来。“瞧你,”她说,“你都哆嗦呢!你绝对变成了个大傻瓜!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别把事儿看得那么严重。退后一步,把事儿看清楚了。”于是我就思考这次会议,它多么傻,它多么坏。但是,如果有人要求我再参加那种东西,我将羞臊得像个疯子似的逃之夭夭——我的意思是,零!不!绝对不参加!直到今天,我仍然收到参加那种玩意儿的邀请函。
到最后评价这次会议的时候,别人都说,他们从本次盛会得到了那么多的教益,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诸如此类。他们问我的时候,我说:“这次会议,比罗尔沙赫氏测试(Rorschach test)
 还糟糕:那儿有一团毫无意义的墨迹,别人问你,你认为你看到了什么,等到你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吵闹!”
还糟糕:那儿有一团毫无意义的墨迹,别人问你,你认为你看到了什么,等到你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吵闹!”
比这更坏的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要去开另外一个会议,但这次有公众参加进来,负责我们小组的那个家伙有胆量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收获,再说也没有什么进行公众讨论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干脆告诉公众我们已经得到的收获。我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我认为我们一点混蛋收获也没有嘛!
最后,在讨论我们是否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在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的途径这一问题——我们的第二个基本“问题”——的时候,我说,我注意到某种有意思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谈了我们所认为的“关于平等的伦理学”是个什么东西,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谈的,却不在意别的家伙的观点。比方说,这位历史学家建议,理解伦理学问题的途径,是历史地看那些问题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国际律师建议,搞这个途径,是看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怎么发出不同行动的,以及是怎么做安排的;这位耶稣会牧师,总是提起“知识的分崩离析”;我呢,作为科学家,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单独来处理,在方式上应该像伽利略做实验的那种技巧;如此等等。“因此,在我看来,”我说,“我们还完全没有什么对话。恰恰相反,除了一团乱麻,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难道您不认为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
“啊,那个,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或者说……”我搞不明白这怎么扯上了“秩序是从混乱中产生的吗”这个问题。是,不,这怎么说呢?
在那次会上,傻瓜有的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这种傻瓜,能把我逼得上墙。一般的傻瓜,无可指责;你可以跟他们谈,努力帮助他们把事儿搞明白。可自负而浮夸的傻瓜——就是那种又傻、又掩盖其傻,并且一门心思地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傻瓜,他们连哄带骗,以此显示他们多么有能耐——那个,我无法忍受!一般的傻瓜,并不装模作样;诚实的傻瓜,无可指责。但是,一个不诚实的傻瓜,可怕!那就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收获,自负而浮夸的傻瓜,都成串儿了,我心烦意乱。我再也不让自己心烦意乱了,因此我再也不参加跨学科会议了。
在开会期间,我待在“犹太教神学院”,在那里,年轻的拉比们——我认为他们是正统教派——在做研究呢。因为我有犹太背景,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犹太法典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但我从来没看过犹太法典。这法典很有意思:大开本,页角上的小方框里,是原文的犹太法典,然后在一种L形的页边上,围绕着这个方框,是不同人写的注解。犹太法典已经发展了,一切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讨论得非常细致,用的是一种中世纪的推理方式。我认为,那些注解,到13或14或15世纪,就停了——没有什么现代的注解。犹太法典是一本奇书,是一只装着各种各样事儿的大罐子:琐屑的问题,困难的问题——例如,关于教师的问题,如何教学的问题——接着又是一些琐事,等等。学生们告诉我犹太法典从来没有被翻译为其他文字,这事儿透着怪,因为这书是这么有价值。
有一天,两三个年轻的拉比来找我,说:“我们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上,要是不知道科学的事情,我们学不成拉比的,因此我们想问您一些问题。”
当然,发现科学的地方,何止千万,哥伦比亚大学就在附近嘛,但对他们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我感兴趣。
他们说:“那个,比方说,电是火吗?”
“不是,”我说,“但……干吗问这个?”
他们说:“犹太法典里说,安息日汝不得举火,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安息日我们可以用电器吗?”
我深感震惊。他们对科学完全不感兴趣!科学影响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是他们或许能更好地解释犹太法典!他们对外部世界、对自然现象,没兴趣;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儿,是消化犹太法典提出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猜是安息日——我去用电梯,有个家伙站在电梯旁边。电梯来了,我进去,他也跟我进来了。我说:“几楼?”我伸手要去按电钮。
“不,不!”他说,“该是我为您按电钮的。”
“什么?”
“是的!这儿的小伙子们说,安息日是不可以按电钮的,因此我一定要为他们按电钮。您知道,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按电钮没关系。我站在电梯边儿,他们告诉我几楼几楼,我就为他们按电钮。”
唉,这真是让我闹心,于是我决定在一场逻辑讨论中把这些学生置于尴尬境地。我是在一个犹太家庭长大的,因此我知道他们用的那种吹毛求疵的逻辑,我想:“这是个乐子!”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就会问:“犹太观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采纳的观点吗?因为,如果不是,那么这种观点肯定就不是对人类真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们会说:“是的,犹太观点任何人都可以采纳。”
然后,我会牵着他们的鼻子再走上一圈儿,我问:“一个人雇另一个人来做对自己来说是不道德的某事,是道德的吗?比方说,你们会雇一个人来为你们抢劫吗?”慢慢地,非常小心地,我不停地把他们往套子里引,直到我把他们——逮住!
你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都是犹太教学生,是吧?他们比我强十倍!他们一看出我能把他们赶到窟窿里,就挣扎、扭动、挣扎——我记不得他们是怎么挣扎、怎么扭动的——挣脱了!我还以为我遇到了个原创的观点呢——呸!他们的观点,在犹太法典里,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时代了!他们收拾我,就跟吃馅儿饼那么容易——他们完全挣脱了困境。
最后,我想让这些犹太教学生确信,他们在按电梯按钮时出现的那种让他们不安的电火花,不是火。我说:“电不是火。电不是化学过程,火是。”
“哦?”
“当然,在火中的原子之间,是有电的。”
“啊哈!”他们说。
“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其他现象里,都有电。”
我甚至还建议了一个消除火花的可行办法。“如果那个东西让你闹心,你可以在开关上加一个电容器,那样的话,电断开、接上,都不会有任何火花——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这实在叫人失望。他们待在我这儿,慢慢缓过神来,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犹太法典。你想想啊!身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时代,那些家伙在研究,以便走向社会,去干点事儿——去当个拉比——他们想到科学或许有意思的唯一方式,是他们那些古老的、狭隘的、中世纪的问题,稍稍受到了某种新现象的骚扰。
当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儿,也值得在这里提一提。犹太教学生和我仔细讨论过的问题,有一个是为什么在某些学术的事情上,比方说理论物理学方面,犹太孩子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人口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犹太教学生认为,其原因在于,犹太人有着尊重学习的历史:他们尊重他们的拉比,拉比实际上是教师,他们也尊重教育。犹太人一直在家庭里把这种传统传承了下来,因此,如果一个小伙子是个好学生,那他就和好的足球队员一样好,即使不更好。
就在当天下午,他们提醒我这种说法有多么真实。我应邀到了一个犹太教学生的家里,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她刚从华盛顿回来。她两手一击,喜出望外,说:“哎哟喂!我这一天,算是功德圆满了。今天,我见到了一位将军,还有一位教授!”
我心知肚明:没有多少人认为见到一位教授,和见到一位将军一样重要、一样好。因此,我猜,学生的那种说法,真有道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