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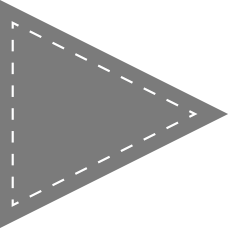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但那是艺术吗?
但那是艺术吗?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上打邦戈鼓,打得蛮热闹。有个家伙,特受鼓声的感染。他进了洗澡间,把衬衫脱了,用剃须膏在胸膛上画了个可笑的图案,出来发疯地跳,耳朵上还挂着樱桃。很自然,这个发疯的傻瓜和我立刻成了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杰瑞·左提安(Jerry Zorthian),他是个艺术家。
关于艺术和科学,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说的是类似这么一种意思:“艺术家,找不着北:他们没什么主题!他们习惯于宗教主题,但他们丢失了自己的宗教,现在他们什么也没了。他们不懂这个他们身在其中的技术世界;对于那个真实世界的美,那个科学世界的美,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心里没什么东西好画的。”
杰瑞会这么回答:艺术家不需要物理的主题;可以用艺术来表达的情感,多了去了。此外,艺术可以是抽象的。不仅如此,科学家把自然打碎了,把它变成了数学方程式,破坏了自然美。
有一次,我到他那儿给他过生日,那一次的这类愚蠢争论,一直延续到下半夜三点。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把他叫醒了:“听着,杰瑞,”我说,“我们这么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原因是,关于科学,你啥也不知道,我呢,关于艺术,也啥也不知道。因此,每个星期天,我们轮换着,我给你上科学课,你给我上艺术课。”
“那好,”他说,“我教你怎么画画。”
“那不可能。”我说,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只会画沙漠上的金字塔——主要是直线构成的嘛——我时不时地想试着画棕榈树,加上个太阳。我绝对无才。跟我坐一块儿的那家伙,跟我一样有才华。要是让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他画的那东西,是两个脏乎乎、扁歪歪的椭圆形,像两个摞在一块儿的轮胎,轮胎里头伸出根杆子,杆子头儿变成了个绿色的三角形。我们得假定那是棵树。因此,我跟杰瑞打赌,他教不会我画画。
“当然了,你得用功啊。”他说。
我保证用功,但还是打赌他教不会我画画。我非常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传达一种感情,我对这个世界的美的感情。那很难说得清楚,因为那是感情。那种感情,跟宗教感情差不多,这个宗教和一个控制着整个宇宙的神有关系。事物显得这么不同,行为也这么不同,可在“布景背后”,它们都受着同一种组织、同样的物理规律的支配,思想此事,你会感觉出有一种普遍性。这是对自然的数学之美的赏识,是对这种美的工作方式的欣赏,是对我们从原子之间内在作用的复杂性当中看出来的意识;是一种关于这种美有多么戏剧化、有多么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敬畏之感——科学的敬畏——我觉得可以通过绘画,把这感觉传达给别人,别人也有这种感情的。我的画可以提醒他,让他暂时记起宇宙的壮丽。
原来,杰瑞是个好老师。他首先告诉我说,回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于是我就想画一只鞋;然后画盆花。画得乱七八糟!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给他看了我的习作:“哦,你看!”他说。“你看,这靠后的这个地方,花瓣的这个线条,没碰着叶子。”(我本意是要它碰着叶子的。)“这很好哇。这是一种表现深度的办法啊。你很聪明。”
“你没把全部的线条都搞得一般粗(我不是故意那么做的啊),是很好的。全部线条都一般粗,那种画,发呆。”他又继续说了类似的一些话:我什么都想错了啊,他习惯于以积极的方式来教我点儿东西。因此,我坚持努力,渐渐有点儿起色,但我怎么也不满意。
为了练习得更多,我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函授学校的班,“国际函授学校”的班,我不得不说这个学校好。他们让我开始画三棱锥和圆柱体,还加上阴影什么的。我们涉猎了许多领域:素描,蜡笔,水粉还有油画。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却渐渐疲塌了:我给他们画了一幅油画,但总也没寄出去。他们不停地给我来信,敦促我不要半途而废。他们非常好。
我一直都在练习画画,对它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在开会,会却开得不顺利的时候——像那次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到加州理工学院来,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该不该搞一个心理学系——我就画别人。我带着一打子小开本的纸,走到哪儿都练习画画。因此,杰瑞教我的时候,我很用功的。
另一方面,杰瑞的物理学学得并不多。他心猿意马。我想教他电学和磁学的什么东西,但我一提起“电”,他就告诉我,他那个转不起来的电动机的什么事儿,他怎么或许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看看电磁铁是怎么工作的,我就卷了个小线圈,把一根钉子系在一根线上,我给它通上电,钉子呢,摇摇晃晃地就进了线圈里,杰瑞说:“噢噢!就跟性交似的!”只好作罢了。
因此,现在我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究竟他是个比我好的老师,还是我是个比他好的学生。
想让一个艺术家来赏识我对自然的那种感情,还想让他能描绘这种感情,这个念头,我打消了。现在我就得加倍努力,学习画画,那样我就能自己来办了。这是个野心勃勃的事业;这个想法,我谁也没告诉,因为我多半是永远也做不到。
在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一个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你应该上帕萨迪纳艺术博物馆那儿。他们那儿有绘画班,有模特呢——裸体模特。”
“不去,”我说,“我画得不够好,我会很尴尬。”
“你很可以了啊;你应该看看别人画得什么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那儿去了。第一节课上,他们说,要准备好印报纸的那种纸——大幅的纸,跟报纸那么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铅笔和炭笔。第二节课,一个模特进来了,她开始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画这个模特,到我才画了一条腿的时候,十分钟用完了。我往四周看了看,人人都已经画好了一幅完整的画,背后还加了阴影呢——整个完工了。
我明白自己是半瓶子醋。可是,到最后,那个模特要摆三十分钟姿势。我画得很卖力气,费了吃奶的力,倒也能画完她整个的轮廓。这次,我有了一半儿的希望。因此,这次我也不把我的画盖住了,因为我已经画完了前一次该画的那些。
我们转来转去,看看别人画得如何,我发现了他们的真本事:他们画的那个模特,惟妙惟肖,明暗有度,连坐着的那个椅子上的那个小挎包也画上了,台子也画上了,什么都画到了!他们手执炭笔,嚓、嚓、嚓、嚓,一气呵成啊,我琢磨着,我是没指望了——彻底没指望了。
我回去把我的画盖上了,它只画了几根线,挤在报纸的左上角那儿——那之前,我只在书本大小的纸上画——但班上的人,都在近旁站着呢:“噢,看看这个,”他们当中有个人说,“笔笔不虚啊!”
我不确切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得到的鼓励,足够让我下次课还来。与此同时,杰瑞不停地告诉我,画得太满,没任何好处。他告诉我不必在意别人,因此他告诉我,他们也不怎么样。
我注意到,那个老师没对大家说得太多(他只告诉我,说我的画在那页上太小了)。他却努力鼓励我们实验新方法。我想起了我们是怎么教物理的:我们有那么多技巧——那么多数学方法——我们从来没停止告诉学生怎么做事情。另一方面,这位画画的老师,怵于告诉你任何事儿。如果你的线条笔力太重,这个老师不会说:“你的线太重了啊。”因为有些艺术家琢磨出了一种办法,能用很重的线条搞出了不起的画来。老师不想把你推到某种特别的方向上去。因此,怎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下达指令的方式来和学生交流,绘画老师就有这种麻烦了。物理老师的麻烦,是总教怎么解决物理问题的技巧,却不教精神。
他们总告诉我要“放松”,要无拘无束地画。我琢磨着,这并不比告诉一个掐着方向盘学开车的人“放松”,更起作用。那么说,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你知道怎么仔细地弄它的时候,你才开始放松。所以,我抵制这种没完没了的叫人放松的玩意儿。
他们发明的一个叫我们放松的练习,是画的时候,不看纸。你的眼一直盯着模特;在纸上画线条的时候,只看着她,不看你画的那些东西。
有个家伙说:“我就是忍不住要看。我没办法不自欺欺人。我敢打赌,大家都在自欺欺人!”
“我不自欺欺人!”我说。
“哇噢,装蒜!”他们说。
我把练习做完了,他们过来看我画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发现,确实,我没自欺欺人;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铅笔尖儿就断了,纸上除了压痕儿,空空如也。
等我把铅笔弄得好用了,我又来试。我发现,我的画有某种力度——一种可笑的、毕加索式的力度——这让我自己很得意。我觉得这画好,原因是,我知道那样画,是不可能画好的,因此呢,你不必画好——那才是这种放松练习的目的所在。我本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信笔涂鸦”,但实际上是别担心画出来的画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这个班里,进步不小,我感觉颇为不错。到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的模特都是身量庞大得走了形的那种,画这种模特很好玩儿。可是,最后一堂课,我们的那个模特却是个体态匀称、金发碧眼的妞儿,比例非常完美。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仍然不知道怎么画画:我能画出来的东西,怎么看也不像这个漂亮的女孩儿!画别的模特,你画什么东西,如果画得大点儿或者小点儿,无所谓,因为反正是个走形儿。但是,如果你画的这个东西装配得这么好,你就不能自欺欺人了,一定得画好才是!
有一次在下课的时候,我无意听到那个真会画画的家伙问这个模特,她能不能单独为他摆姿势。她说,可以。“那好。但是,我还没有画室呢。我必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琢磨着,我可能从这个家伙那儿学到不少东西;除非我想点儿办法,我就没机会再画这个体态匀称的模特了。“对不起,”我对他说,“我房子楼上有个房间,可以用做画室。”
他们俩都同意。我把这家伙的几幅画拿给杰瑞看,但他吓呆了。“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啊。”他说。他努力解释为什么,但我实在是听不懂。
在开始学画之前,我从来没有太大的兴趣去看看艺术。对艺术的东西,我不怎么欣赏;要说欣赏,也不经常,比方说,那次我在日本的一个博物馆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幅在泛黄的纸上画的竹子。在我看来,这画的妙处,在于它不过是寥寥几笔,但它同时又是竹子,这二者之间有一种完美的平衡——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把它看作笔触,一会儿把它看作竹子。
绘画班之后的那个夏天,我在意大利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我想看看西斯廷教堂。早晨我早早就去了,比任何人都先买了票,然后一开门,我就跑上台阶。因此我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时光,在别人来之前,在宁静的敬畏中,看着这整个教堂。
游客们很快就来了,一群一群的人到处乱转,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的。我到处走,看了一阵子天顶。然后,我的视线稍微向下移动了一点儿,我看到了一些巨幅的、装了框子的画,我想,“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
不幸的是,我把导游手册忘在旅馆里了,但我心里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不出名了;这些画不怎么好啊。”但是,我接着看另外一幅,我说:“哇噢!那幅好啊。”我看了另外那些。“那个也好,那个也是一样,但那个稀松。”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拿得准,这些画都好,只有两幅是例外。
我到了一个叫“拉菲尔”的地方——拉菲尔展室——我注意到了相同的现象。我心里想,“这拉菲尔,参差不齐啊。他画得不总是好。有的时候,他很好。有的时候,就是垃圾嘛。”
等我回到了旅馆,我那本导游手册,关于西斯廷那部分,说:“在米开朗基罗的那些画下面,有十四幅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佩鲁吉诺(Perugino)的”——这都是大艺术家——“还有两幅是什么什么人的,没什么重要性。”这对我来说,可是太兴奋了,我也认得出来一个美的艺术品和一个不美的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啊,虽然那究竟是怎么个区别,我也说不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总是认为你明白自己做的事儿;可是,艺术家,说“那个很伟大”,“那个不怎么样”,过后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像杰瑞对我带给他看的那些画所发表的评论那样,你就信不过他们了。但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也能这么干!
拉菲尔展厅,有个秘密,原来是这样:只有一部分绘画,才是大师手笔;其余的,是学生弄的。我喜欢拉菲尔的那些。这让我对自己的艺术欣赏力自信大增。
不管怎么说,艺术班的那个家伙和那个体态匀称的模特,来过我家好几次,我想画她,我想学他。做了许多习作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觉得实在好的画——她的头像——第一次成功,我很兴奋。
我有了足够的自信,问我的一个叫史蒂夫·德米垂阿德(Steve Demitriades)的老朋友,可否请他漂亮的妻子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我把肖像送给他。他笑了。“如果她愿意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不介意,哈、哈、哈。”
我为她的这幅肖像工作得很卖力,等他看到了,他完全站到了我的立场上:“画得可真漂亮啊!”他叫起来。“你能不能把它用照相机照下来,多复制几份?我想寄一份给我在希腊的妈妈!”他妈妈从来也没见过儿媳妇。想到我已经进步到有人要我的画的地步,这事儿来劲啊。
相似的一件事儿,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家伙搞的一次小型艺术展览会上,我贡献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在画上贴个价格标签。”
我想:“别犯傻了!我不打算卖啊。”
“那会使这个展览更有意思一点儿嘛。如果你不是舍不得的话,那就弄个标签上去。”
展览之后,那个家伙告诉我,一个女孩儿已经买了我的一幅素描,还说想跟我说说话,以便发现这画的更深的寓意。
那画名为“太阳磁场”。为了这幅特别的画,我借了一幅在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拍的漂亮的日冕照片。因为我明白太阳磁场是怎么把火焰拽起来的,而且在当时,我琢磨出了一种技法,来画磁力线(跟女孩儿飘动的长发相似),我想画画家们都没想到要画的某种漂亮的东西:磁场中的那种相当复杂和翘曲的线,在此处聚拢,却在彼处散开。
我把这些都解释给她听,还给她看了使我有了这个主意的那幅照片。
她告诉了我这么个故事:她和她丈夫去看过展览,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幅素描。“我们干吗不买下来?”她建议。
她丈夫,是那种从来也不会当机立断的人。“让咱考虑考虑再说吧。”他说。
她想起来,再过几个月,就是他的生日,于是她当天返回,自己买了。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心情抑郁不振。她终于弄明白了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觉得,把那幅画买来给她,那才好;但是,等他回到展览会,有人告诉他,那画已经卖出去了。因此,她就把这事儿秘而不宣,等他过生日的时候,好给他个惊喜。
我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启示,这启示对我还是很新鲜的:起码从某些方面说,我终于理解了艺术确实有什么用处。艺术给某个单个的人以快乐。你能制造出一个东西,有人宝贝之至;他们或者沮丧,或者愉快,都是因为你制造的这破玩意儿!在科学中,那是一种普遍而大的东西:你不知道直接欣赏它的那些单个的人。
这个使我明白了这么一件事儿:卖画,并非为钱,而是为了踏踏实实地知道,那画实在想要属于一个人;那个人,要是得不到它,就茶饭不香。这事儿透着好玩。
因此,我决定卖画。然而,我却不希望大家来买我的画,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这个物理学教授没画画的本事,这可够你咂摸味儿的,所以我就起了个假名字。我的朋友建议我叫“奥菲”(Au Fait),在法语里是“办妥”之意,我却把这个名字写成“阿飞”(Ofey),这刚好就是黑人送给“白鬼”(whitey)的那个称呼。但我毕竟是个白鬼,所以正合适。
我的一个模特,想让我给她画幅画,但她没那份钱。(模特没钱;如果她们有钱,就不干模特这行了。)如果我给她一幅画,她就愿意免费为我摆三次姿势。
“事儿得倒过来,”我说,“如果你白为我摆一次姿势,我会给你三幅画。”
她把我给她的画中的一幅,挂在她的小房间的墙上,很快,她的男朋友注意到了。他太喜欢这画了,他想出钱为她画一幅肖像。他要付我60块钱。(我现在涨了行市了。)
她有个念头,想当我的经纪人:她到处兜售我的画,能赚点儿小小的外快,她会说:“在阿尔塔迪纳,新出了一位艺术家……”身处另一个世界中,这堪为乐事啊!她做了一番筹划,把我的一些画摆到了“小公牛”,这是阿尔塔迪纳最雅致的一家百货商店。她和艺术部的那位女士来挑了我的几幅画——是几幅我早先画的植物(我不喜欢)——全都装了画框。然后呢,我得到了“小公牛”的一份签了字的文件,说他们接受委托,取走什么什么画。当然,没有卖掉任何一幅,但我是大大成功了:我的画在“小公牛”那儿卖啊!把画放在那儿,也是乐事啊。这样,有朝一日我就可以说,在艺术世界里,我曾经达到那样一种成功的巅峰。
我大多数的模特,是通过杰瑞搞到的,但我也想自己找一些模特。每当我遇到个年轻女人,看样子好像对画画感兴趣,我就让她为我摆姿势。最后的结果,总是我画她的脸,因为我不怎么知道如何处理裸体这个主题。
有一次我在杰瑞那儿,我对他妻子达布妮(Dabney)说:“我没办法让女孩儿们光着身子摆姿势,我不知道杰瑞是怎么弄的!”
“哈,你从来也没有要求她们那么做?”
“哦!我连想都没那么想。”
我遇到的下一个女孩儿,想要她为我摆姿势,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我问她愿不愿意为我裸体摆姿势。“当然。”她说,事儿就这么成了!因此,这事儿容易。我猜,我心里杂念太多,以为那么要求人家,不知道怎么就不对。
到现在,我已经画了很多画,我已经到了这么一种造诣,最喜欢画裸体。据我所知,严格来说,那不是艺术;那是一种混合物。谁知道这混合物中的各种物质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通过杰瑞认识的一个模特,曾经是《花花公子》杂志的花花女郎。她身材颀长,美艳无比。然而,她觉得自己太高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女孩儿,瞧她一眼,都嫉妒得要死。在她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上半身得弯着进去。在她摆姿势的时候,我想教教她,请她站起身来,因为她是如此优雅,如此耀眼。我终于说动她照着我说的做了。
她接着就有了另一种担忧:她的腹股沟那儿有些“凹坑儿”。我不得不找出一本解剖学书,给她看那是肌肉与肠骨的接合部,还为她解释,你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那些“凹坑儿”的;要想看到,那必须一切都刚好合适,完完全全地合乎比例,就像她那样。我从她那儿了解到,每个女人,无论她们多么漂亮,都担心自己的长相。
我想用彩色为这个模特画一幅画,用粉蜡笔,仅仅是为了做实验。我觉得应该先用炭笔勾勒轮廓,再用粉蜡笔覆盖。在我用炭笔勾完了之后,我不操心这画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了,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画过的最好的画之一。我决定,这样就行了,别在这幅画上用粉蜡笔了。我的“经纪人”看到这画,想把它带走。“这幅画,你卖不出去,”我说,“它画在报纸纸上啊。”
“哦,别担心,”她说。
几个星期后,她回来了,带着这幅画,用漂亮的木头画框给装了起来,红色的镶边,金色的边框。这事儿够滑稽的,一定会让一般的艺术家们闷闷不乐——你给一幅画装了框子,这对它的改善也太大了。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某位女士,对这画整个着了迷,我的经纪人就把这画送到画框师那儿了。他告诉她,有一种特别的技术,来装画在报纸上的画:用塑胶使之饱和,这么捣鼓,那么捣鼓。因此,这个女士必得遭受我画的这画带来的这些麻烦,然后呢,她还要让我的经纪人把画带给我看。“我想,这位艺术家或许想看看,它装了画框的时候,有多么可爱。”她说。
我肯定想看。有人从我的一幅画中得到了这种直接的快乐,这又是一个例子。因此,卖画,还真是件乐事儿。
有那么一段时间,城市里有脱衣舞饭店:你可以到那儿吃午饭或晚饭,女孩儿们光着上半身跳舞,跳着跳着,就一丝不挂了。有这么一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也就是2500米,因此我经常到那儿。我坐在包厢里,在圆齿边线的纸上做一点儿物理计算;有的时候,我画一个跳舞的女孩儿,或者画一个顾客,仅仅为了练习。
我妻子格温妮丝(Gweneth),是个英国人,我到这么个地方,她态度端正。她说:“英国男人都有俱乐部可去。”因此,那儿就跟我的俱乐部似的。
那地方墙上挂着一些画,但我不是太喜欢那些画。那是用荧光性的颜料画在黑色的天鹅绒上的——有那么点儿丑——画的是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孩儿什么的。我有一张相当不错的画,那是我用我的模特凯西画的,于是我就把这画送给了饭店老板,好挂在墙上,他很高兴。
给了他这么一幅画,结果产生了一些有用的结果。老板对我非常友好,我的饮料一直是免费的。现在,我每次到这个饭店,一个女服务员就给我端来免费的“七喜”(7-Up)。我一边看女孩儿跳舞,一边做做物理学研究,备备课,或者画点儿什么玩意儿。如果我有点儿累了,我就看一会儿节目,回头再做点儿研究。老板知道我不想有人打扰,因此,如果有个喝多了的主儿凑过来,要跟我说话,立刻就过来一个女服务员把他支走。如果有个女孩儿过来,他就不多事儿了。我们关系很好。他叫乔诺尼(Gianonni)。
我的画在那儿展览,有另一个效果,大家都问他,这画是怎么回事儿。有一天,一个家伙走到我这儿来说:“乔诺尼告诉我,那画是你画的。”
“是啊。”
“很好。我想请您画幅画。”
“行啊;你喜欢什么?”
“我要的这幅画,得画一头长着男人头的公牛,正在向一个裸体女斗牛士冲击。”
“那个,呃,要是我知道这幅画派什么用处,那会对我有点儿帮助。”
“我的开业典礼用得着。”
“什么买卖的开业典礼啊?”
“按摩廊。你知道的,小私密房间,按摩女——明白这事儿?”
“对,我明白这事儿。”我不想画一头长着男人头的公牛,正在向一个裸体女斗牛士冲击,于是我就想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那会对顾客留下什么印象?那会让女孩儿们有什么感觉?你想过吗?男人们到那儿去,你用这画,把他们搞兴奋了。你希望他们那么对待那些女孩儿?”
我没把他说服气。
“假定警察进来了,他们看到这幅画,而你声称这是一家按摩廊。”
“对对对,”他说,“你说得对。我改主意了。我想要的这幅画嘛,如果警察看它,对一个按摩廊来说,那没什么不合适的;但是,顾客一看,他就会明白点儿事儿。”
“那好。”我说。我们商定了60块钱的润笔,我就开始画这画。首先,我得琢磨,这画怎么个画法。我想啊、想啊,觉得还不如当初就依了他,干脆画个裸体女斗牛士得了!
最后,我琢磨出了怎么来画:我画个想象中的罗马年轻女奴,在为某个重要的罗马人按摩——或许是个元老院议员。因为她是个女奴,她脸上就有某种表情。她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儿,而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我在这画上花了不少劳动。我让凯西当模特。后来,我找到了另一个模特来画那个男人。我做了许多研究,模特费很快就已经到了80块。我不在乎钱,我喜欢受托作画这一挑战。最后,我画完了一幅画:一个肌肉壮实的男人,躺在一张桌子上,女奴在给他按摩。她穿着某种长袍,盖住了她的一个乳房,另一个乳房裸着,我把她的那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表现得恰如其分。
我正准备着去交差,把我的大作给按摩廊送去,乔诺尼却告诉我,那家伙给抓起来了,下了大牢了。于是我就问这个脱衣舞饭店的女孩儿,帕萨迪纳这方圆之内,有没有好的按摩廊愿意挂我这幅画。
她们告诉我帕萨迪纳和周围几家按摩廊的名字和地点,还告诉了我这么些事儿:“如果你到了什么什么按摩廊,就说要找弗朗克——他是个挺不错的家伙。要是他不在,那就别进去。”还有:“别搭理艾迪。艾迪可不懂一幅画有什么用处。”
第二天,我把画卷起来,把它放在我汽车的后座上,我妻子格温妮丝祝我好运,我就出发去访问帕萨迪纳妓院,去兜售我的画。
就在去我名单上的第一家妓院的时候,我心里想:“你知道,我到其他地方之前,我应该先到原先那家按摩廊,说不定那儿还在营业呢,说不定新经理也要我的画呢。”我就去了那儿,敲门。门开了个缝儿,我看到了女孩儿的一只眼。“是熟客吗?”她问。
“不,不是,可你不想在门厅里挂一幅挺合适的画吗?”
“抱歉,”她说,“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位艺术家为我们画画,他眼下正画着呢。”
“我就是那位艺术家,”我说,“你们的画,画好了!”
原来,那家伙在入狱之前,把我们的安排跟他老婆说了。于是,我就进去了,给她们看这幅画。
这家伙的老婆和他妹妹,现在操持着这个地方,不十分喜欢这画;她俩想让女孩儿们也来参谋参谋。我把画挂在墙上,就挂在休息室里,姑娘们都从后面不同的房间里过来看,并且开始发表评论。
有个女孩说,她不喜欢女奴脸上的表情。“她看起来,不怎么乐,”她说,“她该笑才对。”
我对她说:“告诉我——你给一个家伙按摩的时候,可他连看你也不看,你还会笑?”
“哦,不!”她说,“我觉得我真真儿地就是她那副样子!但把这画挂起来,不是个事儿啊。”
我把画留在她们那儿了,在我为这画反反复复担心了一个星期之后,她们决定不要这画了。原来,她们不想要这画的真正原因,是那个裸着的乳房。我解释说,我画这画,要比原来要求的节制得多,但她们说她们对这画的看法,和那个家伙的看法有所不同。我想,这可够讽刺的,开了这么一家买卖的这些人,对一个裸露的乳房如此谨小慎微,真可博人一笑,我就把画拿回家了。
我那位做生意的朋友,达德利·赖特(Dudley Wright),看到这画,我就把这故事讲给他听了。他说:“你应该把价码提高到三倍才是。艺术这玩意儿,真没人知道它值多少,因此呢,大家就想啦,‘要是价码高,它的价值想必就大!’”
我说:“你疯了!”但是,仅仅是为了逗乐儿,我买了一个20块钱的画框,把这画装起来,好准备着卖给下一个顾客。
有个家伙,在气象台干活儿,看到了我给乔诺尼的那幅画,问我有没有别的画。我邀请他和他老婆,到我家楼下的“画室”来,他们问了那幅新装了框子的画。“那幅嘛,200块。”(我把60块乘以3,外加20块的画框费。)第二天,他们回来把那幅画买了。这就是说,按摩廊的画,最终挂在了一个气象预报员的办公室里。
有一天,一个警察突袭了乔诺尼的脱衣舞饭店,逮捕了几个脱衣舞女。有人想要乔诺尼停止脱衣舞表演,乔诺尼不想停。于是就起了一场大官司;这事儿,当地的几家报纸上都登着呢。
乔诺尼四处奔走,求顾客们为他作证,支持他。人人都找借口:“我开了一家夏令营,要是家长们知道我到这么个地方来,他们就不会再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了……”或者:“我做的是什么什么买卖,要是公众知道我溜到这儿来,我们会失去顾客的啊。”
我心里想:“这里只有我是自由人了。我没什么借口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愿意看到它继续开下去,我看不出脱衣舞有什么不对的。”因此,我对乔诺尼说:“好的,我很高兴为你作证。”
在法庭上,这个大问题是,脱衣舞对社区而言,是可取的吗?——社区标准允许脱衣舞吗?
辩护律师试图把我弄成个社区标准的专家。他问我,我是否也去别的酒吧。
“去的。”
“平均而言,您每星期去乔诺尼饭店几次?”
“一个星期五六次吧。”(这一点都记录在案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这位物理教授,一个星期六次去看脱衣舞。)
“乔诺尼饭店的顾客,都包括社区的什么样的人?”
“几乎什么人都包括:有一些干房地产的家伙,有一个家伙是市府的,加油站的一群工人,工程公司的一些家伙,一个物理学教授。”
“既然这个社区许多阶层的人都在看脱衣舞,都喜欢看,那么,您是否会说脱衣舞娱乐活动,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我倒想知道,你说‘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什么意思。没什么事儿,人人都接受。因此,为了使‘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说法成立,社区人口接受某事必须是多大百分比才成?”
这位律师建议了一个数字。其他律师反对。法官宣布休庭,他们在密室里待了15分钟,这才决定“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意思是社区50%的人接受。
尽管事实上是我让他们把事儿弄得准确了,我却没有精确的数字可作证据,于是我说:“我相信社区50%以上的人,都接受脱衣舞,因此,脱衣舞对社区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乔诺尼暂时输掉了官司,但他的这个案子和与此相似的另一个案子,最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与此同时,他的饭店还在经营着,我得到了更多的“七喜”饮料。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做出了一些努力,以便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有人捐钱把一座破旧的植物科学大楼,改造成了艺术工作室。设备和材料买来了,供学生们使用,他们还从南非雇了一个艺术家,来组织和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的艺术活动。
各色人等都来教课。我把杰瑞·左提安弄来讲素描课,别的一个家伙来教版画,我想学这个。
这位南非艺术家来过我家一趟,看了我的画。他说,他认为举办一次个人画展,是很有意思的。这次,我可自欺欺人了:如果我不是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大家就不会觉得我的画有价值。
“我的一些比较好的画都卖了,给那些人打电话,我会觉得不安。”
“你不必担心,费曼先生,”他给我打气儿,“电话不必你打。一切都由我们来操办,画展一定会办得像模像样,没有差错。”
我给了他一个名单,那些人,都买过我的画,他们很快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们了解到您那里有一幅阿飞的画。”
“啊,是的!”
“我们正在筹划一次阿飞画展。我们在考虑,您是否可以把它暂时借给我们一用。”当然,他们很乐意借。
画展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俱乐部“雅典娜神庙”的地下室里举行。一切都跟真事儿似的:所有的画都有标题,那些受托从拥有者那儿借来的画,都有所有权确认说明:例如,“乔诺尼先生热情出借。”
有一幅,画的是艺术班的那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模特,那本来是我打算研究阴影效果的:我把灯光放在她腿的高度,放得斜一点儿,灯光向上射。她坐着的时候,我想照实际情形画阴影——她的鼻子颇不自然地在她的脸上投下了一道影子——这不是那么难看。我把她的躯干也画得很好,因此你也可以看到她的乳房,以及乳房投下的影子。我把这幅画和其他展出的画凑在一块儿,名之曰“居里夫人在观察镭的辐射”。我意在传达的信息是:没人把居里夫人看成个女人,没人把她看成一个秀发飘然、赤裸着乳房的女性。大家一看居里夫人,只想着镭。
展览之后,一位著名的工业设计家亨利·德瑞法斯(Henry Dreyfuss),邀请了各色人等到他家参加一个招待会——那个捐钱赞助艺术的女人,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他妻子,等等。
一个艺术爱好者也来了,开始跟我聊:“告诉我,费曼教授,你画画,是用照片还是用模特?”
“我从来都是直接用模特来画。”
“呃,您是怎么让居里夫人为您摆姿势的?”
大约在那个时候,“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有个看法和我的相似:艺术家对科学一点儿不理解。我的看法是:艺术家不理解自然的内在普遍性和自然之美,不理解自然规律(因此,不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描绘这类东西)。这个博物馆的想法是:艺术家应该更多地知道技术:他们应该更熟悉机械以及科学的其他实用功能。
这个艺术博物馆制订了一个计划,他们将让当时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去,这些公司自告奋勇为这个计划出时间、出钱。艺术家们将到这些公司四处溜达,寻找有意思的东西,好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博物馆认为,如果有个人明白一些技术上的事儿,那么艺术家参观公司的时候,他就可以时不时地做个艺术家的联系人什么的。因为他们知道,向人家解释事儿,是我的拿手好戏;说到艺术,我也不完全是个二百五(实际上,我想他们知道我在努力学画画)——无论怎么说吧,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干这个差事,我同意了。
和艺术家去参观公司,乐事儿很多。经常发生的事儿,是某个家伙给我们看一根管子,里头放电火花,蓝盈盈的,曲曲折折的,漂亮。艺术家们全都兴奋了,问我,在展览的时候,怎么用用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需要什么必要的条件?
艺术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绝对是冒牌货:他们自诩为艺术家,别人也都承认他们是艺术家;但等你坐下来跟他们聊聊,他们简直就是言语无味!有个家伙,最是突出,是个最大的冒牌货,穿得总是滑稽,戴着一顶好大的圆顶硬礼帽。他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用的是人人不懂的方式;等你问他用的一些词是什么意思,以便搞清楚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上又堕入云里雾里了!最后,他对艺术和技术展览的唯一贡献,是他的一幅自画像。另一些艺术家,我跟他们说话,开始的时候,你听不出什么意思来,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为你解释他们的想法。有一次,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一起,我到了个地方,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那是一次为期两天的旅行,费了好大劲,反反复复地讨论了很多,我终于理解了他试图向我解释的东西,我认为那很有意思,也很奇妙。
还有些艺术家,对真实世界绝对没有任何看法。他们以为科学家是某种大魔术师,他们什么东西都搞得出来,说的话像是这个样子:“我想做一种三维的画,里头的形象是悬在半空中的,而且还发光,一闪一闪的。”他们制造他们希望的那样一个世界,但制造什么是有道理的,制造什么是胡扯淡,他们是没有什么理解的。
最后,有一个展览,他们要求我当评委,来评判艺术品。尽管那儿有一些好东西,艺术家通过参观公司而得到灵感的好东西,但我认为,大多数的好艺术品,是那些在最后一分钟逼出来的东西,和技术实在风马牛不相及。评委会的其他成员全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了。艺术批评,我不擅长,我一开始就不该当这个评委。
在县艺术博物馆里,有个家伙,名字叫毛里斯·杜克曼(Maurice Tuchman),在谈到艺术的时候,确实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知道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搞的那个个人画展。他说:“你知道,你再也不会画画了。”
“什么?胡说!我为什么再也不……”
“因为你已经搞过个人画展了,而你不过是个业余画家。”
尽管自那以后我还是画画,但我不像以前那么卖力、那么投入了。我也再没卖过一幅画。他是个聪明的伙计,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如果我不是那么固执,我还可以学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