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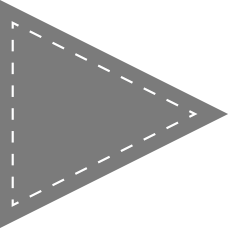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鸡母牛,鸡母牛!”
“鸡母牛,鸡母牛!”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去旅行的时候,总是粗心大意。地址啊,电话号码啊,邀请我的那些人的情况啊,我都不留心。我琢磨着,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别的一个人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但不知怎么,我能把事情弄妥。
有一次,那是在1957年,我去参加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举行的一个引力会议。有人把我看成不同领域中的一个也关心引力问题的专家。
那天,我在机场降落的时候,已经赶不上会了(第一天我没参加),我出了机场打出租车,对车辆调度员说:“我想到北卡罗莱纳大学。”
“你要到哪个北卡罗莱纳大学,”他说,“是在罗利(Raleigh)
 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还是在教堂山(Chapel Hill)
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还是在教堂山(Chapel Hill)
 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不需要说,我一点也不清楚了。“他们在哪儿呢?”我问,以为这两个大学一定相距不远。
“一个在北边儿,另一个在南边儿,距离大约一样。”
我身上没带什么东西能告诉我会场在哪儿,天色都那么晚了,也没别的人往会场那边去了。
我灵机一动。“听我说,”我对车辆调度员说,“会是昨天开始的,因此有一大群家伙都往会场那边去,他们昨天一定是从这儿走的。让我告诉你,他们是个什么德性:他们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互相谈着什么,不大在意到哪儿去,互相说的话,好像是这么个声音:‘鸡母牛,鸡母牛(G-mu-nu)
 ’。”
’。”
他眼睛一亮。“啊,是的,”他说,“这么说,你是要到教堂山了!”他对下一辆正在排队的出租车说:“把这位先生送到教堂山的大学。”
“谢谢。”我说,然后我就奔会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