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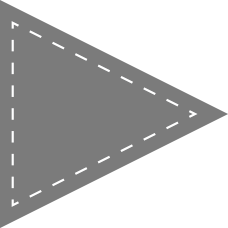 百分之七的答案
百分之七的答案
问题是要发现贝塔衰变的正确规律。看起来好像有两种粒子,名叫陶(τ)和西塔(θ)。这两种粒子,质量似乎完全相同,但是,其中的一种蜕变为两个介子,另一种却蜕变为三个介子。它们不仅是质量看来相同,寿命也相同,这真是一种怪异的巧合。因此,当时人人都关心这事儿。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在回旋加速器当中,这两种粒子在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能量产生出来的时候,其数目也总是相同——有多少个陶,就有多少个西塔。
当然,有这么一种可能性:那是同一种粒子,有的时候衰变为两个介子,有的时候衰变为三个介子。但是,没人承认竟然有这种事儿,因为有一个定律,叫宇称律;这个定律基于这么一个假定之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镜像对称的,这就是说,一个东西,要是能变成两个介子,那它就不可能变成三个介子。
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我真的不怎么能跟得上事情发展的脚步:我总有那么点儿落后。人人都透着聪明劲儿,我呢,觉得自己跟不上趟儿了。无论如何,我跟一个名叫马丁·布洛克(Martin Block)的家伙,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住一个房间。有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这帮家伙,干吗那么拘泥于宇称律?或许陶和西塔是同一种粒子。要是宇称律错了,那会有什么结果?”
我沉思了片刻,说:“那将意味着,对左旋和右旋来说,自然规律是不同的,意味着有办法以物理现象为右旋下定义。我认为这事儿不那么可怕,尽管这必定会带来一些糟糕的结果,可我不知道。你干吗不在明天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问,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吧。”
所以,第二天在会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陶-西塔难题的时候,奥本海默说:“关于这个问题嘛,我们需要听到某种更野一点儿的新想法。”
那我就站起来说:“我代替马丁·布洛克问这么个问题:要是宇称律错了,那会有什么后果?”
默里·盖尔曼经常拿这个揶揄我,说我没胆子为自己问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认为,那非常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李政道
 代表自己和杨振宁
代表自己和杨振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儿复杂,像以往一样,我听不大明白。会议结束的时候,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的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依我之见,这问题还没了结……仍然有一种可能性。我不是认为这事儿非常可能,可我认为它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儿复杂,像以往一样,我听不大明白。会议结束的时候,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的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依我之见,这问题还没了结……仍然有一种可能性。我不是认为这事儿非常可能,可我认为它可能。
诺姆·拉姆齐(Norm Ramsey)问我,我是否认为他应该做一个实验,来寻找违背宇称律的现象,我回答:“解释此事,莫非实验。你发现不了什么东西,我输你50块;你发现了,你输我1块。”
他说:“那我得大便宜了。”可他从来没做这个实验。
无论如何,违背宇称律的现象,被吴健雄
 发现了,用的是实验方法,她为贝塔衰变理论开创了大量全新的可能性。此事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实验。有些实验表明,电子从核里出来,是飞向左边的,有的证明是飞向右边的;关于宇称律,还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各种各样有趣的发现。但是,得来的资料令人困惑,没人能把事情综合起来。
发现了,用的是实验方法,她为贝塔衰变理论开创了大量全新的可能性。此事也立刻引发了大量的实验。有些实验表明,电子从核里出来,是飞向左边的,有的证明是飞向右边的;关于宇称律,还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各种各样有趣的发现。但是,得来的资料令人困惑,没人能把事情综合起来。
罗彻斯特(Rochester)
 有个会——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会议。我还是落后,人家李政道都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了。他和杨振宁得到了一个结论:宇称律是可以打破的,现在,他在为这种现象制造理论。
有个会——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会议。我还是落后,人家李政道都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了。他和杨振宁得到了一个结论:宇称律是可以打破的,现在,他在为这种现象制造理论。
在会议期间,我待在锡拉丘兹(Syracuse)
 我妹妹那儿。我把那篇论文带回家,对她说:“我看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这些东西。这也太复杂了。”
我妹妹那儿。我把那篇论文带回家,对她说:“我看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这些东西。这也太复杂了。”
“不复杂,”她说,“你的意思,不是说你看不懂,而是说那东西不是你发明的。根据你听到的这个线索,按照你自己的思路,你却琢磨不出个头绪来。你应该设想你现在又是学生了,把论文拿到楼上,一行一行地看,检查一下那些方程式。你会很容易就看懂。”
我听了她的建议,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发现它既明显,又简单。我一直害怕读这个东西,还以为它很难呢。
这让我想起好早以前做过的一件事儿,是和左右不对称方程有关系的。现在看李政道的公式,事情变得清楚了,他的解法简单得多:一切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对电子和μ介子来说,我的预言和李政道的相同,只是我的符号不同罢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李政道处理的仅仅是μ介子耦合的最简单的例子,并没有证明全部的μ介子都是右旋的;但按照我的理论,全部的μ介子必定都是自动右旋的。因此,实际上,我事先就预言到了他说的事情。我的符号是不同的,但我在当时没有看到我把全部的事情都搞对了。
我预言了几件事儿,可还没有人为此做实验;但是,说到中子和质子,我却没把事情搞得和当时已经知道的中子、质子的耦合协调起来,这事儿有点儿棘手。
第二天,我回去开会,一个叫肯·凯斯(Ken Case)的好心人,把他分得的宣读论文的时间,匀了五分钟给我提出我的观点。我说,我确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的,而且中子和μ介子的符号用反了,但我正在极力解决中子的问题。后来,几个实验物理学家问了一些和我的预言有关的问题,然后我就在夏天到巴西去了。
等我回到了美国,我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情况怎么样了。我去了吴健雄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她不在;但另一位女士在那儿,把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拿给我看,乱七八糟的数字全都不对劲儿。在贝塔衰变中的电子,依我的模型来看,应该都是左旋耦合的;可在有些情况下,却右旋了。一切都支离破碎了。
等我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我问一些实验物理学家,贝塔衰变情况如何。我记得三个家伙,汉斯·詹森(Hans Jensen)、阿尔德特·瓦帕斯特拉(Aaldert Wapstra)和费利克斯·勃姆(Felix Boehm)。他们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开始告诉下面这些事实:这个国家别的地方的实验结果,他们自己的实验结果。因为我认识这几个家伙,知道他们是多么仔细,我对他们的结果比对别人的结果,注意得更多。单看他们的结果,还不是那么不协调;但加上别人的结果,就都乱了。
最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一股脑地倒给了我,说:“情况如此混乱,连大家建立多年的一些东西都成了问题——比方说,中子的贝塔衰变是S和T。这个乱劲儿啊!默里·盖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凳子上跳起来了说:“这我就全明白了!”
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呢。但是,我在开罗彻斯特会的时候的麻烦,是中子和质子的衰变:事事妥帖,但有一件事儿掣肘;如果事情是V和A,而不是S和T,那么那个掣肘的事儿也妥帖了。因此,我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
那天晚上,我用这个理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计算出来了。我计算的第一个事情,是μ介子和中子的衰变率。两个衰变率应该是互相联系着的,如果我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根据某种关系,那么这个理论只差9%就对了。这很接近了,9%啊。这个理论本该更完美的,但也非常接近完美了。
我继续检查了另外一些事情,符合,连带着新的和更新的东西都符合了,我喜出望外。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知道了一个自然规律,别人却不知道。[当然,这说法不真实;我后来发现,起码默里·盖尔曼—还有苏达山(Sudarshan)和马沙克(Marshak)—都搞出了相同的理论,但我没觉得他们败兴。]
以前我做过的另一些事儿,是把人家的理论拿过来,改善其计算方法,或拿来一个方程式,如薛定谔
 方程式,来解释一个现象,如氦的现象。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程式,我们也知道这个现象,但怎么拿方程式来解释现象呢?
方程式,来解释一个现象,如氦的现象。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程式,我们也知道这个现象,但怎么拿方程式来解释现象呢?
我想到了狄拉克
 ,他拥有他的方程式有一阵子了——那是个新方程式,告诉我们电子怎么行为——现在我也有一个关于贝塔衰变的方程式,没有狄拉克的方程式那么重大,但也不错啊。我发现了一条新的规律,这是头一遭啊。
,他拥有他的方程式有一阵子了——那是个新方程式,告诉我们电子怎么行为——现在我也有一个关于贝塔衰变的方程式,没有狄拉克的方程式那么重大,但也不错啊。我发现了一条新的规律,这是头一遭啊。
我给在纽约的妹妹打电话,感谢她在罗彻斯特会议期间,让我坐下来研究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曾经觉得不自在,觉得落后,可现在我登堂入室了;我得到了一项发现,仅仅是听了她的建议而得到的一项发现。我又能投身于物理当中了;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为此谢谢她。我告诉她,事事都妥帖了,只差9%。
我太兴奋了,算个不停,妥帖的事儿层出不穷:它们是自动妥帖的,丝毫也不勉强。人在当时,我开始忘记了那9%,因为其他的一切都顺顺利利。
我在夜里干得很卖力,坐在厨房靠窗的小桌子边。工作得越来越晚——下半夜两三点的样子。我努力工作着,把那些计算结果和那些妥帖的事情弄得天衣无缝,我沉思,气定神凝,外面漆黑而宁静……突然,啪、啪、啪、啪——好响,有人敲窗。我一抬眼,一张白脸,就在窗上,近在咫尺,连惊带吓,我尖叫起来!
那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士,跟我生气呢,因为我假期回来,没立刻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回来了。我让她进来,想跟她解释,眼前我正忙着呢,我刚刚发现了个事儿,这事儿蛮重要的。我说:“请出去,让我弄完。”
“不,我不想烦你。我就坐在客厅里。”
我说:“呃,那好,但坐那儿也没劲啊。”
严格来说,她并没坐在客厅里。最好的说法,是她似乎是蹲在一个角落里,把两只手攥到一起,不想来“烦”我。当然,她的目的,是非要把我烦死不可!她达到了目的——我不能不理她。我火来了,我受不了这个。我不得不做这个计算;我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发现,我欣喜若狂,不知怎么的,对我来说,这个发现比这个女的更重要——起码在那个时刻,就是这样。我记不得我最后是怎么把她弄走的,反正挺难。
又干了一阵子,时辰更晚,我也饿了。我走到大街上,往五个或十个街区之外的那个小饭店那儿走。我以前也经常这样,深夜出行。
以前有几次,经常有个警察挡住我,因为我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停住不走了——有的时候,冒出了个想法,要想继续走路,太难了;你必得把什么事儿搞确实了啊。于是,我就不走了,有的时候,我还把双手举在空中,自言自语:“这些东西之间的距离,是那个样子,那么这个就会是这个样子……”
我两手乱比画,站在大街上,警察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儿?你在干什么啊?”
“啊!我在思考嘛。抱歉,我就住这儿,经常到那个饭店去……”过了些时候,他们都知道那是谁,再也不挡我的路了。
我到了饭店,吃着饭还兴奋呢,我告诉一个女士,说我刚刚弄出个发现。她开口了:她是一个消防队员或者护林员什么的老婆。她很寂寞——都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儿。所以呢,那种事儿,有啊。
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去找瓦帕斯特拉、勃姆和詹森:“我已经把一切都搞出来了。事事都妥帖了。”
克里斯蒂(Christy)也在那儿,说:“你用的是什么衰变常数?”
“就是那谁谁的书上的那个。”
“可那个已经被发现是错误的,最近的测量表明它有7%的误差。”
我这才记起了那个9%。这对我来说,像个预言:我跑回家,搞出了这么个理论,说中子衰变将有9%的误差,第二天早晨他们告诉我,实际上,那个数有7%的变化。但是,是从9%变为16%(这可不好),还是从9%变为2%(这个很好)?
正在那时,我妹妹从纽约打来电话:“那9%怎么样了?——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刚发现,有一个新的数据:7%……”
“往哪边变啊?”
“我正在把这事儿捣鼓出来呢。回头给你打电话。”
我太兴奋了,兴奋得没法思考。这好像你赶飞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了,你就是搞不清楚了,这时,有人告诉你:“现在是夏时制嘛!”没错儿,可提前还是延后?往哪边?人一激动,这事,想不清楚的。
于是,克里斯蒂进了一个房间,我进了另一个房间,各人都静悄悄的,这样我们才能把问题想透彻:这个是这么动的,那个是那么动的——这不算很难,真的;就是激动。
克里斯蒂出来了,我也出来了,我们都同意:是2%,稳稳当当地在实验许可误差之内。那个常数毕竟已经改变了7%,那2%倒真可能是误差。我给我妹妹打电话:“2%。”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实际上,那不对:真的说来,那是1%,什么原因,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后来尼古拉·卡毕博(Nicola Cabibbo)才理解了这事儿。因此,那个2%,完全不是实验误差。]
默里·盖尔曼把我们的观念比较并综合了一番,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理论的论文。这个理论相当严整;它比较简单,它把许多事情都弄妥帖了。但我以前告诉过你,有好多乱七八糟的数据。在有些时候,我们竟然能走得这么远,能说出哪些实验是错误的。
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是瓦伦丁·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做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测量了当一个中子衰变的时候,向各个方向飞出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言,各个方向上的电子数应该是一样的,但特勒第发现一个方向上的电子数要比另一个方向上的多11%。特勒第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家,做事很仔细。有一次,他在什么地方讲话,提到了我们的理论,说:“理论家的麻烦,是他们从来也不留心实验!”
特勒第还给我们寄了封信,话说得并不严厉,但无论如何还是在表明,他确信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在信末,他写道:“关于贝塔衰变的‘费盖(费曼、盖尔曼)理论’,得‘费劲掩盖’点儿什么。”
盖尔曼说:“我们拿这事儿怎么办?你知道,特勒第善于做实验。”
我说:“我们权且等待。”
两天之后,从特勒第那儿又来了一封信。他心服口服了。根据我们的理论,他发现:从中子弹出来的质子,在所有的方向上是不同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忽视了。他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相同的。用我们的理论所预言的数据,来修正他一直在用着的数据,实验结果就没有掣肘的地方了,理论和实验完全一致。
我知道特勒第非常出色,跟他顶牛儿,不大容易。但在当时,我已经确信他的实验必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且他也会发现——他自己找漏子,要比我们去找,好得多。我说我们不应该去琢磨那件事儿,而是权且等待,原因就是如此。
我去了巴舍尔教授那儿,把我们的成功告诉了他,他说:“是啊,你们挺身而出,说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非T。大家在以往都以为那是T。说它是T的那个基本实验在哪儿?你为什么不看看以前的实验结果,找找那些实验出了什么毛病。”
我离开他,去找到了关于那个实验的原始文章,文章说中子-质子耦合是T,有什么东西让我大吃一惊。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读过这篇文章(以前,《物理评论》上的文章,我篇篇必读——那时它还不厚)。我记得,当我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看着那条曲线,心里想:“那什么也证明不了啊!”
你看,它依靠的是整个数据范围靠边上的一两个点,有一个原则:在数据范围靠边上的一点——最后一个点——是不够好的,因为,如果它足够好的话,那就还有一个更靠外的点。我本来就意识到,中子-质子耦合是T这整个观念,就是基于那最后一个点的,那个不很好的点,因此它证明不了什么。我记得我注意到了这个!
等我对贝塔衰变感兴趣的时候,我就直接阅读那些“贝塔衰变专家”的报告,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看过原始数据;我只读那些报告,跟个傻瓜似的。假定我是个好物理学家,那么以前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我想到原来那个观念的时候,本来立刻就会检查“我们知道那是T,果真可靠吗?”——那才是明智之举。我本来会马上意识到我早就注意到那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任何东西。
打那以后,对“专家们”的任何东西,我再也不费心思了。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计算。当人们说夸克理论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让两个博士,费恩·拉芬达尔(Finn Ravndal)和马克·基斯令格(Mark Kislinger)与我一道,把这个理论从头到尾搞了一遍。只有这么个搞法,我才能检查出这个东西还确实能得出相当妥帖的结果,而且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理论。我再也不会犯那个错误了,只读专家意见的那个错误。当然,你只有一次生命,你把什么错误都犯过了,这才知道不该做什么,而你这一辈子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