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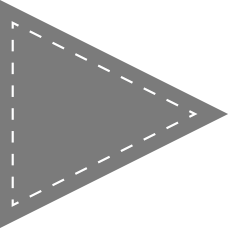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你解狄拉克方程吗?
你解狄拉克方程吗?
我在巴西那年的岁末,收到了惠勒教授的来信,说在日本将有一个理论物理学的国际会议,我喜欢不喜欢去?日本在战前有几位有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
 和朝永振一郎
和朝永振一郎
 以及仁科芳雄等——但这次会议,是战后日本恢复生机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认为应该去帮助他们。
以及仁科芳雄等——但这次会议,是战后日本恢复生机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认为应该去帮助他们。
惠勒还随信寄来了一本军用短语手册,他写道,我们大家都学点儿日语,会很有意思。我在巴西找到了个日本妇女,教我发音,我还练习用筷子夹起纸片儿,读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东西。那时候,对我来说,日本很神秘,到这么一个奇怪而奇妙的国家,该是很有趣儿的,所以我很用功。
等我们到了那儿,大家在机场见了面,我们被送到东京的一家旅馆。这旅馆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设计的。这是模仿欧洲旅馆里头的小个子家伙,穿着一身制服,活脱就是菲利普·莫利斯(Philip Morris)
设计的。这是模仿欧洲旅馆里头的小个子家伙,穿着一身制服,活脱就是菲利普·莫利斯(Philip Morris)
 。我们这不是在日本;这明明是在欧洲或者美国嘛!送我们到房间的那家伙,磨蹭着不走,把窗帘拉来拉去,等着你给他小费呢。什么东西都像是美国的。
。我们这不是在日本;这明明是在欧洲或者美国嘛!送我们到房间的那家伙,磨蹭着不走,把窗帘拉来拉去,等着你给他小费呢。什么东西都像是美国的。
我们的主人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的楼顶上吃晚饭,为我们服务的女人,打扮是日本的,可菜单是英语的。
为了学会几个日语短语,我遇到的麻烦可不少。到晚饭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对女服务员说,“Kohi-o motte kite kudasai.”她一鞠躬,退一边儿去了。
我的朋友马沙克(Marshak)一叠连声地说:“什么、什么?”
“我说日语呢。”我说。
“哈,装模作样!你走哪儿都没正经,费曼。”
“这话怎么说的?”我说,语气很正经的。
“那好,”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让她拿咖啡来。”
马沙克不相信。“我跟你打赌,”他说,“如果她把咖啡拿……”
女服务员出现了,端着咖啡,马沙克输了。
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学会了几句日本话——甚至惠勒,他还告诉大家都应该学日语呢,也一点儿没学会——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格的旅馆的书,我们住的旅馆应该完全跟这个不一样嘛。
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个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日本家伙叫到我房间来,“我想住在日本风格的旅馆里。”
“这恐怕不可能啊,费曼教授。”
我在书上读过,日本人很礼貌,但也很固执:你得一直做他们的工作才成。因此,我拿定主意,跟他们一样固执,也跟他们同样礼貌。那是一场脑筋搏斗: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了30分钟。
“你为什么想去住日本风格的旅馆?”
“因为在这个旅馆里,我感觉不到我在日本。”
“日本风格的旅馆,一点儿都不好啊。你得睡在地板上。”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想看看是怎么个样子。”
“还没椅子哪——你呢,守着桌子坐地上。”
“没问题。那很好玩儿。那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才把难言之隐说了出来:“如果您住别的旅馆,汽车到会场的时候,得多停一站。”
“不用,不用!”我说,“早晨,我到这个旅馆来,在这儿上车。”
“那就妥了。好。”啰唆半天,都为这个——好像花费半小时才触及真实问题,倒无关紧要似的。
他走到电话机那儿,要给别的旅馆打电话;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了;又掉链子了。我又花了15分钟才发现,这次是为了信件收发的事儿。如果会上有什么消息,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该去哪儿传达。
“没问题啊,”我说,“我早晨来坐车的时候,就在这个旅馆拿走给我的信啊、材料什么的。”
“那成。好。”他打电话去了,最后,我们终于往那个日本风格的旅馆走了。
我们一到那儿,我就觉得值啊:太可爱了!前头呢,有个地方,好脱鞋;然后呢,有个女孩儿,穿着民族衣服——宽腰带——穿着木屐,悉悉索索,碎步而出,拿了你的东西;你跟在她后头,穿过走廊,走廊上还铺着草席子呢,把纸糊的拉门拨开,她呢,喳喳喳喳,小碎步走着。这整个太有意思了!
我们进了房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那家伙,一路跟来,疲惫不堪,然后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她呢,赶紧跪下去,也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我觉得自己好尴尬。我也应该用我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吗?
他们这么互相打了招呼,他认可了给我的这个房间,出去了。这实在是个好玩的房间。到处都是照规矩弄的、符合标准的东西,这现在你都知道;可当时,在我看来,都无不新鲜。有个小壁龛,里头还有一幅画;一个花瓶,漂漂亮亮地斜插着几枝褪色柳;一方小桌,地板上放着,近旁铺好了软垫;屋子尽头,是两扇拉门,迈步出去,便是花园。
照顾我的这位太太,是位中年妇女。她帮我宽衣解带,给了我一件尤卡塔,就是一件简朴的蓝白便服,好在旅馆里穿。
我开了门,欣赏这个可爱的花园,然后坐在桌子边,做点儿小小的工作。
我在那儿待了15或20多分钟,一件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抬眼一看,就在花园那厢,在门口那儿,门边还有帘子,我瞥见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日本妇人,一身华裳。
关于日本的风俗,我读过不少,我心里扑腾开了:谁派她来干吗。我暗想:“这,或许会非常有趣啊!”
她稍知英语。“您,花园,喜欢看看?”她问。
我套上和我穿的尤卡塔相配的鞋子,我们就步入花园。她挽着我的胳膊,指给我看这看那。
到头来,事儿是这样:她知道点儿英语,旅馆经理就想,或许我喜欢她带我去浏览一下花园——不过如此而已。我有那么点儿失望,当然;但这是文化相会呀,我也知道,想入非非,想的不是时候。
过了一阵子,照料我房间的那位妇人进来,说了点儿什么关于洗澡的话——用日语说的。我知道日本的洗澡,很有意思,迫不及待地要以身尝试,于是我说:“嗨!”
我在书上看到过,说是日本的洗澡,非常复杂。他们用好多的水,而水是在外头烧的,而且,你不可把肥皂弄进洗澡水里,那会把水弄脏,下个人还得用这水呢。
我站起来,迈进浴室,那儿有洗手盆,我听得见隔壁那家伙,也正关着门在家洗澡呢。突然之间,门儿拉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主儿,想看看这个不速之客是谁。“教授!”他用英语对我说。“别人在洗澡,您却闯进了洗澡间,这错得都离谱了!”那人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说,那妇人问过我,我想洗澡吗,此事无可怀疑;果真如此,她会为我善加准备,等洗澡间无人之时,她会禀告我的。世界上犯过如此严重的社交错误的,大有人在;幸运的是,我犯在汤川教授手里!
那个日本风格的旅馆,真是好玩;有人来访,尤其好玩。别的家伙来到我屋,席地而坐,谈吐挥霍。我们还坐不到5分钟,照料我屋子的那位妇人,就端着糖盘、茶盘进来了。好像你就是主人,这儿就是你自己的家,旅馆的工作人员呢,是帮助你招待宾客的。在美国,有客人造访你的旅馆房间,没人理你;你必得打电话叫人过来服务,如此等等。
在这个旅馆吃饭,也别有情调。那个把托盘送来的女孩儿,在你吃饭的时候,会待在这儿陪着你,所以你不觉得孤独。我没法和她好好聊聊,但不妨事儿的。饭也美妙。比方说,汤上来了,是盛在盖着盖儿的碗里的。你掀开盖儿,里头是一幅漂亮的画:小块的葱叶,就那样在汤上漂着;美哉。食物放在盘子里,样子如何,很讲究的咯。
我拿定主意,我得尽可能像日本人那样生活。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吃鱼。我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吃鱼;但是,在日本,我发现,不吃鱼,可有点儿孩子气了:我吃了很多鱼,而且吃得有滋有味。(等我回到了美国,我做的头一件事儿,是直奔鱼那儿。可怕——跟从前一样可怕。我受不了鱼。后来,我发现了答案:鱼必得非常、非常新鲜——要是不这么新鲜,它就有股子味儿,我烦这味儿。)
有一次,我在这家日本风格的旅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上了一个圆形的、硬硬的玩意儿,跟鸡蛋黄大小相似,放在一杯黄色液体当中。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吃过;但这玩意儿,吓住我了:这东西够费解的,样子像个脑子。等我问那个女孩儿,那是什么玩意儿,她答道“kuri”。问也白搭。我琢磨着,它多半是个章鱼蛋什么的。我哆里哆嗦,吃这东西,因为我希望尽可能深入日本生活嘛。(我还记得“kuri”这词儿,好像我的命就系在这东西上——30年之后,我都没忘这事儿。)
第二天,我问开会的一个日本家伙,那叫人费解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他,那东西难吃死了。“kuri”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那词儿的意思是‘栗子’。”他回答。
我学的那些日本话,有几句是很有用的。有一次,汽车等了好长时间也不开,几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语;让他们赶紧点儿!”
我说:“Hayaku!Hayaku!Ikimasho!Ikimasho!”——这意思是说,“走吧!走吧!快点儿!快点儿!”
我发现自己的日语失控了。我是从一本军事短语手册上学的这些短语的,那些说法想必是非常粗鲁的,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开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车也立刻就开了。
日本的这次会,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东京,另一部分在京都。在到京都的车上,我把日本风格的旅馆的一些事儿,告诉了我朋友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都城旅馆”里,里头美国风格和日本风格的房间都有,派斯和我共用一个日本风格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料理我们房间的那个年轻女人,为我们准备了洗澡水,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阵子,她端着托盘回来送早饭。我衣服穿了一半。很客气地,她转朝我说“Ohayo, gozai masu”,这意思是“早晨好”。
派斯刚刚洗完澡,浑身滴答水儿,一丝不挂。她转朝他,同样安然自若,“Ohayo, gozai masu”。然后,把我们的餐盘儿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老天爷,我们文明吗!”我们意识到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仆来送早饭,这个家伙站在那儿,赤身露体的,那就会有一声尖叫、一通做作。可在日本,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对于这些事儿,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更进步,更文明。
我那时正在捣鼓关于液氦的理论,我已经琢磨出了怎么用量子力学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这种奇怪的现象。对这一成就,我觉得很自豪,想在京都会议上讲讲我的研究。
第二天晚上,在我讲话之前,有个晚宴,坐在我旁边的,不是别人,正是昂萨格
 教授,液态物理学和液氦问题的一流专家。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可金口一开,便掷地有声。
教授,液态物理学和液氦问题的一流专家。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可金口一开,便掷地有声。
“呃,费曼,”他说,嗓子粗哑,“我听说,你已经明白了液氦的事儿。”
“那个,是……”
“哼。”整个晚宴,那就是他对我说的全部的话!不太怎么提情绪啊。
第二天,我发表了讲话,把液氦的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到末了,我抱怨说,我还有点儿东西没有琢磨透:就是说,液氦从一态到另一态的转化,是属于第一序列(如在固体融化或者液体沸腾的时候——温度是恒定不变的),还是属于第二序列(如有时候你在磁力现象中看到的那样,温度是不断变化的)。
昂萨格教授站起来,语气严厉:“哈,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初出茅庐啊,我想,他需要接受点儿指教。有件事儿,他是应该知道的,而我们应该告诉他才是。”
我想:“我的个老天爷!我招谁惹谁了?”
昂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费曼,根据基本原理,没什么人已经正确地琢磨出任何液氦状态转化属于什么序列……因此,他的理论不允许他正确地搞出这个序列,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不曾令人满意地理解了液氦的许多其他方面。”到头来,他这是恭维我呢;但从他开讲的那个派头看,我还真以为他要修理我一顿呢!
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在房间里,电话响了。是《时代》周刊打来的。打电话的那家伙说:“我们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您能否寄给我们一份拷贝?”
我从来也没上《时代》,我非常兴奋。我很为我的工作自豪,我的讲话在会上的反响也很好,于是我说:“当然!”
“好的。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这家伙把地址给了我。我感觉棒极了。
我重复了一遍地址,那家伙说:“没错儿。谢谢您,派斯先生。”
“哦,不!”我说,大吃一惊,“我不是派斯;你找的是派斯啊?抱歉。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有话跟他说。”
几小时之后,派斯回来了。“嗨,派斯!派斯!”我说,声音激动。“《时代》杂志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把你在会上的论文,寄给他们一份。”
“哎呀!”他说,“名声,是个婊子啊!”
我倍感震惊。
打那以后,我发现派斯说得对,但人在当时,我想,要是我的名字上了《时代》,那可真的美啊。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归心似箭,说哪个大学要我,我都去。日本人安排了一系列地方,够好几天参观的。
等到这一次,我已经和玛丽·娄结婚了,不管我们到哪儿,他们都热情招待。有个地方,他们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整套仪式,还伴以舞蹈,这通常是为大旅游团体表演的。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在船上遇到了许多学生。还有一个地方,市长见了我们。
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待在树林里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天皇来的时候,就待这儿。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周围都是森林,就是漂亮;选在溪流淙淙的这个地方,也是费了心思的。这地方有某种静谧之感,一种宁静的优雅气氛。天皇到这么个地方来小住,我以为,说明他比我们一般的西方人,对自然有着更细腻的感觉。
在每一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我就和他们讨论。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一般问题,然后写出一大堆方程式。
“稍等片刻,”我说,“这个一般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例子?”
“怎么没有;当然有啊。”
“那好。给我一个例子。”我得看例子:除非我脑子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着它怎么走,我是理解不了任何一般的东西的。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我迟钝呢,以为我不明白那个问题,因为我问了许多这种“傻瓜”问题:“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可是稍后,当这个家伙掉进方程式堆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事儿,我就说:“稍等片刻!那儿,有个错误!那不可能对!”
这家伙看了看他的方程式,过了一阵子,他果然发现了那个错误,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一开始听不明白,可他怎么就能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方程式中间看出个错误呢?”
他以为我是在推演数学步骤,但我干的不是这个。对于他正在努力分析的那个问题,我有一个具体可感的例子;我本能就知道,我亲身体验着那个东西的属性。因此,当方程式说它会这么这么行为的时候,我知道那错了,我跳起来说:“等等!那儿有个错误!”
因此,在日本,除非他们能给我一个可感的例子,他们大多数人找不到个例子,我就不能理解任何人的工作,不能跟他们讨论。有些人倒是能给我一个例子,但那个例子经常稀松,你用一个简单得多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例子所表达的问题。
由于我总是不问数学方程式的问题,而是问他们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的物理环境,一份在科学家中间流通的油印小报的标题,“费曼的轰炸,与我们的反击”,对我的日本之行做了归纳。(小报不起眼,可那是他们在战后搞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交流系统。)
在走访了好几座大学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所”过了几个月。我很喜欢在那儿工作。一切都那么好。你来工作的时候,得把鞋脱掉,早上会有人过来给你上茶,那时你正想喝杯茶。这很是惬意。
在京都,我发了狠心想学日语。我用功得多了,学到可以打出租车转悠和做事儿的地步。一个日本人每天给我上一小时的课。
有一天,他教我“看”这个词儿。
“好了,”他说,“你想说,‘我可以看看您的花园吗?’怎么说?”
我造了一个句子,用了我刚学到的一个词儿。
“不成,不成!”他说,“如果你想对某人说,‘您想看看我的花园吗?’你就用第一个‘看’。但是,如果你想看别人的花园,你得用另一个‘看’,这一个更礼貌些。”
在第一个情况中,你实际上说的是这么个意思:“你愿意瞥一眼我这个邋遢的花园吗?”可是,当你想看另一个伙计的花园的时候,你一定得这么说:“我可否观赏您漂亮的花园?”这就是说,你必得用两个不同的词儿。
然后,他给了我另一个情况:“你到一个庙里去,你想看看那个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用的是那个礼貌的“看”。
“不成,不成!”他说,“庙里的花园优雅得多,因此你一定得说出相当于这么一种意思的一句话:‘我可否瞻仰你们至为美妙的花园?”
一个意思,要用三个或四个词儿来说,因为我做那事儿,那事儿就寒碜;你做那事儿,那事儿就高雅。
我学日语,主要是为了技术上的事儿,因此我决定试试在科学家们中间,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在研究所里,我对办公室里的家伙们说:“‘我解狄拉克方程’这句话,用日语怎么说?”
他们说这样这样说。
“那好。现在我想说,‘你解狄拉克方程吗?’——你怎么说这个?”
“哈,你一定得用一个不同的词儿来说‘解’。”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我解这方程,你解这方程,做的不是同一件倒霉的事儿吗?”
“哈,是啊,可得用不同的词儿——那才更礼貌啊。”
我打了退堂鼓。我断定,我讲不来这种语言,不学日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