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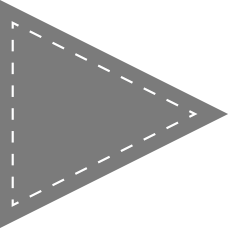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盛情难承
盛情难承
康奈尔大学什么系都有,但我兴趣都不很大。(这意思,不是说这些系有什么毛病;是我碰巧对这些系不感兴趣而已。)有家政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脑袋尤其空),还有文化的东西——音乐之类。当然,跟我言语投机的人,还真有几个。数学系有凯克(Kac)教授和菲勒(Feller)教授;化学系,有加尔文(Calvin)教授;动物学系还有个很了不起的家伙,就是格里芬(Gri n)博士,发现蝙蝠用回声导航的,就是他。但要找到足够多的这类谈话对手,难。但低水平的信口雌黄,却有的是。
天气也实在不佳。有一天,我正开着车,没想到天上急匆匆地下起雪来,你没防备这个,你就琢磨:“哦,不会下得太大吧;我继续开得了。”
可那雪接着就厚起来,车开始有点儿打滑,所以你不得不用防滑链。你从车里出来,把链子铺在雪地里,链子冰凉啊,你也开始瑟瑟发抖了。然后,你把车倒在链子上,你麻烦来了——或者说,那年头,我们就有这个麻烦;下雪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里头有个链子,你必得把这个链子先钩住。因为链子必须扣得很紧才成,让钩子钩住链子,就难了去了。然后,你不得不用手指头,把这个夹子扳下去,到这时候,你的手几乎冻僵了。因为你在车胎的外头,可钩子在里头,你的手又冻僵了,要把事儿办妥,太难了。链子总是滑掉,链子还冰凉,雪又下得紧,你想把这个夹子扳下去,你的手冻得好似猫啃,可这倒霉玩意儿就是不下来——好了,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刻,我想明白了:这是犯傻。世界上必定有个地方,没这种麻烦。
我记得我去过几次加州理工学院,巴舍尔教授请我去的,他早先在康奈尔大学。我去访问的时候,他很机灵。他对我太了解了,于是他说:“费曼,我有辆车,用不着,我想把它借给你。现在你就可以去好莱坞和落日带(Sunset Strip),好好玩儿。”
于是,我每天晚上就开着这车到落日带去——去夜总会,去酒吧,去看表演。都是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我喜欢的东西——漂亮女孩儿、大赌家之类。巴舍尔知道怎么使我对加州理工学院发生兴趣。
一头驴,不偏不倚站在两堆干草正中间,不知道到哪边去,因为两堆干草完全一样,这故事,你知道吧?呵,不知道就算了。康奈尔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开始给我提供条件,我琢磨着加州理工学院比较好,正当我开始动身的时候,康奈尔那边儿就加码了;到我觉得留在康奈尔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那边儿又加了点什么好处。因此,你能够想象得到,两堆干草中间的这头驴,只是情况更复杂,他刚要到一边儿去,另一边儿就高了一点儿。这真叫人左右为难!
最后把我说服气了的一个论点,是我的休假年。我还想到巴西去,这次是10个月,我刚刚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休假年。我不想失去休假年,因此现在我就发明了一个理由,好做出决定,我就写了封信给巴舍尔,告诉他我做出了什么决定。
加州理工学院回信:“我们将立刻聘请您,您的第一年就是休假年。”他们就是这么个搞法:无论我决定怎么做,他们都死叮住你不放。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实际上是在巴西度过的。我在第二年才到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我从1951年就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了,我在那儿一直很开心。这个学校,正合我这种偏执的家伙的口味儿。那儿有的是顶尖级的人物,对自己干的事儿都很感兴趣,我也跟他们谈得来。所以我觉得非常称心如意。
可是,有一天,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好长时间了,我们遭到了很严重的烟雾袭击。那烟雾,比现在的可厉害得多——至少你的眼睛要疼得多。我站在一个角落里,泪眼汪汪的,我心里说:“这简直发疯!这绝对是神经病!最好是回康奈尔大学去。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我就给康奈尔打电话,问他们,我有没有可能回去。他们说:“没问题!我们这就把事情安排好,你明天就过来。”
第二天,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老天爷必定是安排好了,好帮助我下定决心。我正往我办公室那儿走呢,一个家伙跑过来,对我说:“嗨,费曼!你听说出什么事儿了吗?巴德
 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恒星!我们原来测量的我们到各星系的距离,都是以一种类型的造父变星为根据的,可现在有另一种类型,因此,宇宙的年龄会是我们原来设想的2倍、3倍,甚至4倍!”
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恒星!我们原来测量的我们到各星系的距离,都是以一种类型的造父变星为根据的,可现在有另一种类型,因此,宇宙的年龄会是我们原来设想的2倍、3倍,甚至4倍!”
我知道这个问题。在那年头,地球似乎比宇宙还古老。地球有45亿年,宇宙却只有20亿或30亿年。这是一个大难题。这个发现,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现在,事实证明宇宙比以前设想的要老。我马上就得到了这一信息——这家伙跑来,把这件事儿都告诉了我。
还没等我穿过校园到我办公室去,另一个家伙过来了——马特·梅瑟尔森(Matt Meselson),一个副修物理学的生物学家。(我曾经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他建立了第一台我们称之为“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机”的东西——它能测量分子密度。他说:“看我正在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他已经证明,当一个细菌制造一个新细菌的时候,有个分子,原封不动地由一个细菌传给了另一个细菌——我们现在知道,这分子就是DNA。你知道,我们总是认为一切东西都分裂、分裂。因此,我们以为细菌里的一切都一分为二,把其中的一半给了那个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个包含着遗传信息的最小分子,不能够一分为二,而必须复制出一份它自身的拷贝,然后把这份拷贝送给那个新细菌,把另一份留给那个老细菌。梅瑟尔森是这么证明这一点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中生长。他进行实验的时候,用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机来测量分子的重量。
第一代新细菌的全部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在重氮中细菌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和在普通氮气中的细菌的染色体分子的重量之间——如果一切都分裂,连染色体分子也分裂,结果就会是这样。
但在随后的几代细菌当中,当我们期望染色体分子重量将是重氮和普通氮情况下的分子重量之差的1/4、1/8和1/16的时候,分子重量却只有两组。一组和第一代一样重(在较重和较轻的分子正中间),而另一组轻些——其重量就是在普通氮气中弄的分子的重量。较重的分子个数的百分比,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但其重量不变。这可太令人兴奋了——这是一项基础性发现。在我终于到了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待在这地方了。在这里,不同科学领域中的人,都告诉我事儿,这太令人兴奋了。这才是我真想要的东西,真想要的。
因此,过了一会儿,康奈尔大学打电话来,说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了,这就快准备好了,我说:“我很抱歉,我主意又变了。”但是,我当时决定永远不再变了。没什么事情——绝对没什么事情——能够再次改变我的想法。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有的是这种闹心的事儿——你该到哪儿去吗,你怎么办。你真上火啊,想拿定主意,可接着又来了别的事儿。怎么简单,就怎么决定,倒来得容易些。别担心——没什么能够改变你的主意。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这么做了一次决定。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懒得为吃什么甜点费心思了,因此我就决定总要巧克力冰淇淋,永远不再为这事儿操心——我就是这么解决那个问题的。无论如何,我决定永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了。
有一次,有人想让我对加州理工学院变卦。费米刚刚去世不久,芝加哥大学在找人接任他的位置。芝加哥大学过来两个人,要到我家来看看我——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事儿。他们开始给我讲,我应该到芝加哥大学的所有的好理由:我能干这个,我能干那个,他们那里大人物很多,我有机会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儿。我没问他们会给我多少钱。他们不停地暗示,如果我问的话,他们就告诉我。最后,他们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多少。“哦,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学院。我妻子玛丽·娄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是多少,我们又该吵了。除此之外,我已经决定不再变了;我永远待在加州理工学院。”因此,我不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给的薪水有多少。
大约1个月以后,我在开一个会,利昂娜·马歇尔(Leona Marshall)过来说:“你不接受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条件,可真够滑稽的。我们大失所望啊,我们搞不明白,你怎么能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容易,”我说,“因为我没让他们告诉我那是多少钱。”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打开信,第一句话是:“他们提供的薪水是——”一大笔钱啊,是我当时薪水的三四倍。晕!她在信里继续说:“在你还能继续读这封信之前,我就把薪水告诉你了。也许你现在愿意重新考虑一下,因为他们告诉我,那个位置还在为你预备着,我们非常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于是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在信里看到这么一大笔钱,我觉得,我必须谢绝。我不得不谢绝这份薪金的原因,是我将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儿——找个迷人的情妇,为她买一座漂亮的房子,给她买好东西……用你们给的这份薪水,我必定真的会这么做,我知道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会为她操心,挂念她在干什么,我们会吵架。我回家的时候,又会如何如何。这些闹心的事儿,会让我寝食不安,会让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都将是一团糟!我一直想做的这种事情,对我是很坏的,因此,我已经决定,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