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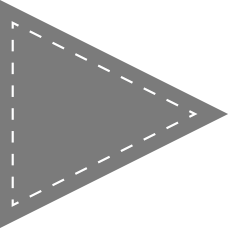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照您吩咐的,老大!
照您吩咐的,老大!
每个夏天,我常常开车横穿美国,想开到太平洋边儿上。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总卡在什么地方——通常是拉斯维加斯(Las Vegas)。
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到那儿,我非常喜欢那次的经历。当时和现在一样,拉斯维加斯从赌徒那儿赚钱,因此,旅馆唯一的问题,就是把大家弄到这儿赌博。因此,旅馆里有表演,有饭,都非常便宜——和白看白吃差不多。什么都不需要你预定:你可以迈步进去,找一张空桌子,坐下,欣赏演出。对一个不赌博的人来说,这事儿太妙了——房间不贵;饭,简直不花钱,表演不错,女孩儿我喜欢。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游泳池边上,有个家伙走过来,开始跟我搭话。我忘记他是怎么跟我聊上的,但他以为我想必是个靠工作活命的人,而这实在是相当愚蠢的。“你看我活得多潇洒,”他说,“我成天在游泳池边上流连忘返,在拉斯维加斯优哉游哉。”
“你不干活儿,怎么还活得这么滋润?”
“简单,我赌马。”
“我对马一窍不通,但我看不出,你怎么能靠赌马过日子。”我满腹狐疑地说。
“当然能,”他说,“我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我教教你怎么弄这个事儿。待会儿我们去赌一把,我保证你赢100块。”
“你怎么弄的?”
“我赌100块,赌你赢,”他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赢了,你一个大子儿也不用出;如果你输了,你就赢我100块!”
我就想了:“嚯!那好啊!如果我在赛马上赢100块,那就给他了,我不损失什么;权当练练手——那就证明他那套管用。如果他输了,我就赢他100块。这很妙!”
他带我到了一个赌马的地方,那里列着马的名字和全国各地赛马场的名字。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些人,他们说:“嚯,他很了不起!我赢了100块!”
我逐渐意识到,我必须押上我自己的一些钱才能赌,我开始有点儿紧张了。“我必须赌多少钱?”我问。“哦,三四百块吧。”我没那么多钱。再说,这事儿让我着急了:要是我输了呢?
于是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建议只花你50块,如果这主意灵验,我就给你100块,你横竖都是赢嘛。”我琢磨着,“哇!这样我两头儿都赢——不是赢50,就是赢100!这主儿怎么能这么办?”稍后,我明白了:如果你输赢机会平均的话——把听他的建议以便理解其中的奥妙所付出的小小损失暂且忘掉——那么你赢100块的机会比你输400块的机会是四比一。因此,他在某个人身上试这一招儿,试五次,他就有四次赢100块,他就能赢200块顾问费(他还要向他们说明白自己是多么聪明);到第五次,他必须付出100块。因此平均来说,他每付出100块,就能得到200块!因此,我终于明白了他是怎么弄的。
这个过程持续好几天。他设计出了一个乍听起来非常合算的方案,但等我思考了一阵子之后,我慢慢琢磨出了这是怎么弄的。最后,他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好了,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50块买建议,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你的钱全还给你。”
现在,我想输都输不了了!因此我说:“好吧,成交!”
“好,”他说,“但不凑巧,我这个周末得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得了,如果你把你那400块输掉了,我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前几个方案,设计出来,是凭诚实的数学计算为他赚钱的。现在,他却要出城了。他拿这个方案赚钱的唯一办法,是不把钱寄过来——当个真正的骗子。
因此,我从来没有接受他任何建议。但看明白他怎么操作这一套,堪为乐事。
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事,是认识表演的女孩儿。我猜,她们是在表演之外的空闲时候,在酒吧里拉客的。我这么见了她们好几个,跟她们聊天,发现她们人都很好。“表演女郎,哦?”这么说话的那些人,对她们有先入之见!可在任何人堆儿里,如果你看仔细了,那就什么样的人都有。比方说,东海岸一个大学里的一个院长的女儿,就在那儿。她有舞蹈天赋,喜欢跳舞,放暑假了,跳舞的工作难找,于是她就到拉斯维加斯,在一个歌舞团里找了个工作。大多数表演女郎人都很好的,很友好。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就是爱漂亮女孩儿。说穿了,表演女郎是我如此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儿害怕:这些女孩儿也太漂亮了,她们有怎么怎么样的名声,等等。我就想办法跟她们见面,我说话的时候,呼吸都有点急促呢。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渐渐地,事儿容易了,最后我信心十足,不怵任何人。
我有我自己的冒险路数,这路数很难解释的:那好像是钓鱼。你把线放出去,然后呢,你需要点儿耐心。当我对人家讲起我的一些冒险经历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说:“哦,来啊——咱们干这个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一个酒吧,看看能不能弄出点事儿,可20来分钟,他们就不耐烦了。平均而言,要想弄出事儿,你得等上几天。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跟表演女孩儿聊。一个女孩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过了一阵子之后,有意思的事儿就常常会发生。
我记得一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儿。她在“火烈鸟旅馆”跳舞,我跟她很熟。我进城的时候,不等她坐下,我就给她要一杯吉普森,放在她桌子上,以此宣布我大驾光临。
有一次,我进来,坐在她身边,她说:“我今天晚上要和一个男人在一块儿——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阔佬。”(我早就听说过这家伙。每当他玩双骰子的时候,大家都凑过来看他赌。)在他回到我们坐的这桌的时候,我的表演女孩儿把我引荐给了他。
他跟我说的头一句话是:“你可知道?昨儿晚上我在这儿输了6万美元。”
我知道怎么应对,我转朝他,完全无动于衷,说:“你觉得,那是聪明,还是愚蠢?”
我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饭。他说:“听着,让我来替你签单。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要我钱,因为我在这儿赌得太多了。”
“我有的是钱,用不着操心谁来给我付早饭钱,谢谢。”他每次想给我摆阔,我都不买他的账。
他什么招数都用:他有多么富,他在得克萨斯州有多少石油,没一样灵的,因为我知道这种套路!
到最后,我们一道找了不少乐子。
有一次,我们两个坐在酒吧里,他说:“你看那边那桌,那些妞儿?她们是从洛杉矶来的婊子。”
她们相貌非常漂亮,是有一定级别的呢。
他说:“告诉你我要干什么:我会把她们介绍给你,然后呢,你挑一个,我来付钱。”
我不觉得我想见这些女孩儿,我也知道他说这个,是为了给我摆阔,于是我就对他说不。可我转念一想:“这里头有事儿!这家伙不遗余力跟我摆阔,还要为我买这个。如果我将来讲起这档子事儿……”于是我就对他说:“那个,好吧,为我引荐。”
我们凑到她们那桌,他把我介绍给那些女孩儿说:然后就暂避一边了。一个女服务员过来了,问我们想喝点儿什么。我要了些水,坐我旁边的那女孩儿说:“我来杯香槟好吗?”
“你要什么都成,”我冷冷地回道,“你自己买,谁管得着。”
“什么毛病啊,你?”她说,“小气鬼儿还是怎么着?”
“随你怎么说。”
“你真不够绅士!”她义愤填膺地说。
“你真是一眼把我看了个透!”
我回嘴。鄙人以前在新墨西哥州学习过,学习不当绅士。
很快很快,她们倒主动给我买喝的——真是乾坤颠倒啊!(顺便说句,得克萨斯的那位卖石油的,一去不回头了。)
过了一阵子,其中的一个女孩儿说:“咱到艾拉大棚屋(El Rancho)去吧。说不定那儿现在事儿热闹了。”我们进了她们的车。车不错,人也不错啊。在路上,她们问我名字。
“迪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的,迪克?你干什么的啊?”
“我是从帕萨迪纳来的,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儿说:“哦,那不是那个科学家鲍林
 待的地方吗?”
待的地方吗?”
我反反复复到过拉斯维加斯好几次,但那儿没人知道科学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个商人谈过各种各样的事儿,对他们而言,一个科学家,什么也不是。“没错。”我说,心里惊讶。
“有个叫盖伦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家伙——是个物理学家。”简直难以置信。我坐的这个车,满车的妓女,都知道这类事儿!
“是啊!他名叫盖尔曼
 !你怎么凑巧知道?”
!你怎么凑巧知道?”
“你们的照片都上《时代》周刊了啊。”这不假,《时代》周刊里常有美国科学家的照片,不知什么原因,我也进去过,还有鲍林和盖尔曼。
“你怎么记得住那些名字啊?”我问。
“哈,我们从照片里找最年轻漂亮的!”(盖尔曼比我年轻。)
我们到了艾拉大棚屋旅馆,女孩儿们继续跟我玩儿大家通常跟她们玩儿的那一套游戏:“想赌一把吗?”她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一点点儿,我们玩儿得很开心。
过了一阵子,她们说:“好了,我们看到你这个大活人了,现在不得不把你撇下了。”她们回去工作了。
有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我注意到两个女孩儿和一个老头儿在一块儿。最后,老头儿走了,她俩就凑到我这儿来坐下:比较漂亮、比较活跃的那个,挨着我坐,她那位木讷的朋友,叫潘,坐在另一边。
事儿一开始就进行得很顺利。她非常和气。一会儿工夫,她就靠在我身上,我呢,把一只胳膊搭在她肩上。进来两个男的,坐在近旁的桌子那儿,然后,女服务员还没来得及过来,这两位却出去了。
“你看见那俩男的了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见了。”
“他们是我丈夫的朋友。”
“哦?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我刚刚和约翰老大结婚了。”——她提到的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拌了几句嘴。我们这是度着蜜月呢,可约翰总在赌。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就出去找我的乐子去,可他总是派特务来转悠,看看我在干什么。”
她要我把她送到她的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于是我们就上了我的汽车。在路上,我问她:“那个,约翰怎么办?”
她说:“别担心。看看周围有没有个大红汽车,有两根天线的。要是你没找到,那他就不在附近。”
第二个晚上,我带着这位“喜欢吉布森鸡尾酒的女孩儿”和她的一个朋友,去看“银拖鞋旅馆”的晚场表演,那儿的表演比别的旅馆都晚。在别的地方表演完了的女孩儿,都喜欢到那儿去。各种各样的舞女进门的时候,节目主持人就报奏她们大驾光临。因此,当我两只胳膊上挎着两位可爱的舞女款款入场的时候,他说道:“从火烈鸟来的什么什么小姐和什么什么小姐大驾光临!”大家都扭头看这是谁来了。我感觉自己好伟大!
我们找了张靠近吧台的桌子,坐下来,过了一会儿,起了一阵子小小的慌乱——服务员拉桌子,几个保镖登堂入室,还带枪呢。他们在为名人腾地方呢。约翰老大,大驾光临!
他走到吧台那儿,与我们这桌子挨着,立刻有两个家伙想和我带来的这俩女孩儿跳舞。她们去跳舞,我一个人守着桌子坐着,这时,约翰走过来,坐在我这桌上。“还好吗?”他说,“你在拉斯维加斯,干吗来着?”
他准是发现我和他老婆的什么事儿了。“鬼混呗……”(我得硬气点儿,对吧?)
“你,在这儿鬼混了多少日子?”
“四五个晚上吧。”
“我认得你,”他说,“在佛罗里达,我见过你吗?”
“这个嘛,鄙人确实不知……”
他问这个地方,问那个地方,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知道,”他说,“那是在艾拉摩洛哥的事儿。”(艾拉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玩家都去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教授什么的,对吧?)
“一定是在那儿了。”我说。我在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翻开底牌。最后,他朝我倾过来,说:“嗨,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俩女孩儿,等她们跳完舞?”
他想要的是这个啊;原来他根本不认识我!于是我就想引荐他,但我的表演女孩儿说她们累了,想回家。
第二天下午,我在火烈鸟旅馆看见了约翰老大。他站在吧台边,跟服务员聊照相机,还拍照片呢。他想必是一个业余摄影家了:闪光灯和照相机,他有一大堆;但他说的那些话,却傻瓜透顶。我断定他根本不是个业余摄影家;他不过是个有钱的主儿,买了几个照相机而已。
到那时候,我琢磨清楚了,他并不知道我一直在跟他老婆鬼混;他跟我说话,只是为了那俩女孩儿。于是我就想玩个游戏,我为自己设计了个角色:约翰老大的随从。
“嗨,约翰,”我说,“拍几张照片吧。我替你拿着闪光灯。”
我把那些闪光灯装在口袋里,我们就出发去拍照片了。我在把闪光灯递给他的时候,时不时地给他点儿建议;他喜欢这路事儿。
我们到了“前线旅馆”去赌,他开始赢了。旅馆都不喜欢赢家离开,但我看得出他想走。问题是,怎么走才不失风度。
“约翰,我们现在必得走了啊。”我说,语气严重。
“可我赢着呢。”
“知道你赢着,可我们今天下午不是有个约会吗?”
“那好吧,备车。”
“照您吩咐的,老大!”他把钥匙递给我,告诉我车是什么样子。(我没让他知道我早知道他车是什么样子。)
我出去,到了停车场那儿,果然,那儿有一部大胖车,漂亮透了,还有两根天线。我爬到里边去,转动钥匙——启动不了。这车有个自动打火器;这玩意刚出来,我一点儿不懂。折腾了一阵子,我碰巧把钥匙转到了“打火”上,启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这辆百万美元的车,开到旅馆门口。我下了车,到里面那桌子,他还在赌呢,我说:“车预备好了,先生!”
“恕不奉陪了。”他宣布,我们离开。他让我开车。“我想去艾拉大棚屋。”他说,“那儿的女孩儿,你认得吗?”
那里有个女孩儿,我很熟,我就说“认得啊”。到那时候,我拿得准,他跟我玩我发明的这个游戏,唯一的目的,就是会女孩儿,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敏感话题:“有天晚上,我见着你老婆了……”
“我老婆?我老婆不在拉斯维加斯这地方。”我就把我在酒吧遇到那个女孩儿的事儿,告诉了他。“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在洛杉矶那儿,见到那个女孩儿和她朋友,就把她们带到拉斯维加斯这儿来。她们干的头一件事儿,就是用我的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朋友打电话,打了一小时啊。我气坏了,就把她们给轰了出去!她就到处告诉大家,说她是我老婆,呃?”因此,这事儿,算是澄清了。
我们到了艾拉大棚屋,大约15分钟,表演就开始了。这地方人多,屋子里没座位了。约翰就到总监那儿,说:“我,需要张桌子。”
“敢情,老大先生!几分钟就给您预备着。”约翰给了他小费,转身去赌了。同时,我转到后边去,女孩儿们都在那儿为演出做准备呢,问我的朋友在不在。她出来了,我跟她说,约翰老大跟我在一块儿。演出之后呢,他需要有人陪陪。
“没问题,迪克,”她说,“表演完了,我带几个朋友过来见你。”
我转到前面来找约翰老大。他还在赌。“你先一个人进去,”他说,“我随后就到。”
有两张空桌子,在紧前头,紧贴着舞台边儿。别的桌子,都满满当当的。我自己一个人坐下。就在开演之前,约翰进来了,表演女孩儿就出场了。她们看得见我就坐在这张桌子那儿,一个人坐着。还没等她们来得及以为我不过是个偶尔来玩玩儿的教授,现在她们该明白,我是一个大赌家啊。
最后约翰进来了,很快几个人就占了我们旁边那桌子——约翰的“老婆”和她朋友潘,还有两个男的!
我倾过身去,对约翰说:“她在那张桌子那儿。”
“是啊。”
她看到我在照顾约翰,所以她就从另一张桌子那儿侧着身子问我:“我可以和约翰说几句话吗?”
我一言不发,约翰也一言不发。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我倾过身去,对约翰说:“她想跟你说话。”
然后,他稍作沉吟。“可以。”他说。
我等的时间还长点儿,然后向她侧过身:“现在,约翰要对你讲话。”
她走到我们这桌来,开始卖弄她那套“翰翰”,坐得离他也太近了。我看得出来,事情还是稍微缓和了一点儿。
我喜欢搞点儿恶作剧,所以,每当他们有所缓和的时候,我就提醒约翰点事儿:“电话啊,约翰……”
“是啊!”他说,“打我电话,打一小时,什么意思啊?”
她说,打电话的是潘。
事儿又缓和了一点儿,于是我指出,把潘带到这儿,可是她的主意。
“是啊!”他说。(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好开心,这么玩了好一阵子。)
到表演结束的时候,艾拉大棚屋的女孩儿们来到我们这桌儿,我们跟她们聊,直聊到她们不得不去演下一场。然后,约翰说:“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小酒吧,离这儿不远。咱到那儿走一遭。”
我开车把他送到那个酒吧那儿,我们进去了。“看到那边那娘们儿了吗?”他说,“她实在是个好律师。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
约翰为我们做了介绍,找了个借口,去了洗手间。他一去不回头。我以为他还回来跟他“老婆”重修旧好呢,那样我就再开始捣乱。
我对那娘们儿说“嗨”,为我自己点了一杯喝的。(我玩的还是那一套: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想当绅士。)
“你可知道,”她对我说,“在拉斯维加斯,在律师当中,我是数得着的。”
“哦,数不着,数不着你,”我淡淡地回答,“在大白天的时候,你或许是个律师;但是,现在,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小酒吧里,鬼混,如此而已。”
她喜欢我,我们到了好几个地方跳舞。她舞跳得真不赖,我呢,爱跳舞,所以我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
接下来,正跳着舞呢,冷不丁地,我后背疼起来。那是一种剧痛,而且来得突然。我现在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一连三天三夜,我搞这些疯狂的冒险,我是彻底虚了。
她说,她要把我带到她家去。我一钻到她床上,砰腾一声,就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晨,我在这张漂亮的床上醒来。窗外阳光灿烂,却不见她的踪影,有一个女仆在那儿。“先生,”她说,“您醒了啊?早饭给您预备好了。”
“那个,呃……”
“我给您拿去。您喜欢吃什么?”她把整张早餐菜谱念了一遍。
我点了早饭,在床上吃了——在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的床上;我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不知道她从哪儿来。
我问了这女仆几个问题,可她对这个神秘的女人,也是一无所知:她刚刚被雇到这儿,这是她上班的第一天。她还以为我是这家的男主人呢,我倒问她问题,这叫她好生纳闷。我穿好衣服,最后离开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神秘的女人。
我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就坐下来把各种赌博的概率都算出来了,我发现掷骰子的概率是0.493的样子。如果我赌1块钱,只需要花费我1.4分钱。于是,我心里想:“为什么我这么不情愿赌?这几乎不花什么钱啊!”
于是我就开始赌,一眨眼,我就一口气输了5块钱——1块、2块、3块、4块、5块。我本来以为只会输7分钱,但我输了5块啊!我从此以后再也没赌过(我是说,没用自己的钱赌)。才一试手,就输,我很幸运。
有一次,我和一个表演女孩儿一块儿吃午饭。下午这个点儿,静悄悄的;不像别的时候那样,人都急匆匆的。她说:“看那边儿那主儿,正穿过草地的那位?那是‘希腊人尼克’,一个职业赌棍。”
我已经对拉斯维加斯的全部赌博概率了如指掌,我就说:“他们怎么能够拿赌博当职业呢?”
“我喊他过来。”
尼克过来了,她为我们做了介绍。“玛丽莲说你是个职业赌家。”
“她说的没错儿。”
“那个,我想知道,你靠赌博过日子,这怎么可能,因为在赌桌上,胜算是0.493。”
“你说得对,”他说,“我会给你讲明白。我不在桌子上赌,也不干任何那类事儿。我只是在机会对我有利的时候才赌。”
“啊?什么时候机会对你有利啊?”我满腹狐疑地问。
“实际上很容易,”他说,“我在桌子边儿站着,等有个家伙说,‘我要9点,它就来9点!’这家伙兴奋了;他以为那会是9点,他想赢。可我知道全部数字的概率,于是我就对他说,‘我以4块赌你3块,我赌不是9点’,时间长了,我会赢。我不在桌子上赌;我和在桌子上玩儿的那些心存偏见的人赌——他们迷信幸运数字。”
尼克继续说:“既然我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事儿就更容易了,因为大家甚至在知道概率不很有利的时候,也还是要和我赌,只为有机会跟大家讲怎么打败希腊人尼克,这得在他们赢了的时候才成。因此,我真的是靠赌博过日子的,很好玩儿啊!”
因此,希腊人尼克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人很好,很有魅力。我感谢他为我解释这事儿;现在我明白了。我一定要理解这个世界,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