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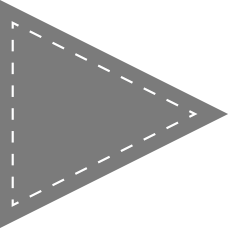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什么话都会说
什么话都会说
在巴西的时候,我玩命学当地语言,拿定主意用葡萄牙语讲物理课。我一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得到邀请,参加巴舍尔教授做东的聚会。我到场之前,巴舍尔告诉客人:“费曼这个家伙,学了几句葡萄牙语,就自以为聪明,咱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太太,就这位(百分之百的白人),在中国长大。咱们让她用中国话跟费曼打招呼。”
我被蒙在鼓里,溜达着来参加聚会。巴舍尔把我引荐给这些人:“费曼先生,这位是什么什么先生。”
“请来会会费曼先生。”
“这位是什么什么先生。”
“幸会,费曼先生。”
“这位是史密斯太太。”
“哎,您好!”她说,还鞠躬。
我吓了一跳,我琢磨着,只好以同样的派头作答了。我礼貌地向她弯弯腰,信心十足地说:“啊,垒好!”
“哦,我的上帝!”她叫起来,自己倒绷不住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我说普通话,他说广东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