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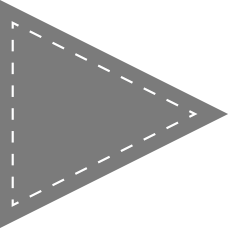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又是这个美国人!
又是这个美国人!
有一次,我捎带了一个搭便车的,他告诉我南美多么有意思,还说我一定得到那儿去一趟。我发牢骚,说语言不通,但他说,去学就是——问题不大。我就想了,主意不错:我要到南美。
康奈尔大学有外语课,用的仍然是战时的办法:大约十个学生一个小组,一个外国老师只讲外国话——再没别的。在康奈尔大学,由于我是个面相年轻的教授,我就决定参加一个班,像个一般学生似的。还因为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到南美的什么地方,我就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那儿大多数国家都说西班牙语。
因此,等到语言班报名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外边,等着到教室里去,就在这当口,一个魅力四射的金发碧眼的妞儿,飘然而至。你知道,你立刻会有什么感觉,哇噻!这不是天仙下凡吗!我暗自念叨,“或许她要参加西班牙语班——那可就太美了!”可是,不,她款步进了葡萄牙语班。于是我琢磨着,管它的——我或许也可以学学葡萄牙语。
我开始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可我那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观点冒出来了,我说:“别,决定说哪种语言,这理由站不住脚。”于是我就又折回去,报名参加西班牙语班,心里却是一百个不乐意。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物理学会的会议,我发现自己坐在翟米·第奥诺(Jaime Tiomno)旁边,他是巴西来的,他问我:“这个夏天,准备干什么?”
“我正琢磨着,到南美走走。”
“哦!为什么不到巴西来?我会在‘物理研究中心’给你弄个位置。”
这么说,我现在必得改弦更张,学葡萄牙语了!
我在康奈尔大学找到了个葡萄牙的研究生,每个星期他教我两次课,所以我可以把我已经学到的西班牙语都改成葡萄牙语。
在飞往巴西的飞机上,我碰巧和哥伦比亚的一个家伙坐在一起,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我不跟他说话,因为我不想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混成一团。但坐在我前边的两个家伙,说的是葡萄牙语。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真正的葡萄牙语;我的那位老师,说得又慢又清楚。这里的这俩家伙,说话跟爆豆儿似的,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我连“我”或者“这个”这两个词儿都听不清,什么也听不清。
最后,等我们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停机加油的时候,我凑到这俩伙计那儿,用葡萄牙语,或者我自以为是的葡萄牙语,慢慢说:“打扰了……你们能够听明白……我现在对你们正在说什么吗?”
“ Pues nao, porque nao ?”——“能啊,干吗听不明白?”他们回答。
于是我就尽力跟他们解释,说我在学葡萄牙语,现在都学了几个月了,但是还没有听到过在谈话中的葡萄牙语,在飞机上我一直在听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
“哦,”他们笑着说,“
Nao e Portugues!E Ladao!Judeo!
”他们在说:他们说的那种葡萄牙语并不纯粹,就好像犹太人说的那种德语的意第绪语
 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学德语的家伙,坐在两个说意第绪语的后头,想琢磨出他们在聊个啥。他们说的显然是德语,但不管用。他想必是没把德语学到家。
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学德语的家伙,坐在两个说意第绪语的后头,想琢磨出他们在聊个啥。他们说的显然是德语,但不管用。他想必是没把德语学到家。
等我们回到了飞机上,他们指给我看另外一个人,他真说葡萄牙语,所以我就挨着他坐了。他一直在马里兰州研究神经外科,所以和他谈话,来得容易——但我必须跟他谈“ cirugia neural, o cerebreu ”(“神经循环、神经中枢”)之类的“复杂”东西。比较长的英语词,实际上很容易翻译成葡萄牙语,因为唯一的区别只是词尾不同:英语的“-tion”在葡萄牙语中是“-a~o”;“-ly”是“-mente”,如此等等。可是,等他朝窗外看,说了个什么简单的东西的时候,我却摸不着头脑了:我不会翻译“天是蓝的”。
我在累西腓(Recife)下了飞机[巴西政府负责我从累西腓到里约(Rio)的旅费]。恺撒·雷提斯(Cesar Lattes)的岳父、妻子和另一个人来接我。雷提斯是位于里约的“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两个男人去取我的行李的时候,这位太太用葡萄牙语对我说:“你说葡萄牙语啊?你是怎么学葡萄牙语的啊?”
我回答得很慢,费了好大的劲。“首先,我还是学习西班牙语……然后我发现我要去巴西……”现在我想说的是“所以,我学了葡萄牙语”。但是,我想不起“所以”是怎么说的。我知道怎么说比较大的词儿,因此我是这么结束这个句子的:“CONSEQUENTEMENTE, apprendi ;Portugues!”——“因此之故,我学了葡萄牙语!”
两个男人带着行李回来了,她说:“哎,他会说葡萄牙语!而且还会用‘因此之故’这种了不得的字眼儿呢!”
接着,广播喇叭传来一个通告。到里约的航班取消了;到那儿的航班,星期二才有——但我最迟也得在星期一到达里约。
我觉得非常不安。“或许有货机。我坐货机得了。”我说。
“教授!”他们说,“累西腓这儿实在不错。我们带你到各处看看。干吗不放松一下——你现在是在巴西啊。”
那天晚上我在城里溜达,遇到一小群人围着看马路中间的一个长方形大坑——挖这坑是为了铺设排污管道什么的——坑里边,一辆小汽车,踏踏实实地坐在里头。事儿有点儿巧:这坑把车嵌得严丝合缝,车顶棚刚好与路面齐平。工人在傍晚收工的时候,懒得立几个标志,而那个家伙也果真把车开了进去。我注意到了一个区别:我们挖坑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绕行标志,还有闪闪发光的灯来保护我们。在那儿,他们挖了个坑,等一天的活儿干完了之后,就那么走人了。
不管怎么说,累西腓是个不错的城市,我也确实等到下星期二才飞到了里约。
等我到了里约,我见到了恺撒·雷提斯。国家电视台想为我们的会面拍点儿录像,所以他们就开拍了,但不录声音。摄像师说:“摆出你们正在谈话的样子。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成。”
雷提斯就问我:“你找到一本枕边词典(当地女孩)了没有?”
那天晚上,巴西的电视观众,看到这位“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欢迎来自美国的访问教授,但大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谈的,竟然是找个女孩儿度此良宵!
等到了中心,必须决定我讲座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
雷提斯说:“学生喜欢下午。”
“那就下午吧。”
“可下午在海滩上玩才好,所以,你为什么不在上午讲座,下午你就可以到海滩上逍遥。”
“但你说学生喜欢在下午听讲座。”
“那个你不必担心。照对你最方便的办法来!下午到海滩玩去。”
因此,我学会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看待生活的方式。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急匆匆的。其次,如果事情对你比较好,那用不着担心!于是,我就在上午上课,下午到海滩上玩儿。早知道有海滩,那我首先就会学葡萄牙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我原本想用英语上课,可我注意到:当学生用葡萄牙语向我解释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听不大懂,虽然我还是知道一点儿葡萄牙语的。他们说的是“增加”还是“减少”,是“不增加”还是“不减少”,还是“慢慢减少”,我是不大清楚的。但是,在他们苦挣苦扎地说英语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些“啊啪”或者“度恩”之类的声音;尽管他们发音稀松,语法勉强,我还是能猜出他们想说什么。因此,我明白了,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话,想教他们,最好是我来说葡萄牙语,我说得蹩脚就蹩脚吧。那样的话,他们听起来会容易些。
我第一次在巴西待了六个星期,那时我得到了邀请,要在“巴西科学院”讲个话,讲我刚刚做完的量子电动力学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要用葡萄牙语讲这个话,中心的两个学生说会帮我的忙。我开始把我的讲话用绝对稀松的葡萄牙语写出来。我是自己写的,因为如果让他们来写,我不认识的词儿就太多了,也读不好。因此,我写,他们改正语法,改正错字,弄得好一点儿,但文字水平,仍然允许我读得容易,多少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帮助我读得绝对正确:“de”应该介于“deh”和“day”之间——一定得读成这样。
我到了“巴西科学院”的大会上,头一个讲话的,是个化学家,站起来,发言——用英语。他这是为了表示礼貌,还是怎么的?我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因为他的发音糟透了;但是,或许别人都有相同的口音,所以他们能听得懂吧;懂不懂的,我也不知道。接着,另一个家伙站起来,用英语发表他的讲话!
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我很抱歉;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的讲话没用英语来准备。因此,请原谅,但我是不得不用葡萄牙语来发言了。”
于是我就读这个东西,大家都听得很愉快。
下一个家伙站起来说:“学习美国同事的榜样,我也用葡萄牙语讲话。”因此,就我所知,我把“巴西科学院”的语言传统改变了。
几年后,我遇到了个从巴西来的人,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在科学院讲话的头几句。很明显,我的讲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这种语言,我觉得很难,我就学而不倦,看报纸,等等。我一直坚持用葡萄牙语上课——我称之为“费曼葡萄牙语”,我知道,它不可能和地道的葡萄牙语是一个东西,因为我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我不知道街上的人讲的是什么。
因为我太喜欢我第一次在巴西的经历,一年之后我又去了,这一次是10个月。这一次我在里约大学讲课,他们本该给我钱的,但从来没给,因此中心一直在给我里约大学本该给我的钱。
我最后住在位于克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上的一家旅馆里,旅馆名叫“米拉玛”(Miramar)。住了一阵子,我住在了十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可以从窗口看大海,看海滩上的女孩儿。
后来才知道,这家旅馆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lines)的飞行员和女乘务员“下榻”的地方。“下榻”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儿叫人反胃。他们的房间都在四楼,三更半夜的时候,常有人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在电梯里串上串下。
有一次,我离开旅馆几个星期在外旅行,到我回来的时候,经理告诉我,他不得不把我的房间订给了别人,因为那是最后一个空房间,他已经把我的东西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那个房间正好在厨房那边。人们通常在这里住不长的时间。这位经理算是琢磨透了:我是唯一看得出住在那个房间有好处的一个家伙;非常清楚的是,我会忍受油烟味儿,不会发牢骚。我真没发牢骚:房间在四楼,离女乘务员很近。这省了不少麻烦。
航空公司的人,不知怎么,厌倦自己的生活;真够奇怪的是,晚上她们常去酒吧喝酒。我喜欢她们这些人,为了显得合群儿,一个星期好几个晚上,我都和她们一块儿去酒吧喝上几杯。
有一天,大约在下午三点半,我在克帕卡巴纳海滩对面的人行道上溜达,遇到一个酒吧。我突然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我要的就是这个;说着娘家人儿,孩子他舅舅就来了。此时此刻,我就是想喝一杯!”
我就开始迈步进酒吧,可我突然脑子里想:“且慢!这才下午正中间,这儿什么人也没有。没什么社交理由要喝酒啊。可你必得要喝一杯,你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从那以后,我再也滴酒不沾了。我想,实际上,我并没有处在什么危险之中,因为我发现,悬崖勒马,并不算难。但那种我不理解的强烈感觉,吓着我了。你知道,我不想毁了这个最令人愉快的机器,这机器使生活成为这么一大乐子。我从这种思考过程中,得到了好大的乐趣。后来,尽管我对幻觉很是好奇,但还是踌躇于拿迷幻药亲身实验,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在巴西快到年终的时候,我带着一位空姐——一位扎着辫子的、非常可爱的女孩儿——到博物馆去。在我们走过埃及部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向她讲这么些事儿:“石棺上的翅膀,意思是这个这个;这些瓶子,是用来放人的内脏的;转过那个角落,那里应该有那个那个……”我暗自思忖:“你自己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个东西?是从玛丽·娄(Mary Lou)那里听来的啊!”——她不在身边,我觉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尔大学遇到玛丽的,后来,等我去了帕萨迪纳(Pasadena)
 ,我发现她已经来到了附近的威斯特伍德(Westwood)。我喜欢她有一段时间,但我们经常吵架;最后,我们断定事情没希望了,我们就分手了。但是,一年的时间,和这位空姐里出外进,却无功而返,我灰心丧气。因此,当我给这女孩儿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玛丽·娄实在是个好女孩儿,我们不应该吵的。
,我发现她已经来到了附近的威斯特伍德(Westwood)。我喜欢她有一段时间,但我们经常吵架;最后,我们断定事情没希望了,我们就分手了。但是,一年的时间,和这位空姐里出外进,却无功而返,我灰心丧气。因此,当我给这女孩儿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玛丽·娄实在是个好女孩儿,我们不应该吵的。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求婚。明白人都会告诉我,这是危险的:你在外头,除了信,你什么也没有,你觉得寂寞了,你就只记得那些美好的事情,忘记了你们是为什么吵架的。结婚,也解决不了问题。一结婚,争吵又起,这桩婚姻只延续了两年。
美国使馆有个人,知道我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我第一次在巴西的时候,曾经听过在街上练习的一个桑巴乐队的演奏,我也想多了解一些巴西音乐。
他说,有一个叫“土风”的小乐队,每星期在他的公寓里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有三四个人——一个是这公寓的看门人——他们在这个公寓演奏的音乐非常安静,他们没有别的地方演奏。有个家伙打小手鼓,他们称之为“盼得乐”(pandeiro),另一个家伙拨弄小吉他。我总是听到有敲鼓的声音,但没有鼓啊!最后,我琢磨出那是小手鼓的声音。那家伙演奏小手鼓的手法很复杂,手腕乱转,用拇指敲打鼓皮。我发现这有趣,多少学会了怎么演奏盼得乐。
稍后,狂欢节即将来临。这是个展示新曲子的季节。他们并不一年到头推出新曲子和新唱片;他们等到狂欢节,才全盘端出来,这可令人兴奋啊。
原来,这位看门人是一所小桑巴“学校”的作曲家——说它是个学校,搞的却不是教育,而是沽名钓誉——在克帕卡巴纳海滩上沽名钓誉。这乐队名叫“Farqantes de Copacabana”,意思是“克帕卡巴纳的骗子”,这很合我的口味儿,他还请我入伙儿。
原来这个桑巴学校是这么个东西:大家从远处的法维拉(favelas)——也就是这城市的贫民区——赶来,在一处正在施工的公寓楼建筑工地的后面集合,为狂欢节排练新曲子。
我选了一样名叫“福瑞吉得乐”(frigideira)的东西来演奏,那是个金属造的玩具平底锅,直径15厘米,用小金属棍儿来敲。它是一种伴奏乐器,伴随着主要的桑巴曲子和节奏,它弄出的动静,脆而快,使曲子丰富多彩。因此,我就试着玩这个东西,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乐声一路喧嚣,跟60年代那股子狂劲儿相似。大家闹得正欢,突然之间,首席演奏家,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大喝一声:“停!叮住,叮住!——等一下。”大家都僵在那儿。“福瑞吉得乐,出了毛病!”他声如雷鸣,“ O Americana, outra vez! ”(“又是这个美国人!”)
于是我就觉得不自在。我不停地练习。我抓着那两根棍儿,沿着海滩走,手腕儿乱转。练啊、练啊、练啊。我一直在捣鼓这个,但总觉得不如人,总觉得扯了人家后腿,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好了,越来越接近狂欢节了。有一天晚上,乐队队长和另一个家伙在谈事儿,接着,队长开始转着圈儿地走,在选人呢:“你!”他对一个号手说。“你!”他对一个歌手说。“你!”——他指着我。我还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淘汰的呢。他说:“到前头去!”我们向前走到建筑工地前边——我们五六个人——那儿有一辆旧卡迪拉克敞篷小汽车,篷子拉了下来。“上车!”队长说。
车地方不够我们坐,我们有几个人得坐在后车帮上。我对我旁边的那家伙说:“他在干吗?——打发我们滚蛋?”
“ Nao se, nao se. ”(“我不知道。”)
我们的车离开大路,往边上的高坡上开,停在悬崖的边上,俯瞰着大海。车停了,队长说:“下车!”——他们把我们带到悬崖边上!
果然,他说:“站成一排!你第一,你下一个,你下一个!开始奏乐!现在,齐步走!”
我们会齐步掉下悬崖的——多亏有条向下的陡坡儿。我们的小乐队就这样走下了这条小路——号、歌手、吉他、盼得乐、福瑞吉得乐——来到了一个在树林里举办的露天晚会上。我们被挑出来,不是因为队长想把我们打发走;他派我们到这个私人晚会上,那儿需要桑巴舞曲!后来,他敛了点儿钱,好为我们乐队买服装。
此后,我感觉好些,因为我明白,在他挑选演奏福瑞吉得乐的人时,他选了我!
还有一件事儿,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过了一段时间,从另一个桑巴学校来了个家伙;那学校在勒巴伦(Leblon),在更远的那边的那个海滩上。他想加入我们学校。
老板说:“你从哪儿来的?”
“勒巴伦。”
“你演奏什么?”
“福瑞吉得乐。”
“那好。让我听听你演奏的福瑞吉得乐。”
这家伙于是就操起他的福瑞吉得乐和他的金属棍儿,接着,“卜拉哒哒,哧可啊哧可”,嚯!妙啊!
老板对他说:“你到那边去,挨着美国人站着,你会学会怎么演奏福瑞吉得乐!”
我的推测是这样:这就像一个说法语的人到了美国。刚开始,他们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你简直听不明白他们说什么。后来,他们坚持练习,终于说得蛮像样儿,而且你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有一种挺悦耳的弯弯儿——他们的口音颇为好听,你很爱听他们说话。所以呢,我在演奏福瑞吉得乐的时候,想必也有某种口音,因为我不可能和那些演奏了一辈子福瑞吉得乐的家伙比试比试;那必定是某种傻乎乎的口音。但是,不管是什么吧,我成了一个相当成功的福瑞吉得乐演奏家。
有一天,就快到狂欢节了,桑巴学校的队长说:“好了,我们要到街上排练走步。”
我们都从建筑工地出发到了街上,街上车水马龙。克帕卡巴纳的街道总是一团乱。不管你信不信,有一条电车线,电车在那儿往一个方向走,汽车在那儿朝另一个方向走。当时正是克帕卡巴纳的上班高峰时间,而我们是打算齐步走到“大西洋大街”的正中间。
我对自己说:“耶稣!老板还没弄许可证呢,他还没征得警察的同意呢,他什么也没干。他决定我们就那么出去。”
于是我们就出发到了大街上,周围的每一个人,兴高采烈。几个看热闹的,自告奋勇,拿根绳子,把我们围在一个大正方形里,免得行人闯进我们的行列。人们把脑袋探出窗外。人人都想听到新的桑巴舞曲。场面令人非常兴奋!
我们一开始行进,我就看到一个警察,在马路对面不远处。他张望着,看那儿闹腾什么,然后让车辆改道行驶!一切都不是正式的。没人做过安排,但事儿还搞得不错。人们在我们四周扯着绳子,警察在让交通改道,行人在拥挤,交通被堵塞,可我们却畅行无阻!我们走完了大街,转过街角,转遍了这个乱糟糟的克帕卡巴纳,一切都是率意而发的!
最后,我们停在一座公寓楼前的小广场上,老板的妈住这儿。我们在这地方站着演奏,那家伙的妈,他姑妈,七大姑八大姨,倾巢而出。她们还戴着围裙呢;她们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呢,你看得出来,她们喜出望外——她们几乎要哭出来。
这才是人性啊,确实美好啊。大家都从窗口探出身来——难以形容啊!我记起了我上次来巴西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桑巴乐队——我是多么热爱这种音乐,几乎欣喜若狂了——现在,我身在其中!
顺便告诉你,我们那天绕着克帕卡巴纳游行的时候,我看到人行道上的一群人当中,有两位美国使馆的年轻女士。下星期,我接到使馆的一封信,说:“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喋喋不休的一堆废话,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巴美关系似的!所以我做的事才是“大”事嘛。
言归正传,为了去排练,我不想穿平常穿的那种衣服,就是我到大学时穿的那种。乐队里的人很穷,只有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就穿了一件旧内衣,同样旧的裤子,等等,这样我看起来就不过分特别了。可这样我就没办法从克帕卡巴纳海滩、太平洋大道上我住的豪华宾馆的门厅里进出了。所以我总是坐电梯一坐到底,从地下室里出来。
接近狂欢节,将要举行一场特别的比赛,比赛在几个海滩桑巴学校之间展开——克帕卡巴纳海滩,爱帕尼玛海滩,还有勒巴伦海滩;有三四个乐队,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穿着演奏服,沿着太平洋大道一路走下来。穿着这种花里胡哨的狂欢节服装,我有那么一点儿不自在,因为我不是个巴西人。但我们原本应该打扮成希腊人的模样,因此我琢磨着我和他们一样像希腊人。
在比赛那天,我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领班的服务员,经常看到我一听到桑巴舞曲,就在餐桌上击节以和之,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天晚上会有你喜欢的事儿! tipico Brasileiro ——最具巴西特色:桑巴学校的游行,就从旅馆前边经过!这音乐太棒——你可得听听。”
我说:“啊哈,我今天晚上有点儿忙。我不知道能不能腾出身来。”
“哎呀!但是你会爱得不得了啊。你千万不可错过!那才是tipico Brasileiro !”
他很固执,我一个劲儿告诉他我想我不会在那儿看的,他大失所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跟平时那样从地下室溜出去。在建筑工地那儿,我们披上行头,一百个穿着纸做的行头的巴西希腊人,开始沿着太平洋大道游行,我走在后边,演奏福瑞吉得乐。
太平洋大道两侧,人山人海;大家都把脑袋探出窗外,我们正往米拉玛旅馆那边走,我就住那儿。那儿的人都站在桌子椅子上,大家蚁涌蜂攒一般。我们的乐队经过旅馆前边的时候,我们一直演奏着,跟60年代一样疯狂。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员跳上跳下,他指着我,在这人声鼎沸之中,我听得见他喊:“啊,教授!”领班的服务员这才明白,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可能站在那里看比赛——我是参赛的啊。
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个我老在海滩上遇到的女士,她在大道边上有一座公寓楼。她跟几个朋友,高高在上,观看桑巴学校的游行。当我们走过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喊道:“听弹奏福瑞吉得乐的那家伙——他棒啊!”我成功了。没人指望我能做这件事儿,可我硬是做成了。
狂欢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学校露面的人却不多。为这一盛事,我们做了一些特别的服装,但现在人却不多。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不可能胜过城里真正大牌的桑巴学校;我不知道。我认为,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又是排练,又是游行,都是为了狂欢节;可狂欢节到了,许多队员却不见人影了,我们的实力就不怎么样了。就连我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几个人还半路开溜了呢。结果是这样,真够滑稽!我从来也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在海滩上的比赛中出人头地,才是他们主要的兴奋点和乐趣所在,在海滩上,大多数人水平都差不多。顺便说一句,我们乐队真的赢了。
在巴西待的10个月,我对轻原子核的能价发生了兴趣。我在旅馆房间里把这事儿的全部理论都搞出来了,但我想看看试验数据是怎么样的。这个新玩意儿,就是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Kellogg)实验室的专家正在搞的东西,我就通过业余无线电跟他们联系——把时间安排好了。在巴西我遇到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大约每星期我都到他家里一趟。他和在帕萨迪纳的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进行联系;因为这事儿有点儿非法,他就给了我一个呼号,他说:“现在我将把你转给WKWX,他就坐在我旁边,等着跟你说话。”
我就说:“这是WKWX。请告诉我硼原子的那些能价间隔,就是我们上星期谈的那个。”诸如此类。我利用试验数据来修正我的常数,并检查我的路子对不对。
头一个家伙去休假了,但他让我到另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那儿去。这第二个家伙是个盲人,他有自己的电台。这两个人都不错,我利用业余无线电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的联系,很有效率,这对我很有用。
就物理学自身而言,我干的活儿可不少,而且都有道理。后来别人也搞出来了,证实了我的理论。但我觉得,有很多参数需要校准——太多的“关于参数的现象调整”,为的是把一切都弄妥帖——我拿不准这么个搞法是不是有用。我想对原子核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始终不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事儿,所以我对此再也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说到巴西的教育,我的经历相当有趣。听我课的那些学生,最后都当老师,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在科学方面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些学生已经学了很多课程,我教的课是他们在电学和磁学方面的最高级的课程——麦克斯韦方程式之类。
里约大学分散在全城好几座办公楼里,我在一座俯瞰海湾的建筑里上课。
我发现了一个好奇怪的现象:我问一个问题,学生们随口就答得上来。但是,下一次我还是问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问题——他们却完全答不上来!比方说,有一次,我在讲偏振光,给了他们一些偏振片。
偏振片只允许电矢在某种方向上的光通过,于是我就向他们解释,看看偏振片是暗的还是亮的,你就能说得出来光是怎么发生偏振的。
他们首先拿起两个偏振片,转动它们,直到它们允许最大量的光通过。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说得出来,这两个偏振片允许光在相同的方向上发生偏振——能从一个偏振片通过的光,也能从另一个偏振片通过。但我接着问他们,如果只有一个偏振片,你怎么说得出来偏振的绝对方向呢?
他们茫然无知。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需要一点儿机灵劲的,所以我给了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边海湾反射过来的光。”
没人说话。
然后我说:“你们听说过布鲁斯特角吗?”
“听说过,先生!布鲁斯特角是光在某种介质上的反射角,这种介质的折射率允许光完全偏振化。”
“当光被反射的时候,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先生,光的偏振方向与反射面垂直。”连我自己还得想一想呢;他们却硬生背下来了!他们甚至还知道,那个角度的正切值等于折射率呢!
我说:“然后呢?”
仍然默无声息。他们刚刚告诉我,光以一定的折射率从某种介质(譬如外面的海湾这种介质)上反射回来,就成了偏振光;他们甚至连光发生偏振的方向也告诉了我。
我说:“看看外面的海湾,透过偏振片来看,现在,转动偏振片。”
“哦哦哦,光发生偏振了!”他们说。
在进行了许多调查之后,我最后琢磨透了:这些学生把什么都死记硬背下来,但那是个什么意思,一概不知。当他们听说“以某一折射率从某种介质上反射回来的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所谓介质就是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光的方向”就是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朝它看的那个方向,等等。一切都完全是死记硬背的,但没有什么东西被翻译成有意义的词句儿。我问:“什么是布鲁斯特角?”找台计算机,把键敲准了就成。但是,如果我说:“看看水。”鸦雀无声——“看看水”这话隐藏着什么意思,他们莫名其妙。
后来,我在工学院听他们的课。课的上法,翻译成英语,是这样的:“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将产生出……相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将产生出相等的加速度。”学生们坐在那儿,记录口述。趁着教授重复句子的当口,检查是不是记得正确。然后,他们记第二个句子,再记,再记。明白教授正在讲的是具有相同惯性矩的一些物体的,我是唯一的一个,而他讲得相当难琢磨。
我看不出他们这样学怎么能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在讲惯性矩;但没有下面这种讨论:你把重物抵在门的另一边,你推门有多么费力;比较一下,你把重物放得靠近合叶一些,又如何——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下课后,我对一个学生说:“你把笔记都记好了——笔记有什么用?”
“哦,我们研究笔记,”他说,“我们要考试的。”
“考试,是怎么个考法?”
“非常容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个试题。”他看着他的笔记本说,“‘在什么时候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它们的力矩产生了相同的加速度。’”您看,大家都能通过考试,都能“学会”这些玩意儿;除了他们背诵下来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以后,我又看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那是个口试,我得到允许,可以旁听。有个学生,绝对超一流:一切问题,对答如流!主考问,什么是反磁性,他回答得很完美。主考又问:“光以一定角度穿过有一定厚度的材料板,折射率为N,光有什么变化?”
“先生,它出来的时候,与自身平行——位移。”
“位移了多少?”
“我不知道,先生,但我能算出来。”他果真算出来了。他很优秀。但到那个时候,我仍然疑心重重。
考试之后,我走到这个聪明的年轻人那儿,我告诉他,我是从美国来的,我想问他几个问题,而且我这么问,无论如何不会影响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可以举出几个抗磁性物质的例子吗?”
“不能。”
然后我问:“如果这本书是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什么东西;如果我把这块玻璃倾斜起来,那么物像会有什么变化?”
“它会偏斜的,先生,会偏到你转动这本书的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没把它和镜子弄混了,是吧?”
“没弄混,先生!”
刚才在考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光线会位移,与自身平行,因此物像会移到一边去,但不会以任何角度转动。他甚至计算出了物像会移动多少,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有折射率的材料,没意识到他的计算本来就适用于我的问题。
我在工学院开了物理数学方法这门课,讲课过程中,我试图表明如何用试错法来解决问题。这东西,大家通常都不知道,于是我就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来演示这个方法。80来个学生当中,只有8个完成了第一次作业,这让我很吃惊。因此,我在上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要真的去试试,不要作壁上观,不要只看我做。
这节课下课之后,几个学生,组成了个小代表团,来找我,告诉我说,我不理解他们的背景,说不必搞这些问题照样学习,说他们已经学过算术,说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水平之下。
我就继续教这个班,而且无论学的东西多么复杂,或者无论多么明显地高级,他们从来就没交过什么鬼作业。我当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做不了!
我没能让他们做成的另一件事儿,是提问。最后,一个学生对我解释说:“如果在上课的时候我问您问题,过后大家都要对我说,‘你干吗在课上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想学点儿什么,可你问问题,不让他讲。’”
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坏作风,明明是谁也不明白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可他们把一个人打压下去,就好像他们真明白似的。他们都假装明白,如果有个学生有那么一刻承认什么东西把他搞昏头了,提出一个问题,其他的人就采取高人一等的态度,那做派就好像没什么东西不清楚似的,告诉那个学生他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对他们解释,在一起研究、讨论问题、把想法说个畅快彻底,这办法是多么有用;但他们连这个也不做,因为问了别人,就丢了面子。这太可悲了!他们出力不少,人也聪明,但却使自己陷入了这么一种滑稽的精神状态,这种奇怪的、自体繁殖式的“教育”,没意义,完全没意义!
学期结束之际,学生们要我发表一个讲话,谈谈我在巴西的教学经历。讲话的时候,在场的,不光是学生,还有教授,有政府官员,因此我要求他们做出允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说:“没问题,当然。这是个自由国家嘛。”
我就这么进来了,带着大学第一学期他们用的那本基础物理课本。他们认为这书特别好,因为它是用不同字体印刷的——粗黑体,意思是最重要的东西,得记住;颜色浅的,不那么重要,诸如此类。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会说这书的坏话,是吧?写这书的人,在这儿呢,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本很好的书。”
“你们答应过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讲座大厅座无虚席。我给科学下了个定义,以此作为开场白,我说,科学是对自然的行为的理解。然后,我问:“为什么教科学?站得住脚的好理由是什么?当然,没哪个国家,能自称自诩是一个文明的国度,除非……啰里啰唆,啰里啰唆。”在座的人,频频点头,因为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这么个看法。
然后,我说:“这么想,是荒唐的,当然荒唐,因为,我们有什么必要觉得自己必得跟上另一个国家的脚步?我们搞科学,应该有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个不那么傻里傻气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别的国家也搞科学。”然后,我讲到了科学的功用,以及科学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诸如此类——实际上,我这是在逗他们呢。
然后,我说:“我讲话的主要目的,是想向诸位表明:巴西没教什么科学!”
我看得出,他们都燥热起来,他们在想:“什么啊?没教什么科学?这绝对是痴人说梦!科学课程,我们都有嘛。”
于是,我告诉他们,在我刚来巴西的时候,使我颇受震动的头几件事当中,有一件,是小学生在书店里买物理书。在巴西,有这么多孩子在学物理,比美国孩子起步早得多。可你在巴西找不到许多物理学家,这事儿透着怪——这是怎么搞的?这么多孩子,这么努力地学,却没什么收效。
然后,我用一个希腊学者来打比方,这个希腊学者热爱希腊语,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没有多少孩子学希腊语。但来到了另一个国家,他欣喜地发现,大家都在学希腊语——连小学里的小孩子也在学。他去为一个要在希腊语方面拿学位的学生当考官,问他:“关于真与美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有些什么看法?”——这学生答不上来。然后,他问这个学生:“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对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学生眼睛一亮,率尔答曰:“吧啦吧啦吧啦。”——口若悬河啊,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都告诉你了,一字不差啊,用漂亮的希腊语说的!
但是,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谈的那些东西,就是真与美之间的关系啊!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另外这个国家的学生,学希腊语,先是学字母的发音,然后学词儿,然后学句子和段落。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们背得下来,一字不差地背,却没有意识到那些希腊词儿,实际上意味着某种东西。对学生而言,那些词儿,全是做作出来的声音。没人把那些词儿翻译成学生能够理解的词儿。
我说:“在我看到你们在巴西教孩子们‘科学’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强的冲击波,是吧?)
然后,我把那本他们正在用着的基础物理课本举在手里。“在这本书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任何实验结果,有个地方例外,那儿有个球,正在滚下斜面,在那个地方,书里说,在1秒、2秒、3秒、多少多少秒之后,这球滚出多远。这些数字有‘误差’——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些数字,你还当是在看实验结果呢,因为这些数字,比理论上的数值大一点儿或小一点儿。这书甚至谈到了必须纠正实验误差的问题——这很好。问题是:如果你根据这些数值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是多少的话,你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一个沿着斜面向下滚的球,如果你真动手让它滚的话,它还有惯性,这惯性让它转动,如果你真做这个实验的话,你将得到正确答案的5/7,因为需要额外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因此,这唯一一个实验‘结果’的例子,还来自假实验呢。没人曾经滚过球,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那种结果!”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我继续说,“随便翻到哪一页,随便把我的指头按在哪儿,然后读我按住的那个句子,我可以向诸位表明,我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怎么就不是科学,而是死记硬背,整本书都是如此。因此,我敢说,现在我随便翻到哪一页,当着在座各位的面,我用手指头按到这儿,给你们读这句话,让诸位自己看看。”
我就这么办了。扑啦扑啦扑啦——我指头按住一个地方,我开始读:“摩擦发光。摩擦发光是晶体摩擦时发出的光……”
我说:“就在这儿,你们看到科学了?没有!你们只是用另一些词儿来告诉一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你们没说到自然——你摩擦晶体发光,你摩擦的是什么晶体,为什么它们会发光。你们看到过有任何学生回家去试试这个吗?他没法儿试。”
“但是,如果你这么写,‘你拿着一块儿糖,在黑暗中用钳子夹它,你可以看到蓝盈盈的闪光。其他一些晶体也是如此。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叫作摩擦发光。’然后呢,有人就会回家去试了。然后呢,这就有了一个关于自然的体验。”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我的指头按住书的什么地方,无关紧要;这种例子满篇皆是。
最后,我说,我可看不出任何人怎么可能从这种自体繁殖式的体制中受到教育,在这种体制中,大家考试过关,再去教别人考试过关,但没人理解任何东西。“然而,”我说,“我必定说错了。我班上有两个学生,做得不赖;我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完全是在巴西受的教育。因此,这体制坏是坏,可有些人倒也有可能在其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这下可好了,我话讲完了,科学教育部门的一个负责人,站起来说:“费曼先生刚才对我们讲了一番逆耳之言啊。看来他是真正热爱科学啊,他的批评也是诚恳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听他的。我到这儿来,已经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在身,我现在才知道,我们是得了癌症啊!”——他坐下了。
这使别人得到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大家情绪高涨。大家都站起来提建议。学生们事先组成了一个什么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了出来,他们也让别人组成委员会,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在他的讲话末尾提到的那两个学生中的一个。但我不是在巴西受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只是今年才到了巴西。”
另一个在班里干得不赖的学生,也说了相似的事儿。我提到的那位教授,也站起来说:“在战争期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的,在那时,幸运的是,教授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学,因此我学到的全部东西,都是我自己读来的。因此,我实际上不是在巴西的体制下接受教育的。”
这个,我可没想到。我知道这个体制坏,但现在它是100%的坏——这可太糟糕了!
因为我是在美国政府一个项目的赞助下到巴西的,美国教育部要我写一个报告,谈谈我在巴西的经历,所以我把刚才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也写进了报告。后来,通过小道消息,教育部某人对此的反应是:“你该明白了,把这么一个幼稚的人派到巴西,有多么危险。傻乎乎的家伙;他只能制造麻烦。这里面的问题,他不明白。”恰恰相反!教育部这主儿,看到一个大学开了课程列表,什么都说得天花乱坠,就把这当真事儿,我觉得,他才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