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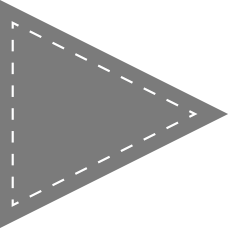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幸运数字
幸运数字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天,我在休息室坐着,无意听到几个数学家在讨论e x 的级数,把它展开就是1+x+x 2 /2!+x 3 /3!。每一项,都是通过把前一项乘以x并除以下一项的项数来得到的。比方说,为了得到x 4 /4!后面的那一项,你就把它乘以x并除以5。这很简单。
在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对级数着了迷。我已经用那个级数计算过e的值,看到新的那些项是如何很快变小的。
我喃喃自语,用那个级数来计算e的无论多少次幂,是多么容易(只要你用幂次来代替x即可)。
“哦,是吗?”他们说,“那好,e的3.3次方是多少?”有个玩笑大王说——我想那是涂基(Tukey)。
我说:“那容易,是27.11。”
涂基知道把它心算出来并不容易。“嗨!你怎么算的?”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知道费曼,他信口雌黄。那数,实际上不对。”
他们去找数学用表,就在他们找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27.1126。”我说。
他们在表上找到了。“对啊!可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只是把级数逐项加起来。”
“没人能那么快就把这个级数加起来。你必定是碰巧知道了那个数。e的3次方是多少?”
“干吗呀,”我说,“这活儿很累!一天只算一个!”
“哈!弄虚作假!”他们得意地说。
“那好吧,”我说,“是20.085。”
在他们查表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现在他们可就兴奋起来了,因为我又说对了。
在场的都是当年的几个大数学家,茫然不知我是怎么算出e的任意次幂的!其中的一个说:“他绝不可能只是在进行代换和加法运算——那太难了。有窍门的。你不可能随便算出像e的1.4次方这样的数。”
我说:“这活儿很累,但我给你面子,是4.05。”
在他们查表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说:“今天到此为止!”出去了。
其实是这样:我碰巧知道三个数——以e为底的10的对数(用来把数字从以10为底换为以e为底),值是2.3026(因此我知道e的2.3次方非常接近于10)。因为放射现象(半衰期),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是0.69315(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我还知道e(它的1次方)是2.71828。
他们要我计算的第一个数,是e的3.3次方,它等于e的2.3次方(等于10)乘以e,得27.18。在他们忙着瞎猜我是怎么算出来的时候,我在修正我的答案,减去了多出的0.026——因为以e为底的10的对数2.3026,是稍微多了一点儿。
我知道,再要我算一个数,那就算不出来了;刚才完全是碰运气。但是,那家伙接着问的却是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嘛,或者说是10乘以2。所以我知道得数是20多一点儿。在他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我是怎么算的当口儿,我又对答案做了0.693的调整。
现在,我真的知道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因为上一个数仍然是纯粹碰运气。但是,那个家伙说的是e的1.4次方是多少。那是e的0.7次方乘以它自身。因此,我只需要在4上面稍微加一点儿而已!
他们怎么也琢磨不出我是怎么算的。
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发现汉斯·贝特绝对是计算高手。比方说,有一次,我们要把几个数代入公式,最后算到48的平方。我就找玛珍计算器,他说:“是2300。”我开始按按钮,他说:“如果你要精确的数字,那就是2304。”
机器的得数是2304。“嚯!这可太神啊!”
“怎么计算接近50的数的平方,你不知道吗?”他说,“你先算出50的平方——是2500——再从2500里减去100乘以你的数和50之间的差(在这个例子里是2)。如果你要的是精确的数,那就把那个差数的平方加上去,那就是2304嘛。”
几分钟后,我们需要算出2(1/2)的立方根。用玛珍计算器算立方根,得先查数学用表,查出一个近似值。我开了抽屉找表——这次花的时间长些——他说:“大约是1.35。”
我用玛珍一试,对了。“你怎么算出这个的啊?”我问,“你知道求立方根的秘诀吗?”
“啊,”他说,“2(1/2)的对数是多少多少。这个对数的三分之一在1.3的对数多少多少和1.4的对数多少多少之间,那我就在这两者之间内插了一个数。”
因此,我发现了一点儿东西:第一,他背得下来对数表;第二,光是他做的内插计算量,我找数学用表、拿计算机敲键,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此后,我也想干这样的事儿。我记住了几个对数,开始注意事儿。比方说,如果有个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你会注意到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20乘以1.4,因此28的平方必定大约是400乘以2,或者说800。
如果有个人过来想算1除以1.73,你可以张口就来,是0.577,因为1.73近似于3的平方根,因此1/1.73必定是3的平方根的三分之一。如果要算1/1.75,那它刚好是7/4的倒数即4/7,而你记得1/7的循环小数0.142857142857……,于是得数就是0.571428……。
和汉斯用窍门儿快速计算,我得到了很多乐趣。我知道答案而他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少;等我答对了一个,他就开怀大笑。他几乎总能回答任何问题,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一。每个数都接近他知道的一个数——对他而言,这很容易。
有一天,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午饭的时候,在技术区,也不知道我从哪儿冒出个念头儿,反正我宣布:“任何人在10秒之内能说完的任何问题,我都能在60秒内答出来,误差10%!”
大家开始把他们认为可能算难的问题说给我,例如,计算1/(1+x 4 )的函数的积分,在他们给我的x的范围内,这东西几乎是不变的。有人给了我一个最难的问题,是算出(1+x) 20 中的x 10 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的时候答出来了。
他们都给我出难题,我得意扬扬,那时保罗·奥伦(Paul Olum)刚好从大厅走过。在来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保罗和我在普林斯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总是比我聪明。比方说,有一天,我正心不在焉地玩一个卷尺,就是你一按按钮,就啪地一下子缩回去的那种。尺子总是缩过头,打在我的手背上,真有点儿疼呢。“哎呀!”我叫起来。“我真是个呆子。老是玩这玩意儿,每次都打疼了我的手。”
他说:“你拿得不对劲。”他把这鬼东西拿过去,把尺子拉出来,按按钮,它好好地就缩回去了。不伤人的。
“哇!你是怎么弄的啊?”我喊道。
“自己琢磨!”
此后几个星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无论到哪儿,手里总在玩卷尺,手都打破皮了。最后,我受不了了。“保罗!我作罢了!你到底是怎么握的,让它打不着你?”
“谁说它打不着我?它打我也打得怪疼啊!”
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蠢啊。他愚弄我到处拿着个卷尺打自己的手,直打了两个星期!
刚才说到奥伦正走过吃午饭的地方,这帮家伙都兴奋不已。“嗨,保罗!”他们大声叫。“费曼可了不得!我们在10秒钟内给他出题目,可他一分钟就给得数,误差10%。你干吗不给他出个题目?”
他几乎连脚步也没停,说:“10的100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的嚣张气焰下去了:你必须把一个一百位数除以π!这可没指望了。
我有一次吹牛说:“任何人都得用路径积分来解决的问题,我就能用别的办法来得出答案。”
奥伦就给了我一个罪该万死的积分: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杂函数开始,把它的实部去掉,只把虚部留下,就得到了这么个积分。他已经把它展开了,所以它非得用路往积分法不可!他总是让我这样泄气。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伙计。
那是我头一次到巴西的事儿。我在我也不知道的什么时间吃午饭——我来饭店,总是来得不是时候——那地方只我一个顾客。我就着牛排(我喜欢)吃米饭,周围站着四个服务员。
一个日本人进了饭店。我以前见过他,看到他到处兜售算盘。他开始和服务员说话,向他们挑战:他说他算加法比他们谁都算得快。
服务员不想丢面子,他们就说:“是啊,是啊。你为什么不到那边,向那位顾客挑战呢?”
这人过来了。我抗议道:“可我葡萄牙语说得不好!”
服务员笑了。“数目字儿,容易。”他们说。
他们给我找来一支铅笔和纸。
这人让服务员喊出数字好加起来。他把我赢得好惨,因为在我把数写下来的当口,他却在拨弄算盘珠子的同时,得数已经出来了。
我建议服务员,在两张纸上写下相同的一些数,然后同时交给我们俩。这没造成多大变化。他还是胜过我许多。
可是,这人得意忘形了:他想显显别的本事。“Multiplicaa~o!”他说,要比乘法。
有个人写了个题,他又打败了我,但只是险胜,因为我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呢,这人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接着比除法。他有所不知的是,题越难,我胜算越大。
我们俩都做了一道很长的除法题。平了。
这让这个日本人坐立不安,因为他的珠算显然训练有素,可在这儿,差点儿败在饭店里吃饭的一个家伙手里。
“ Raios cubicos !”他说,想报仇。立方根啊!他要用算术法求立方根!在算术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难的题了。在他的算盘国度中,这想必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随便写的——我至今还记得:1729.03。他拨开了算盘,满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魔鬼似的忙个不亦乐乎。他挥汗如雨,跟这个立方根干上了。
与此同时,我在那儿闲坐呢。
一个服务员说:“你干吗呢?”
我指了指脑袋。“想呢!”我说。我在纸上写了12。沉吟片刻,我有了得数12.002。
使算盘的这主儿,抹掉脑门子上的汗:“12!”他说。
“啊,不对!”我说,“再加几位数!再加几位数!”我知道,用算术法求立方根,每一位数都比前头那位数更费工。这活儿累得很。
他又埋头干开了,嘟嘟囔囔的。趁这工夫,我又加上了两位数。他最后抬起头来说:“12.0!”
服务员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他们告诉这主儿:“瞅瞅!人家寻思寻思就成,你呢,还得用算盘!人家还多好几位数呢!”
他一败涂地,满面羞赧,溜之乎也。服务员们弹冠相庆。
这顾客怎么打败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碰巧知道1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比12大一丁点儿。多出的1.03,大约只有1/2000。我在微分课上学过,对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1/3。因此,我只需要算出1/1728是多少,再乘以4 ;(即除以3再乘以12)。所以,我的得数就有那么多位数。
几个星期之后,那个人来到了我住的宾馆的鸡尾酒休息室,当时我坐在那儿。他认出我来,就过来了。“告诉我,”他说,“你怎么能那么快算出立方根?”
我就开始解释,说那是一种求近似值的方法,跟误差的百分比有关。“假设你给我的数是28。现在这么想,27的立方根是3……”
他抓起算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哦,是啊。”他说。
我发现,他不懂数字。靠着个算盘,你是不必记住一大堆算术组合的;你只需要学会怎么上上下下拨弄小珠子就成。你不必记住9+7=16;你只需要知道,在你加9的时候,你只要把十位上的珠子推上去、把个位上的珠子拉一个下来。弄起基本算术来,我们慢些。但我们懂数。
另外,近似值方法的整个观念,他是理解不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任何方法都求不出立方根的精确得数,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因此,我跟他解释不清我是怎么求立方根的,也解释不清在他碰巧选了1729.03这个数的时候,我有多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