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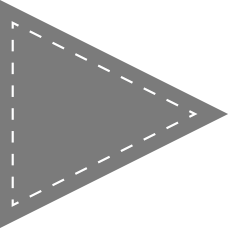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我要我的一块钱!
我要我的一块钱!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常常回老家法洛克维看看。有次我碰巧在家,电话响了: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长途。在那年头,长途电话意味着事情非常重要,何况这长途电话是从远在百万千米之外的加利福尼亚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那边儿那家伙说:“是费曼教授吗,康奈尔大学的?”
“没错儿。”
“我是某某飞行器公司的某某先生。”他说的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大飞机公司;很不幸,我记不得是哪个了。这家伙继续说:“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实验室,研究核动力推进的火箭飞机。这个项目的年度预算是多少多少百万美元……”
我说:“稍等,先生;我不明白,你干吗跟我说这个。”
“让我告诉你呀,”他说,“让我把一切解释清楚。请让我按我的方式说话吧。”他又说了一些话,说有多少人要来这个实验室,多少多少人是这个水平,多少多少博士是那个水平……
“抱歉,先生,”我说,“我想你是找错人了。”
“我不是在跟理查德·费曼说话吗?”
“是的,但你……”
“好不好您让我把话说完嘛,先生;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事。”
“那好吧!”我坐下来,把眼闭上,听他絮叨,讲的都是这个大项目的细节,可他为什么为我提供这些信息,我还是丝毫不明白。
最后,事儿都说完了,他说:“我之所以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您,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出任该实验室的主任。”
“你找的这个人,真合适?”我说,“我是个理论物理教授。我不是个火箭工程师,不是飞机工程师,也不是任何那类东西。”
“我们确信,我们找的人合适。”
“那你是从哪儿知道我名字的?你为什么决定给我打电话?”
“先生,您的大名在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书上。”
“哦,”我说,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在专利书上,待会儿我一定给你讲讲这故事。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但我想在康奈尔大学继续当个教授。”
原来,在战争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那儿有个挺不错的伙计,为政府负责专利局的事儿,他就是史密斯上尉。史密斯给大家都发了一个通知,通知上说,“我们专利局将为您为美国政府贡献的每一个构想申请专利。您关于核能源或者核利用的构想,无论您认为那是人人都知道的,还是人人都不知道的:即请光临我局,将该构想告诉我。”
我在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了史密斯,在我们溜达回技术区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到处发的那个通知,要我们把每一个构想都告诉你,是有点儿发疯啊。”
我们反反复复讨论了这事儿——等我们到了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说:“关于核能源的许许多多构想,我都再清楚不过,我会在这儿待上一整天,统统告诉你。”
“都什么呀?”
“别大惊小怪的!”我说,“举例:核反应堆……在水底下……水进到这儿……蒸汽从另一边出来……刷——这是个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边涌进来……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窍喷出……嗡地一声穿过大气——这是飞机。或者:核反应堆……你让氢气流过这玩意儿……嗵!——这是火箭。或者:核反应堆……用的不是一般的铀,而是在高温下添加了氧化铍的铀,为的是让它更有效……这是个发电厂。构想嘛,有100万个!”我说着,走出了办公室。
什么动静也没有。
大约3个月后,史密斯叫我到那个专利局去,说:“费曼,潜水艇已经让人家弄了去。但另外三个,是你的。”所以,加利福尼亚的那个飞机公司的那些家伙,在筹建实验室的时候,就想火箭推进什么的专家是何许人也,直截了当去看谁申请了这方面的专利!
无论如何,史密斯让我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表示我准备把那三个构想贡献出来,作为政府的专利。这在法律上是冒傻气的:你把这个专利权给了政府,那么你签的那个文件就不是有效的法律文件,除非这其中有某种交易,所以嘛,我签的那份文件上说:“我,理查德·费曼,愿意以一块钱作为回报,将该构想转让给政府……”
我在文件上签了字。
“我那一块钱呢?”
“那不过是个形式嘛,”他说,“我们没有设立这么一项专款,来支付这一块钱啊。”
“肯定有这款子,为这一块钱,字我也签了,”我说,“我要我那一块钱!”
“这也太可笑了。”史密斯抗议。
“不,不可笑,”我说,“这是个法律文件嘛。是你让我签字的,而我这人很老实。如果我在什么东西上签了字,说给我一块钱,那我非得要那一块钱不可。这可不是无理取闹。”
“得得得!”他说,气急败坏了,“我给你这一块钱,我自己掏腰包!”
“成。”
我拿了那一块钱,冒出个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值一块钱的饼干和糖果,那种里头有果酱软糖的巧克力糖果,买了一大堆——那时钱很值钱。
我回到理论物理部,遍施小惠于天下:“我得奖了,各位!吃饼干!我得奖了!一块钱就拿走了我的专利!我的专利为我换了一块钱!”
每个有专利的人——许多人都签过字——都跑去找史密斯:要他们那一块钱!
他开始掏自己的钱包,但很快就明白,自己出血出得要破产!他急疯了,想去设立一项专款,好支付那些一味儿坚持要一块钱的主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