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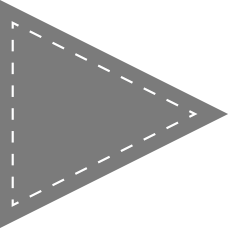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每星期都要到水牛城的一个航空实验室,去搞系列讲座。康奈尔跟这个实验室搞了个协议,其中就包括康奈尔的人在晚上来讲物理。早先有个家伙已经来讲了,但人家不喜欢听,所以物理系就来找我。那时我还是个年轻教授,不好一口拒绝,因此我同意去讲。
他们让我坐一个小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公司只有一架飞机。公司名叫“罗宾逊航空公司”(这就是后来的“莫霍克航空公司”)。我记得我第一次飞往水牛城的时候,罗宾逊先生就是飞行员。把机翼上的冰敲掉,我们就飞走了。
总而言之,每星期四晚上都到水牛城,这主意我不喜欢。大学除了报销费用之外,还另给35美元。我是在“大萧条”中长大的苦孩子,琢磨着把这35美元攒起来。在那年头,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呢。
突然,我有了个主意:我意识到这35美元的目的,是让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让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的方法,是把这钱花了。因此,我决定每次到水牛城的时候,都把这35美元花了,为自己找点儿乐子,我想看看我能不能不虚此行。
在大学之外,我就不怎么老道了。连钱都不知道从哪儿花起,我就让那个在机场接我的出租车司机,给我当向导,在水牛城的大街小巷找乐子。他帮了大忙,我仍然记得他的名字——马库索(Marcuso),开169号车。我星期四晚上一到水牛城机场,总向他请教。
我讲第一堂课之前,问马库索:“哪儿有个有意思的酒吧,就是有好些热闹事儿的那种?”我还以为那些事儿是在酒吧里搞的呢。
“阿里比小舍,”他说,“那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好些人。下了课,我就带你去。”
下课后,马库索来接我,开车送我到阿里比小舍。在路上,我说:“听着,我一定得要点喝的。好的威士忌,叫什么名儿?”
“就要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这么建议。
阿里比小舍是个很雅致的地方,人很多,活动很多。女人穿着毛皮大衣,人人和气,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那儿,要了我的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吧招待很和气,很快就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介绍给我。我给她买了喝的。我喜欢这地方,拿定主意下星期还来。
每星期四晚上,我都来水牛城,169号车把我送去上课,然后到阿里比小舍。我走进这个酒吧,要我的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么搞了几个星期之后,竟到了这么一种程度:我一进来,一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就给我预备停当了。“照您的老规矩,先生”都成了酒吧招待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我把酒端在手,一饮而尽,表示我是条硬汉子,跟我看过的电影里的相似,然后我坐20来分钟,把水喝完。过了一些时候,我连水也不用喝了。
酒吧招待总是留意我旁边的空椅子,他很快找来一个漂亮的女人把椅子填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就在酒吧打烊之前,她们都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那时我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有一次,阿里比小舍快关门了,那天晚上我给她买酒的那个女孩儿,建议我们另找个地方,她认识那儿的许多人。那是另一个房子的二楼,外表看不出楼上还有个酒吧。水牛城的酒吧在两点必须关门,酒吧里的人都被吸引到二楼的这个大厅里,一切继续进行——这是违法的,当然。
我想琢磨出个办法,怎么待在酒吧里看看都搞些什么名堂,而不至于醉倒。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经常光临这个酒吧的家伙,要了一杯牛奶。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毛病:他有胃溃疡,这可怜的伙计。我就有了个主意。
下次我到阿里比小舍,招待说:“照老规矩,先生?”
“不了。可乐。就是普通的可乐。”我说,满脸失意之色。
别的家伙围拢过来,都表示同情:“是啊,三个星期以前,我就戒这马尿了。”一个家伙说。“真得忍着,迪克,真得忍着啊。”另一个家伙说。
大家都为我感到光荣,我现在“戒马尿”了,而且还有勇气来酒吧,面对所有的“诱惑”,仅仅要了个可乐——当然,不喝,也得跟朋友们见面啊。我这么坚持了一个月!我是个真正硬的王八蛋啊。
有一次,我在酒吧的厕所里,那儿有个家伙正在小便。他有那么一点儿醉了,用一种发坏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这张脸。我觉得,我会把你这脸,按扁了。”
我吓得脸发绿。用同样发坏的声音,我回敬他:“别挡着我路,要不我会尿在你身上!”
他说了点儿别的什么,我琢磨着,这就快动手了。我从来没打过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实说,我也害怕受伤。我确实想到了一件事儿:离墙站得远些,因为我琢磨着,要是我挨了打,后头会撞到墙上。
然后,我一只眼咔嚓一下子,感觉好怪——我伤得不厉害——下面的事儿,我知道,我伺候了那龟儿子一重拳,我发现,我连想都不想,就出拳,我觉得这挺怪;这“机器”知道该怎么做。
“这下好了。一比一平,”我说,“还想接茬儿练?”
那小子退后几步,走了。要是那小子跟我一样傻的话,我们会要了对方的命!
我去洗脸,手在哆嗦,牙龈渗出血来——我牙龈本来就不硬——眼也疼。等我安静下来,我回到酒吧,大摇大摆走到招待那儿:“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我说。我琢磨着,这玩意儿能镇静我的神经。
我没注意到,在厕所里让我给修理了一顿的那家伙,在酒吧的另一边儿,正跟另外三个家伙说话呢。转眼之间,这三个家伙——大块头儿的硬汉子——到我坐的这地方来,在我头顶上,朝我倾轧过来。他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说:“挑头儿跟我们朋友打架,什么意思?”
我太傻,浑然不知自己大祸临头;我只知道是非曲直。我干脆也飞扬跋扈起来,反唇相讥:“是谁先挑事儿的,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再来给我添乱!”
他们的威胁没起作用,这事儿让几个大块头着实吃惊,退后几步,走了。
过了一阵子,其中一个家伙又回来了,对我说:“你说对了,克里总这么干。他总是跟人家打架,再让我们给他摆平。”
“你他妈知道我没错儿!”我说,这家伙索性跟我坐一块儿了。
克里和另外两个伙计也过来了,在我斜对面坐了下来,错着两把椅子。克里说了点什么,意思是我的眼不大好看,我说他形状也不堪恭维。
我继续这么嘴硬,因为我琢磨着,一个在酒吧里混的真正的汉子,就得这做派。
局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酒吧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招待说:“伙计们,这不是打架的地方!冷静点儿!”
克里嗤之以鼻:“那好吧;等他出去,我们再跟他算账。”
接下来,一个天才从旁走过。每个领域中都有一流的专家。这伙计走到我这儿,说:“嗨,丹!我不知道你在城里啊!见到你很高兴!”
然后,他对克里说:“我说,克里!来会会我的一个朋友,丹,就这位。我想,你们两个家伙,会投缘的。干吗不握握手啊?”
我们握了手。克里说:“啊,幸会。”
然后,这位天才俯在我身上,凑在我耳朵边儿,悄悄说:“快快开溜!”
“可他们说要……”
“走吧你!”他说。
我拿了外套,匆匆出去。我顺着这房子的墙根儿往前走,以免他们找到我。没人出来,我去了我的旅馆。碰巧课在那天晚上讲完了,因此我再也没去阿里比小舍,起码有几年没去。
(10年之后,我确实又去了阿里比小舍,已经面目全非了。它不像以前那样优雅而光洁,破破烂烂的;里头的人,衣衫褴褛。我跟招待聊,不是原来那位,给他讲过去的事儿。“哦对!”他说。“以前哪,赌赛马的和他们的马子,都在这酒吧逍遥。”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这儿有那么多和和气气、相貌优雅的人,为什么电话响个不停。)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黑眼圈儿需要经过几小时才能充分形成。那天,等我回到伊萨卡的时候,我有些东西要交给系主任办公室。一个哲学教授看到了我的黑眼圈儿,咋咋呼呼的,“哦,费曼先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撞到门上才撞成那样儿的!”
“干吗撞门,”我说,“我在水牛城的酒吧厕所里,跟人干了一架,搞成这样。”
“哈哈哈!”他大笑起来。
接下来,上我的正常课的时候,麻烦了。我走进讲座大厅,低着头,研究我的备课本。准备开讲的时候,我昂然直视;以前的开场白,总是那一套——但这次,口气凶悍:“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