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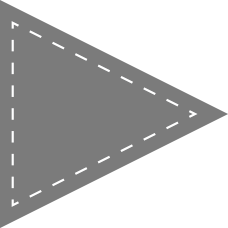 山姆大叔不要你了
山姆大叔不要你了
战争之后,军队千方百计让大伙儿去充当在德国的占领军。在那之前,军队还考虑大家身体之外的原因而准予延缓服役(我可以延缓服役,因为我为原子弹工作过),可是现在他们翻云覆雨,要每个人都首先接受体检。
那个夏天,我在纽约州斯卡奈塔第市(Schenectady)的“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为汉斯·贝特工作。我记得,我不得不走老远的路——我想是到奥尔巴尼(Albany)
 ——去体检。
——去体检。
我到了征兵的那地方,得填许多表格,然后我到各个不同的体检棚子去。他们在一个棚子里查视力,在另一个棚子里查听力,又在别的一个棚子里采血样,等等。
说着说着,最后你来到了第十三号棚子:精神病医生的棚子。你等在那儿,坐在长条椅上。我在那儿等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干什么。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后边都坐着个精神病医生。“犯人”呢,只穿着裤衩儿,坐在精神病医生对面,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时,有许多讲精神病医生的电影。比方说,有一部《爱德华大夫》( Spellbound ),里头有个女的,曾经是个伟大的钢琴家,现在呢,双手五指张开,动弹不得,家人就找了个精神病医生来帮她的忙,那个精神病医生和她一块儿到了楼上,进了一个房间,你看到他随手把门关上了,楼下呢,一家人在吵吵会出什么事儿,然后,她从那房间里出来了,手还是那样怪可怕地张着,颇为戏剧性地走下楼梯,走到钢琴那儿,坐下,把手举到琴键上,突然之间——可叮当叮,当、当、当——她又能弹了。嚯,我受不了这些聊斋故事,我拿得准,精神病医生都是骗子,我可不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轮到我和那个精神病医生谈话的时候,我就这心态。
我靠桌子坐下来,那个精神病医生开始浏览我的文件。“哈喽,迪克!”他用一种挺愉快的语调说,“哪儿工作呀?”
我在想:“他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的昵称,也能是他乱喊的?”我呢,冷冷说道:“斯卡奈塔第。”
“哪个单位的呀,迪克?”精神病医生说,又挂着三分笑。
“通用电器。”
“喜欢你的工作吗,迪克?”他说,脸上仍然是腻味人的笑容。
“一般般吧。”我就是不想跟他套词儿。
三个可爱的问题,接着,第四个问题,彻底变味儿了。“你认为大家都在谈论你吗?”他问,声调儿低沉,严肃。
这我倒来了精神,说:“可不是咋的!我回家的时候,我妈经常告诉我,她是怎么怎么跟她的朋友们讲我的事儿来着。”他不听我解释,却在我的文件上写下了什么东西。
然后,又来了,声调儿低沉,严肃,他说:“你认为大家都盯着你吗?”
我刚要说不认为,他却说:“比方说,你认为那些坐在那边儿长条椅上的小伙子,现在都在盯着你吗?”
刚才我坐着等和这个精神病医生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长条椅上坐着大约12个家伙在等这仨精神病医生检查,他们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的嘛。我就用12除以3,每个医生检查4个,可我保守着点儿,所以我说:“是啊,或许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在看着我们。”
他说:“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他自己却懒得看看!
于是我就转过头去,果然,两个家伙在看。所以我就指着他们,说:“是啊——那个家伙,还有那边儿那个家伙,在看我们呢。”当我转过头的时候,那个样子拿手指着人家,其他人当然就开始看我们,所以我说:“现在,他,那边儿还有两个——现在椅子上的人都在看啊。”他仍然不抬头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他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然后,他说:“你在你脑袋里听到有人说话吗?”
“很少。”我正要告诉他,有那么两次,确有这样的事儿,可他说:“你自言自语吗?”
“是啊,有的时候,我在刮脸的时候,或者在想问题的时候;偶尔吧。”他又写了更多的东西。
“我知道你妻子去世了——你和她说话吗?”
这问题真把我惹恼了,但我耐住性子,说:“有的时候吧,我到山上去的时候,就想她。”
他又写。然后,他问:“你有没有家庭成员住在精神病院?”
“敢情,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把那个叫作疯人院?”他说,怫然不悦,“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叫作精神病院?”
“我觉得那是同一个玩意儿。”
“那你认为精神错乱是怎么回事?”他生气地说。
“那是人类的一种怪异的疾病。”我说得很真诚。
“它比盲肠炎也没什么怪异的!”他反驳。
“我不这么认为。就盲肠炎而言,我们理解它的起因,理解得好得多,理解它的机理是怎么回事儿。可说到精神错乱,事情就复杂得多,也神秘得多。”我不必在这里把这整个的辩论讲一遍;我的意思是,精神错乱在心理学上是怪异的,他却以为我是说,社会认为精神错乱是怪异的。
直到那时,尽管我对那个精神病医生一直不友好,但我说的一切,还是认真的。但是,当他要我把两只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耍花招了。这个花招,是我在排队“抽血”的时候,有个家伙告诉我的。我琢磨着,没人能得着个机会玩这个把戏。我呢,索性破罐子破摔,我准备玩儿它一玩儿。于是,我就把两只手伸出来,一只掌心向上,一只掌心朝下。
那个精神病医生没注意到这个,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两只手都翻过来了。掌心向上的那只,变成了掌心朝下;掌心朝下的那只,变成了掌心向上。他还是没注意到,因为他一直都在专注地看着一只手,看它是不是发抖。因此,这把戏没玩儿成。
最后,问题都问完了,他又变得友好了。他有兴致,说:“我看到你有博士学位,迪克。你是在哪儿上的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是在哪儿上的学?”
“耶鲁和伦敦。你学的是什么,迪克?”
“物理。你学的是什么?”
“医学。”
“这是医学?”
“怎么,是啊。那你以为它是什么?你到那边去坐了,等几分钟。”
我于是又坐在长条椅上,在那儿等着的一个家伙,凑过来说:“嚯!你在那儿磨蹭了25分钟!别的家伙也就5分钟!”
“是啊。”
“嗨,”他说,“你知道怎么涮那些精神病医生吗?你只需要咬指甲就可以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像那样咬你的指甲?”
“哦,”他说,“我真想参军呢!”
“你想涮那几个精神病医生吗?”我说,“你只要把你刚才说的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阵子,有人把我招呼到一个不同的桌子那儿去见另外一个精神病医生。头一个精神病医生很年轻,天真无邪的样子;这一位,头发灰白,神态不凡——显然是老资格的精神病医生。我琢磨着,这一切该到了摆平的时候了,但无论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是不打算待见他们的。
这第二个精神病医生看了我的文件,满脸绽笑,说:“哈喽,迪克。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你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
“没错儿。”
“以前那儿有一所男子中学,对不对?”
“对。”
“那学校里有很多建筑?”
“只有几座。”
三个问题——一个技巧——下个问题,完全变味儿了。“你说,你在你脑袋里听到人说话。请说说看。”
“这种事儿,不常见。在我很注意一个说话带外国味儿的人说话的时候,到我入睡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声音,听得很清楚。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我听见一个老教授法拉塔(Vallarta)说,‘则个则个电场啊。’另一次是在芝加哥,在战争期间,那时特勒教授在跟我解释那个炸弹是怎么工作的。因为我对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感兴趣,我就纳闷啊,我听这些带外国口音的声音,怎么能听得这么真切,可我模仿他们却模仿得不那么好……人人都会有这样的事儿吗?”
这个精神病医生把手捂在脸上,在他的指头缝儿之间,我看到了那么一丝笑容(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呢,这个精神病医生检查了别的什么东西。“你说你和你去世的妻子说话。你对她说什么?”
我火了,我琢磨着,我说什么,关你个屁事儿,我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没碍着你什么事儿!”
一来一往地互相说了几句刻薄话之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现象吗?”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超正常’现象。”
“什么?你,一个博士,学物理的,不知道什么是超正常现象?”
“不知道。”
“那就是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爵士
 和他的学派所相信的那个东西嘛。”
和他的学派所相信的那个东西嘛。”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这事儿,我知道。“你说的是超自然现象?”
“你愿意那么叫它,就那么叫呗。”
“那好,我愿意那么叫它。”
“你相信心灵感应吗?”
“不相信。你信吗?”
“我嘛,我总是宽容而无偏见。”
“什么?你,一个精神病医生,总是宽容而无偏见?哈!”就这么彼此较劲,折腾了好一阵子。
然后,到将近结束的时候,“你觉得生命值多少?”
“64。”
“为什么说是‘64’?”
“你要我说出个数来,为生命定价,又有什么道理?”
“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说‘64’,而不是‘73’,比方说?”
“如果我说了‘73’,你还不是问同样的问题!”
这个精神病医生用三个友好的问题收场,别的精神病医生也是这么做的,把我的文件递给我,我就到了下个棚子去。
在我排队等着的时候,我在看文件,上面写着到目前为止我接受的所有检查的结论。完全是为了恶作剧,我把我的文件给我后边的那家伙看,我用一种愚蠢的声调儿问他:“嗨!你的‘精神病科’得了什么?哦!你得了个‘N’。我别的东西都得‘N’,但‘精神病科’得了个‘D’。那什么意思啊?”我知道那什么意思:“N”是正常,“D”是有缺陷。
那家伙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挺不错的。那说明不了什么。别为那个操心!”然后,他走到这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吓坏了:这是个疯子啊!
我开始看那几个精神病医生写了字的文件,看起来情况颇为严重!第一个家伙写道:
以为人们谈论他。
以为别人盯他。
睡前幻听。
自言自语。
与去世的妻子谈话。
姨母在精神病院。
眼神非常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我说“这是医学?”的时候,眼神确实怪异。)
第二个精神病医生显然更重要,因为他字如蟹腿,更难辨认。他写了些“确定有睡前幻听现象”之类的话。(“睡前”这个词儿,意思是你正在沉沉入睡的时候,你有幻听。)
他写了许多听起来很专业的东西,看起来颇为糟糕。我琢磨着,我一定得想想办法,得跟军队澄清这些事儿。
到整个体检结束的时候,有个军官来决定你是参军还是淘汰。比方说,如果你听觉有毛病,他来决定那是不是真严重到不能参军的程度。因为军队是不遗余力地要扩充兵员,这个军官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像根钉子似的不肯通融。比方说,我前边的那伙计,脖子后头有两块儿骨头凸出来——脊椎移位什么的——这军官不得不从桌子后头站起来,拿手去摸那两块儿骨头——他得搞清楚那是不是真的!
我琢磨着,这是我澄清误解的地方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文件递给军官,正要跟他把一切解释清楚,可这军官,头也不抬。他一眼就看到了“精神病科”后面的那个“D”,伸手就去摸“拒收”的大印,连问题都不问,什么也不说;利利索索地在我的文件上盖了“拒收”的戳子,然后把我那4-F(征兵体检不合格)的文件递给我,眼却还是盯着桌子。
所以呢,我就出去了,上了去斯卡奈塔第的公共汽车。我坐着车,琢磨刚才发生的这些荒唐事儿,不禁失笑——都笑出声了——我对自己说:“我的老天爷!要是他们看见我现在这副样子,那就更确信无疑了!”
等我最后到了斯卡奈塔第的时候,就去看汉斯·贝特。他在写字台后头坐着,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样,迪克,通过了?”
我拉长个脸,慢慢地摇摇头:“没通过。”
他突然很紧张,以为他们发现我有什么重病,他就以关切的口吻问我:“怎么回事儿,迪克?”
我拿手支着我脑门子。
他说:“没那么严重吧!”
“就那么严重!”
他叫起来:“没……那……么……严……重!”他笑得山响,通用电器公司的屋顶差点儿给震塌下来。
我把这故事讲给许多人听,人人都笑,但有几个例外的。
我回纽约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到机场接我,坐车回家的路上,我把这故事整个讲给他们听了。末了,我妈妈说:“嗨哟,这可该怎么办啊,迈尔(Mel)?”
我爸爸说:“你别犯蠢,露西尔(Lucille)。简直是胡闹嘛!”
事儿就这样了,可后来我妹妹告诉我,等我们到家,我不在场的时候,我爸爸说:“听着,露西尔,你不该当着他的面儿说那些个。现在,这可该怎么办?”
但到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冷静下来了,她说:“你别犯蠢,迈尔!”
还有一个人,这故事让他闹心。事情是在“物理学会”的会议饭桌上,斯莱特(Slater)教授,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教授,说:“嗨,费曼!给我们讲讲我听过的那个征兵的故事。”
我为全体物理学家们讲了整个故事——除了斯莱特,别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从头到尾一直笑个不停,但是故事完了,一个家伙说:“呵,那个精神病医生,或许还是有些想法的。”
我率尔说道:“你干哪行的,先生?”当然,这是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参加专业会议的物理学家。但一个物理学家会冒出这么一句,我很惊讶。
他说:“那个,呃,我本来实在不应该坐在这儿,我是受我兄弟的邀请,到这儿做客的,他是个物理学家。鄙人呢,精神病医生。”我和尚面前骂秃子,把他给骂出来了!
过了一阵子,我开始担心。他们会说,这里的这个家伙,在战争期间,一直免服兵役,因为他在造原子弹。征兵委员会一直接到信,说他是个重要人物,可他在“精神病科”得了个“D”——结果他是个疯子!显然,他不是个疯子;他是变着法儿地让我们相信他是个疯子——我们得把他抓回来!
形势看来对我不利啊,因此我必须想个出路。几天之后,我琢磨出了个解决办法。我给征兵委员会写了封信,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先生们:
我认为我不应该去当兵,因为我在给科学学生教书。我们国家的福祉,部分地依赖于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兵力强不强。然而,根据我的体检报告,也就是说,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看,我是不合格的,各位或许会决定免除我的兵役。我觉得,那份报告不应该得到任何重视,因为我认为它满篇都是低级的错误。
我之所以敦请诸位注意这个错误,乃是因为我脑子太疯了,疯得都不想占这个错误的便宜。
理查德·费曼 谨上
结果:“缓服兵役。征兵体检不合格。健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