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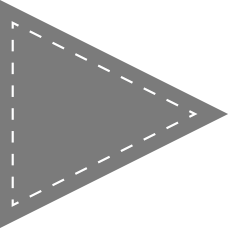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撬锁贼碰到了撬锁贼
撬锁贼碰到了撬锁贼
我跟一个名叫列奥·拉法特里(Leo Lavatelli)的家伙学会了开锁。我发现,一般的旋转弹簧锁——如耶鲁锁——容易开。你把螺丝刀插在锁眼儿里(你得贴着一边往里插,好让锁眼儿留出空隙),试着转动。这么转,是转不动的,因为里头有一些栓子,一定得把栓子抬到一定的高度(用钥匙)。因为锁造得不那么地道,因此经常只有一个栓子在吃力,其他栓子不起作用。现在,如果你把一段铁丝——或许是一个曲别针,头上有个小凸起的最好——插进去,然后再在锁里前后哆嗦着,你最后就能把那个吃大部分力的栓子,撬到合适的高度。锁就松动了,但只松动了一点儿,第一根栓子在上面待着,卡在边上。现在,大部分的力,是第二根栓子吃着,你再花几分钟重复刚才这个随意的过程,直到把全部的栓子都拉起来。
经常发生的事儿,是螺丝刀打滑,你听到吱啦、吱啦、吱啦,这让你急得发疯。在钥匙拔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小弹簧就把栓子推到下边了;把螺丝刀一拔出来,你就听得见栓子啪啦一下掉下去了。(有时你故意把螺丝刀拔出来,为的是看看你插的地方对不对——比方说,你可能插错地方了。)这过程有点儿像西西弗斯(Sisyphus)
 :你总是从山顶上滚下来。
:你总是从山顶上滚下来。
过程是简单的,熟才能生巧。你得学会怎么紧紧把东西压住——压得足够紧,栓子才会待在那儿,但也不能太紧,否则栓子就不往上走了。大家经常把自己锁了起来,把锁开开不那么难,而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
在我们开始在洛斯阿拉莫斯搞原子弹项目的时候,一切都是匆匆上马,实际上没准备好。这项目的全部机密——所有和原子弹有关的东西——都放在文件柜里。要是文件柜锁了的话,也是用的挂锁,这种锁或许只有三个栓子:开这种锁,跟掰开饼似的容易。
为了加强保密工作,车间为每个文件柜加了一根挺长的铁棍儿,把抽屉把手串起来,再用挂锁绊住铁棍儿。
有个家伙对我说:“瞧车间弄出的这个新生事物——现在你能把柜子打开吗?”
我看了看柜子背面,看到抽屉底不结实。每个抽屉上都有了狭缝,狭缝里有一根铁棍,铁棍绊着一个可以滑动的板(它在抽屉里边把文件拢住)。我从后边把手伸进去,把那个板往后推,然后从狭缝往外扯文件。“瞧!”我说,“连锁都不用撬。”
在洛斯阿拉莫斯,大家都很合作,我们觉得指出应该得到改善的事儿,是我们的责任。我一直在发牢骚,说文件不安全,可别人都认为那很安全,因为有钢棍儿,有挂锁,可那顶个什么用啊。
为了证明那些锁不顶用,每当我需要一个人的报告而他又不在旁边的话,我就径直到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文件柜,把东西拿走。我把事情做完了,就把东西还给那个家伙:“谢谢你的报告。”
“你从哪儿弄的?”
“从你文件柜里拿的。”
“但我把它锁了啊!”
“我知道你锁了。锁不顶用。”
终于来了一些文件柜,装了“莫斯勒锁业公司”造的密码锁。柜子上有三个抽屉。把最上边的抽屉拉开,挂钩就开了,另外两个抽屉也就跟着开了。最上边的那个抽屉是这么开的:按照密码,转动密码轮,往左,往右,再往左,然后往右转到10,这就把里边的一个闩挑开了。整个文件柜是这么关的:首先关上底下的两个抽屉,然后关最上边的那个抽屉,转动密码轮离开10,这就把那个闩扣上了。
自然,这种新文件柜立刻成了我的挑战。我喜欢难题。一个家伙搞出个东西,来为难另一个家伙;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必须首先理解这种锁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就把我办公室的那个拆了。它工作的道理是这样的:一根杆上有三个圆盘,一个挨着一个,每一个圆盘都在不同的地方有凹槽。这个想法,是把三个凹槽排成一条线,这样,当你把密码轮转到10的时候,一点点摩擦力会把那个闩带进由那三个圆盘组成的狭缝里。
现在,转动三个圆盘,就有一个栓子从密码轮的后面伸出来,还有一个同样半径的栓子是从第一个圆盘上竖起来的。把密码轮转一圈,你就会把第一个圆盘带起来。
第一个圆盘背后有一个栓子,其半径和第二个圆盘前边的那个栓子的半径一样,因此,等到你把密码轮扭到第二圈的时候,你也把第二个圆盘带起来了。
继续转动密码轮,第二个圆盘背后的栓子,会连动第三个圆盘前面的那个栓子,现在你就把第三个圆盘弄到了跟密码轮的第一个数字相符合的合适位置上了。
现在,你必须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密码轮一整圈,以便从另一边连动第二个圆盘,然后继续按照密码轮的第二个数字转动。以便把第二个圆盘弄到合适的位置上。
你再次反转方向,把第一个圆盘弄到合适的位置上,现在,三个凹槽在一条直线上,把密码轮转到10,柜子开了。
我折腾了一番,没有进展。我买了两本开锁的书,都是大同小异的。书开头讲关于这位开锁匠非凡业绩的几个故事,比方说,一个女人把自己锁在了藏肉的冰箱里,快要冻死了,这位开锁的,把自己倒挂在房梁上,两分钟就把它打开了。或者海底下有一些昂贵的皮毛和金条,他潜到水下,把箱子打开了。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么开保险柜。书里有各种各样的傻里傻气的东西,比方说“把某个日子当密码试试,或许是个好主意,因为许多人喜欢把日期当密码”,或者“考虑一下保险柜主人的心理,他可能把什么数字当作密码”,以及“秘书常常担心把保险柜的密码忘了,所以她或许把密码写在如下这些地方——写字台的边上、通讯录里……”等等。
怎么打开一般的保险柜,这些书确实告诉了我某些有意思的东西,而且也很容易理解。一般的保险柜,有一个多余的把手,因此,如果在你转动密码轮的时候,往下压那个把手,事情就不公平了(对锁不公平)。把手上的力,试图把闩推到凹槽里(并没有排成一条线),而一个圆盘受的力会比另外一个多。当那个圆盘上凹槽走到闩的下面的时候,会有一声轻微的啪啦,用听诊器是可以听到的,或者你手上可以感觉到摩擦力增加了一点儿(要感到摩擦力,你不必用砂纸来擦你的指尖),你知道,“找到一个数码了”!
你不知道那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个数码。但是,你很可能猜得出是哪一个,只要你看看你需要反转密码轮多少次才又能听到那声啪啦就行了。如果不需要转一圈儿,那就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儿,那就是第二个圆盘(你必须根据栓子的粗细做相应的矫正)。
这一有用的手法,只能对付有把手的一般的保险柜,所以我又没辙了。
我在文件柜上把各种各样的辅助手段都试过了,诸如不打开顶上那个抽屉,把前面的螺丝钉卸掉一个,然后插进一段晒衣服用的铁丝,想把下面的两个抽屉的插销弄开。
我试过快速转动密码轮,然后转到10,这样会增加一点儿摩擦力,我指望这会使一个圆盘以某种方式停住。我把什么东西都试过了。我都急眼了。
我还进行了不少系统的研究。比方说,一种典型的密码组合是69-32-21。在你想把保险柜打开的时候,密码允许多大的误差?假如密码是69,那么68也管用吗?67也管用吗?就我们的这种特别的锁而言,答案是:68和67都管用,但66不管用。在两个方向上,允许的误差都是2。这意味着,每五个数码,你就得试其中的一个,所以你可以试0、5、10、15,等等。在一个有100个刻度的密码轮上,就有20个这样的数码,这样就有8000种可能的数码组合;如果你想试遍全部数码的话,那么就有100万种可能的数码组合。
现在的问题是,试完8000种数码组合,要花我多长时间?假定我们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前两个正确的数码组合,比方说,是69-32。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得到的数码组合是70-30。我可以试20种可能的第三个数码组合,而不必每次都确定前两个数码组合。现在,假定只有第三个数码组合是对的。在第三个圆盘上把20个数码试完了之后,我就稍微转动一下第二个圆盘,然后在第三个圆盘上试另外20个数码。
我一直在我自己的保险柜上练习,所以我能以我最快的速度进行这个过程,而且脑子不乱,不会忘记该试的数码到了哪一个,从而把前一个数码搞乱。就像练习变戏法似的,我在试数码的时候,绝对有节奏,不到半小时,就能试遍后面的400个可能的数码组合。这意味着我最多只需要8小时开一个保险柜——平均4小时开一个。
洛斯阿拉莫斯还有另一个家伙,叫斯塔雷(Staley),也对锁感兴趣。我们时不时地谈开锁的事儿,但没谈出个什么。等我琢磨出怎么在平均4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时候,我想向斯塔雷显示一番这是怎么弄的,所以我走进计算部的一个家伙的办公室,问道:“用一下你的保险柜,介意吗?我想让斯塔雷长点儿见识。”
与此同时,计算部的几个家伙过来看热闹,一个家伙说:“嗨,各位;费曼想让斯塔雷见识见识怎么开保险柜,哈、哈、哈!”我本来没真的打算开保险柜;我只是想向斯塔雷显示怎么快速地试后两个数码,却又不会忘记试到哪儿了,以至于不得不再确定第一个数码。
演示开始。“让我们假定第一个数码是40,我们把15作为第二数字来试。我们往前和往后转到刻度10;再往后多转5个刻度,再往前转到刻度10;如此这般。现在,我们已经试过了可能的第三个数码。现在,我们把20当作第二个数码来试;我们往后转到刻度10,往前转到刻度10;再往后多转5个刻度,往前转到刻度10;往后再转5个刻度,往前,咔嚓!”我下巴都掉下来了:第一和第二个数码碰巧对了!
没人看到我什么表情,因为我背对着他们。斯塔雷看来吃惊不小,但我们俩都很快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把顶上的抽屉拉了出来,说:“搞定了!”
斯塔雷说:“我看明白了你什么意思;这办法非常棒。”——我们俩迈步出门。大家都傻了眼。那纯粹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但我确实名声大噪,我会开保险柜。
花了我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才有这造诣。(当然,我也在搞原子弹!)我觉得我已经把保险柜打败了,这意思是说,如果确实真出了麻烦——如果有人失踪了或者死了,没其他人知道密码,但我们急着要文件柜里的东西——我是能把它打开的。在读过了开锁匠书里的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之后,我觉得我这一次堪称壮举。
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没什么娱乐,我们得为自己找点儿乐子,因此摆弄我文件柜上的莫斯勒锁,成了我的一项娱乐活动。有一天,我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当锁开着的时候,抽屉也拉出来了,密码轮停在刻度10(人在打开文件柜往外拿文件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锁闩还扣着呢。锁闩还扣着,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锁闩仍然在排成一条直线的三个圆盘形成的凹槽里啊。哇噻!
现在,假如我把密码轮稍微转离刻度10,锁闩就从凹槽里抬起来了;如果我们立刻返回刻度10,锁闩就又掉进了凹槽,因为我还没把凹槽搞乱。如果我每次转5格转动密码轮离开刻度10,那么到某一个刻度,即使我再返回刻度10,锁闩也不会掉在凹槽里了:凹槽已经搞乱了。紧前面那个数,即仍然允许锁闩掉到凹槽的那个数,就是密码组合的最后一组数!
我意识到,我可以依照此法发现第二组数:一旦我知道了最后一组数,我就可以朝另一个方向,还是每次转5格,一点一点地转第二个圆盘,直转到锁闩掉下去,而紧前面那个数就是第二组数码。
如果我很有耐心,我会把三组数都这样搞出来,但用那种很细致的办法弄到第一组数码组合需要的劳动,要比在文件柜关着的时候并且在你已经知道后两组数码的前提下去试那20个可能的第一组数码所需要的劳动多得多。
我练啊练啊,练到我连密码轮都不怎么看,就能从开着的文件柜上搞到后两组数码。然后,等我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的时候,我就倚着他打开的文件柜,就跟人在谈话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摆弄钥匙似的。我不过是在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扭密码轮而已。有时我用手指头去摸锁闩,所以我也不需要看看它是不是从凹槽里出来了。用这种办法,我搞来了好些文件柜的后两组数码。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把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纸上,藏在我的文件柜里。每次我要看那张纸的时候,都要把锁拆开——我觉得把它藏在这地方,是安全的。
过了一阵子,我的名声传扬开了,因为下面这种事儿是会发生的。有人会说:“费曼,克里斯蒂出城了,我们需要他保险柜里的一份文件——你可以打开吗?”
如果我知道我没有那个保险柜的后两组数码,我就敷衍道:“抱歉,可我眼下腾不出身啊;我得把这个工作做完。”如果我有那两组数,我就说:“好的,可我得去找工具。”我不需要什么工具,但我要回我办公室,把我的文件柜打开,把那张纸拿出来:“克里斯蒂——35,60。”然后,我带着把螺丝刀,到克里斯蒂办公室里,顺手把门带上。很明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我是怎么弄的!
我一个人待在那儿,几分钟就把保险柜打开了。我要干的,仅仅是最多需要20分钟搞到第一组数码,然后坐下来看杂志什么的。让人看出这事儿很容易办,那又何必;有人会琢磨出这其中必定有窍门!过一阵子,我开了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我能把保险柜打开,每次都要摸索。我能把锁打开,是碰巧了,让他们那样想好了,那都是因为和斯塔雷的那次偶然的事儿。没人琢磨出我把他们保险柜的后两组数码搞了去,尽管我一直这么搞,或许正是因为我一直这么搞,他们才不知道,就像一个靠玩扑克骗钱的骗子一样,走哪儿都带着一副扑克。
我经常到橡树岭检查铀工厂的保密工作。一切都是匆匆上马,因为那是战时。有一次,我非得在周末去不可。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那个家伙的办公室里——一个将军,一个头儿,或者某个公司的副总裁,几个大人物什么的,还有我。我们聚在那儿讨论一份报告,这报告在这家伙的保险柜里——一个机密保险柜——他那时突然意识到他不知道密码。知道密码的,只有他秘书一个人,于是他给她家里打电话,结果她到山上野餐去了。
正当这么折腾着的时候,我说:“要是我来摆弄一下这保险柜,你不介意吧?”
“哈、哈、哈——一点也不介意!”我就走到保险柜那儿,开始捣鼓。
他们开始商量,从哪儿弄辆车去找找那个秘书。那家伙越来越尴尬,因为他让大家在这儿空等,他是这么一头蠢驴,连自己的保险柜都打不开。在场的每个人都烦了,都跟他急眼,正在此时,啪啦!——保险柜开了。
在10分钟之内,我就把这个装着和工厂有关的全部机密文件的保险柜给打开了。他们目瞪口呆。这保险柜显然不怎么保险啊。这可是沉重的打击啊:所有这些“只可阅读、不可带走”的东西,这些绝密文件,锁在这么一个美妙的机密柜里,而这个家伙,10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我当然能把这个保险柜打开,因为我搞走人家保险柜的后两组密码,都成了习惯。我在前一个月来橡树岭的时候,来过这个办公室,其时这个保险柜开着呢,我呢,就漫不经心地把它的两组数码弄出来了——我总在操演我的这个嗜好。尽管我没把数码写下来,但我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第一次,我试了40-15,然后试了15-40,但这都不管用。然后我试了10-45,和可能的第一组数码一起试,于是就打开了。
在另一个周末,还是在橡树岭,发生了一件相似的事儿。我写好了一份报告,这报告必须让一个上校认可,而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里。这里的每个人都把文件放在像洛斯阿拉莫斯那样的文件柜里,但他是个上校啊,所以他的柜子花花儿得多:两扇门,装了两个把手,把手把四个2厘米粗的钢制锁闩从构架上拉了回来。大黄铜门晃开了,他把我的报告拿出来读。
我还没有机会见识一下这么好的保险柜呢。我对他说:“在你读报告的时候,我看看你的保险柜,介意吗?”
“随你看。”他说,确信我做不了什么事。我看了看一扇厚重的黄铜门的背后,发现那个密码轮连着一个小锁,这小锁就跟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文件柜上的那个小部件一模一样。同一个公司,同样的小闩子,不同的仅仅是:这里的锁闩下来的时候,保险柜上的大把手能把一些钢棍拨到侧路上,而且借助一串杠杆,你可以把那些2厘米粗的钢棍拉回原处。这整个的杠杆系统,依靠的仍然是把我的文件柜锁住的那样一些小闩子。
仅仅是出于职业完美主义的原因,为了确定这个保险柜实在没什么两样,我把它的两组密码弄到手了,方法和我从其他文件柜上搞密码一样。
与此同时,他在那里读报告呢。读完了,他说:“行,不错。”他把文件放在保险柜里,抓着那两大把手,把两扇大黄铜门晃上。关门的声音,铿然悦耳,但我知道那全是心理战术,因为它除了是同样的破锁之外,什么也不是。
我禁不住想刺挠刺挠他(我对军队里的家伙总有看法,瞧这身神气活现的军装),我就说:“从你关这保险柜的派头来看,我猜,你觉得东西放那儿,挺安全。”
“那还用说。”
“你觉得东西放那儿挺安全,唯一的理由,是因为老百姓把那玩意儿叫作‘保险’柜。”(我在这节骨眼儿上用了“老百姓”这词儿,听起来好像他已经被老百姓愚弄了似的。)
他非常恼火。“什么意思啊,你——它不保险?”
“开锁的好手,30分钟就弄开它。”
“你能30分钟把它弄开吗?”
“我说的是开锁好手嘛。我来开,大约需要45分钟。”
“也罢!”他说,“俺老婆在家等俺吃晚饭来着,可俺打算待在这儿看看热闹。你给我坐那儿,弄那倒霉玩意儿弄上45分钟,要是弄不开的话……”他坐在他的大皮椅子上,把脚翘在写字台上,看起报纸来。
我信心十足,拉了把椅子,坐在保险柜前头。我开始随机转动密码轮儿,这是故作姿态而已。
约莫5分钟之后,当你坐着等的时候,5分钟显得好长,他有点儿不耐烦了:“我说,进展如何?”
“对付这么个东西,开就彻底开了,否则就是开不了。”
我琢磨着,再过一两分钟,也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就真用心地开它,两分钟之后,啪啦——开了。
上校的下巴掉下来了,眼珠子爆出来了。
“上校,”我说,语气严肃,“让我跟你说点儿这些锁的事儿。在保险柜的门敞着的时候,或者顶上的那个抽屉拉开的时候,把密码弄到手,易如反掌。就在你读报告的时候,我正弄这事儿呢,仅仅是为了表明这种危险。你应该坚决要求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把抽屉锁上,因为抽屉敞着,这柜子真是不堪一击呀。”
“敢情!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事儿好玩哈!”从此,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下次我到橡树岭的时候,那儿的秘书,那儿的人,知道我是何许人也,老对我说:“别打这儿过!别打这儿过!”
原来,上校已经给工厂的每个人发了通知,通知说:“在费曼先生上次来访期间,在任何时间,他是否进过你的办公室,是否靠近过你的办公室,或者是否穿过你的办公室?”有些人说是,另一些说否。那些说是的,又得到了个通知:“请更改你保险柜的密码。”
那就是他的解决方案:我成了危险。因此,由于我,他们全体都不得不更改密码。更改密码,再记住新密码,这事儿真是可恼啊,因此他们全体都跟我急了眼了,不想让我靠近他们:他们或许还得再次更换密码。当然,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抽屉仍然敞着!洛斯阿拉莫斯有个图书馆,藏着我们工作的全部文件:那里有一个坚固的水泥房间,有一扇漂亮的大门,门上有个能转的轮子——跟银行金库似的。在战争期间,我曾想凑近看看。我认识在那儿当图书馆员的那个女孩儿,我求她让我玩玩那门。我对这门着了迷: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锁!我发现,我要想进去,用搞到两组密码的那老办法,不灵了。在门敞着的时候,我一扭把手,实际上是把锁锁上了,锁头伸出来了,没办法再把门关上,偏得等那女孩儿来再打开锁才成。我就此罢手,不再玩那锁了。我没工夫琢磨这锁是怎么工作的;它大大超过了我的本事。
在战后的那个夏天,我有一些文件要写,有些工作要扫尾,所以我从康奈尔大学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那年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我工作到中间,必得引用我以前写的一个文件,但我记不得了。那文件就在那个图书馆里。
我到那儿去找那个文件,那儿有个当兵的,走来走去的,还有枪呢。那是个星期六。在战后,这图书馆星期六不开门。
于是我记起了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弗里德里克·德·霍夫曼(Frederic de Ho man)做的事儿。他是“解密部”的。战争之后,军队考虑着把某些文件解密,他不得不来来回回跑那个图书馆——看看这个文件,看看那个文件,检查这个,检查那个——简直快要发疯!他于是就把每一份文件——关于原子弹的全部文件——都拷贝了,放在他办公室里的九个文件柜里。
我到了他办公室,灯亮着呢。看来那儿有人——或许是他的秘书——刚出去几分钟,于是我就等。我一边等,一边开始捣鼓一个文件柜上的密码轮。(插一句,我不知道德·霍夫曼文件柜后两组密码。这些文件柜是在战后、在我离开后送来的。)
我开始玩其中的一个密码轮儿,开始想那几本开锁的书。我心里想:“我从来没把书里写的那些招数放在眼里,因此我也没试过,那就让咱们试试,照书上的点子,看咱能不能打开霍夫曼的保险柜。”
第一招,秘书:她担心把密码忘了,就把密码写在什么地方。我开始踅摸书里提到的几个地方。写字台抽屉锁着,但那锁是列奥·拉法特里教我开的那种普通锁——啪地一声就开了!我看了抽屉边儿:什么没有。
然后,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了一张纸,所有秘书都有这种纸,整整齐齐地写着希腊字母——以便她们能在数学公式里能认出这些字母——还注了音。就在那儿,沿着纸的上缘,漫不经心地写着π=3.14159。好了,六位数,那么为什么秘书必得知道圆周率的数值呢?明摆着的;没别的理由!
我走到文件柜那儿,试第一个:31-41-59。没开。然后,我试59-41-31。也不灵。然后,95-14-13。往前,往后,头朝下,这么摆,那么放——都不管用!
我把写字台抽屉关了,走到门外,又想到了开锁的书;其次,试试心理法。我对自己说:“弗里迪·德·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学常数当保险柜密码的家伙。”
我回到第一个文件柜那里,试27-18-28——啪啦!开了啊!(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圆周率的数学常数,是自然对数的底,e:2.71828……)有九个文件柜,我已经把第一个开了,但我要的文件不在里面——柜子是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的。我试着开第二个柜子:27-18-28,啪啦!密码相同,也开了。我想,“妙哉!我已经打开了关于原子弹的机密文件,但是,如果我在将来要讲这故事的话,那我一定得拿准全部密码真的一个样儿!”有几个文件柜在下一个房间里,于是我就在其中的一个柜子上试27-18-28,开了。现在,我已经开了三个保险柜——全是一样。
我心里想:“现在,我现在可以写一本开锁的书了,管保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在开头,我会讲我是怎么打开那些内容更牛、更有价值的保险柜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开锁匠开过的保险柜,里头的东西都没办法跟这个比——柜子里关的是人,就另当别论了——比毛皮或者金砖厉害。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我开的保险柜,装着和原子弹有关的全部机密:钚的生产程序,纯化工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是怎么工作的,中子是怎么发生的,原子弹是怎么设计的,尺寸是多大——洛斯阿拉莫斯那地方所知道的全部情报:一应俱全!”
我返回第二个文件柜,拿出了我需要的那份文件。然后,我拿了一支红铅笔,在办公室里到处都是那种黄纸片上写道:“借用编号LA4312文件一份——撬锁贼费曼。”我把这纸片放在一摞文件顶上,把柜门关上。
然后,我到我打开的第一个柜子那儿,写了另一张纸条:“这个柜子也并不比另一个难开——聪明的家伙”,把柜子关上了。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柜子里,我写道:“要是密码全都一样,那就全都容易开——同一个家伙。”我也把这个柜子关了。我返回我的办公室,写我的报告。
那天晚上,我去了咖啡馆吃晚饭。弗里迪·德·霍夫曼在那儿。他说他要到办公室去工作,所以我就跟他去了,仅仅是为了好玩。
他开始工作了,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另一个房间去开那里的一个文件柜——这事儿,我倒没想到——他先开的柜子,碰巧是我放第三张纸条的那个。他开了抽屉,看到了那个异物——那个黄灿灿的纸条,上头还用鲜红的铅笔涂鸦了什么玩意儿。
我在书上看到过,说是受了惊吓的人,脸会变成菜色,但我以前还没见识过。敢情,绝对是真的。他脸发灰了,接着变成了黄绿色——他那样子,真是可怕。他拿着这个纸片,手在哆嗦,“看……看……看这是什么啊!”他说,浑身筛糠。
纸条上说:“要是密码全都一样,那就全都容易开——同一个家伙。”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
“我保险柜的密……密啊……密码,全是一……一……一样的!”他连话都说不成个儿了。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哦。”
“现……现在我……我知道了。”他说,抖作一团。
血液从脸上流走的另外一个效果,一定是脑子不灵。“他还签了名,还签了名啊!”他说。
“什么?”(我名字没在这张上面啊。)
“没错,”他说,“和那个一直企图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家伙,是同一个人!”
在整个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后,总有传言说:“有人一直企图闯入欧米伽大楼!”你知道,在战争期间,他们为了原子弹在做实验,想得到足够的材料,以便把材料聚拢起来发生连锁反应。他们把一块儿材料,扔到另一块儿上,让它从另一块儿中间穿过,当它穿过去的时候,反应就会发生,他们就测量得到了多少中子。那一块材料从另一块材料中间落得太快,因此没什么东西能够聚集起来,也不会爆炸。但,他们需要足够强烈的反应,那样他们才能知道事情真的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了,才能知道一切都按预期的那样进行——这实验太危险!
他们自然不会在洛斯阿拉莫斯镇中心做这个实验,而是在好几英里开外、翻过好几个台地的一个峡谷里,一切都封锁了。这座欧米伽大楼也围着栅栏,还有岗楼呢。在夜半时分万籁俱寂的时候,兔子会从草丛中窜出来,闯到栅栏上,弄出一些动静来。卫兵开枪。执勤的中尉走过来了。卫兵能怎么说——不过是只兔子?那不成。“有人一直企图闯进欧米伽大楼,我把他吓跑了!”
所以呢,德·霍夫曼面如死灰、浑身发抖,他没意识到他的逻辑里有漏洞:那个一直企图闯进欧米伽大楼的家伙,和站在他身边的这个家伙,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家伙,这事儿还不清楚呢。
他问我,这该如何是好。
“得,看看少没少文件。”
“看样子没事儿,”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什么。”
我设法把他领到我从里面取了文件的那个柜子那儿。“哦对了,如果全部密码是相同的,备不住他会从另外一个抽屉里拿点儿什么。”
“是啊!”他说,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第一个文件柜打开,发现了我写的第二个条子:“这个柜子也并不比另一个难开——聪明的家伙。”
到那时候,作孽的究竟是“同一个家伙”还是“聪明的家伙”,并无区别:他完全明白,就是那个一直企图闯进欧米伽大楼的家伙。因此,要说服他把我放第一张纸条儿的那个文件柜打开,还真费劲。我记不得我说了什么,把他说动了。
他打开那柜子,于是我就往门厅那儿溜,因为我有点儿害怕了。等他发现是谁给他搞的这一套,他会割断我喉咙!
不出所料,他把我追到了门厅。他倒没发怒,却是实实在在地搂住了我,因为他心里完完全全地一块石头落了地:原子弹机密失窃,不过是我的一场恶作剧啊。
几天后,德·霍夫曼告诉我,他需要从克斯特的保险柜里取个东西。唐纳德·克斯特(Donald Kerst)回伊利诺伊州去了,很难找到他。“如果你用心理方法能打开我全部的保险柜,”德·霍夫曼说(我已经告诉过他我是怎么弄的),“或许你也能这样把克斯特的保险柜弄开。”
到那个时候,这故事已经到处传扬了,因此好几个人都过来看热闹,看我打开克斯特的保险柜的这一匪夷所思的过程——我对这柜子是陌生的。没必要避着人了。我没有克斯特保险柜的后两组密码;要运用心理方法,我需要周围认识克斯特的人。
我们大家都到了克斯特的办公室,我检查了抽屉,希望能发现线索:什么也没有。然后,我问他们,“克斯特会用哪种密码——数学常数吗?”
“啊,不!”德·霍夫曼说,“克斯特干的事儿,非常简单。”
我试了10-20-30,20-40-60,60-40-20,30-20-10。不灵。
然后,我说:“你们觉得他会用什么日期吗?”
“没错儿!”他们说,“他这种家伙,就是用日期的主儿。”
我们试了若干日期:8-6-45,原子弹爆炸的日子:86-19-45;这个日期;那个日期;原子弹项目的启动日期。什么也不管用。
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溜了。他们没耐心看我捣鼓这一套,但解决这类事儿,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
然后,我决定把大约1900年以来到现在所有特别的日期都试一遍。这听起来不老少,但没多少,第一组数是月份,1~12,我只试3个数,10、5和0。第二组数是日,1~31,我可以试其中的6个数。第三组数是年,到当时只有47个数,我可以试其中的9个数。因此,8000个可能的密码被缩减为162个,我在15~20分钟之内就可以试完。
幸运的是,我是从12月份这头开始的,因为到最后我把柜子打开的时候,密码是0-5-35。
我转过头问德·霍夫曼:“1935年1月5号前后,对克斯特有什么特别的?”
“他女儿是在1936年出生的,”德·霍夫曼说,“那想必是她的出生日了。”
现在,我已经把两个陌生的保险柜打开了。我越发老练了。现在,我到专业水平了。
还是战争结束后的那个夏天,资产部的那个家伙,打算把政府买的一些东西收回去,再当剩余物资卖掉。其中有一件是上尉的保险柜。我们都认识这个保险柜。这位上尉,是在战争期间来的,断定那些文件柜对他将要搞到的那些机密文件是不够安全的,因此他必得要一个特别的保险柜。
我们的办公室都在一些稀松的木头楼里,上尉的办公室在一个木头楼的二楼上,他订购的那个保险柜是个钢造的、很重的保险柜。工人不得不先搞了木头底座,再用特别的起重机把它弄上台阶。因为我们没什么娱乐活动,大家都在看热闹,看这个大保险柜,费那么大劲,移往他的办公室,大伙儿都在开玩笑,说他会把什么机密藏在这个保险柜里啊。有个伙计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他的保险柜里,让他把他的东西放在我们的保险柜里。因此,大家都知道这个保险柜。
资产部这主儿,想把它卖掉,但首先得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知道密码的人,那位上尉是一个,可他在比基尼(Bikini)
 ;阿尔瓦雷茨(Alvarez)
;阿尔瓦雷茨(Alvarez)
 也知道,可他忘了。那主儿就求我打开这个保险柜。
也知道,可他忘了。那主儿就求我打开这个保险柜。
我到了他办公室,对那个秘书说:“为什么不给那个上尉打个电话,问他密码啊?”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倒要打扰我打扰八小时。除非你打打电话,否则本人不伺候。”
“行啊,行啊!”她说,她拿起电话,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那个保险柜。就是这玩意儿,那个巨大的、钢制的保险柜,它的门大开着呢。
我回到秘书那儿:“开了。”
“神了喂!”她一边放电话,一边说。
“没什么神的,”我说,“本来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呀,资产部毕竟也能把它打开。”
我跑到资产部找那主儿。“我去看了那柜,本来就开着嘛。”
“啊对,”他说,“抱歉我忘告诉你了。我们把我们的固定锁匠叫到那儿,打算钻开它;但在开钻之前,他想试试能不能打开,他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第一项情报:洛斯阿拉莫斯现在有固定锁匠啊。第二项情报:这人知道怎么钻保险柜,我对此倒一无所知。第三项情报:他能打开陌生的保险柜——在几分钟之内。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职业选手,一个货真价实的情报来源啊。这家伙,我得会会。
我发现他是个锁匠,战后他们雇了他来处理这种事儿(战后他们不怎么担心安全问题了)。原来他没多少开锁的活儿,所以他也修理我们用过的那些计算器。在战争期间,我一直在修那些玩意儿——所以我有门路去会会他。
我去见人,从来不会鬼鬼祟祟、拐弯抹角的;我径直走过去,自我介绍。但目前这档子事儿,会会这主儿蛮重要的。我也知道,我要是不向他显显本事,他是不会告诉我开保险柜的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在理论物理学部的地下室里,我就在那儿工作——我还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没人在晚上用那些机器。因此,首先,我在晚上经过他门口到我的办公室。如此而已;我不过是打那儿走过去罢了。
几个晚上之后,都不过是“嗨”,打个招呼。过了一阵子,他认出打这儿走过的,是同一个家伙,他说“嗨”,或者“晚上好”。
这过程太慢,持续了几个星期,然后我看到他在修玛珍计算器。关于计算器,我什么也没说;还不到说话的时候。
我们之间话逐渐多了一点儿:“嗨!我看你干活,蛮卖力气的!”
“敢情,蛮卖力气!”——如此而已。
最后,出现了一个突破:他请我喝汤。现在我们相处融洽。天天晚上我们都在一块儿喝汤。现在,我开始说了一点儿加法机的事儿,他说他遇到了个麻烦。他一直想把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到那个轴上,可他没有顺手的工具什么的;他已经为这事儿忙了一个星期了。我告诉他,在战争期间,我就是用这些机器工作的。“我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今天晚上,你把这机器放那儿就成了,我明天瞧瞧它。”
“好。”他说,因为他已经没辙了。
第二天,我看了这个鬼东西,想用手抓着那些轮子把它们安回去。它总是啪啦一声跳回来。我心里想:“如果他试同样的办法试了都一个星期了,我也试了,可办不到,那就不是个正确的搞法!”我停下来,仔细看它,我注意到,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仅仅是个小洞。我恍然大悟:我把第一个轮子弹了上去;然后,我把一段铁丝穿在那个小洞里;然后,我把第二个轮子弹上去,再在它的小洞里穿铁丝。然后,下一个,下一个——跟往线上穿珠子相似——我试了头一次,就把整个东西装上去了,装得整整齐齐,把铁丝抽出来,一切都办妥了。
那天晚上,我让他看那个小洞,让他看我是怎么弄的。打那儿以后,我们谈机器谈得多了去了;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办公室里有许多小格架,里头都是拆到一半儿的锁,还有保险柜锁的零件。哇,漂亮啊!但我仍然没提锁和保险柜的事儿。
最后,我琢磨着,日子到了,于是我决定抛出个诱饵,关于保险柜的:关于保险柜,我会告诉他一桩让他瞧得上眼的事儿——当保险柜开着的时候,你是能把它后两组密码搞到手的。“嗨!”我看着那些小格架说。“你在捣鼓摩勒斯保险柜啊。”
“是啊。”
“你知道,这些锁啊,不堪一击。
如果保险柜开着,你是能把它后两组密码搞到手的……”
“你能?”他说,终于表现出一点儿兴趣来了。
“是啊。”
“让我看看怎么弄。”他说,我给他演示怎么弄,他把头转朝我。“尊姓大名?”到那时候,我们还没互相通名报姓呢。
“迪克·费曼。”我说。
“我的个老天爷!”他颇为敬畏地说,“开锁大家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真是相见恨晚啊!我想向您请教,怎么开保险柜。”
“这话儿怎么说的?你知道怎么开保险柜。”
“不知道。”
“听着,上尉的那个保险柜的事儿,我听说过。这一次,我动了这么大心思,因为我想跟你会面。你可倒好,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开保险柜。”
“真不会。”
“得,那你必定知道怎么钻保险柜。”
“那个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我叫起来,“资产部那主儿说,你带着家伙,去钻上尉的那个保险柜来着。”
“假定您是吃开锁匠这碗饭的,”他说,“一个家伙过来让你去钻个保险柜。你怎么办?”
“我嘛,”我回答,“我就装模作样地把我的家伙备齐了,带着家伙去找那保险柜。然后呢,在保险柜上随便找个地方,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通乱钻,饭碗就保住了。”
“确确实实,我就这么干的。”
“但你把它打开了啊!你必定知道怎么开保险柜。”
“哦,是啊。我知道那些锁,在出厂的时候,设置的密码是25-50-25或者50-25-50,我就想啦,‘谁知道,或许那家伙懒得换密码呢’,第二个密码果然管用。”
因此,我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东西——他开保险柜,和我用的是相同的妙法。但更好玩儿的是,那个牛气冲天的上尉,必得要一个超级保险柜,兴师动众,费那么大劲,把这玩意儿吊到他办公室,可他自己却懒得重设密码。
我一个接一个地走访我们楼里的办公室,试那两个出厂密码,五个保险柜,我就能打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