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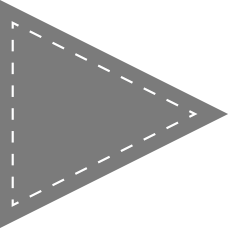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从低处看洛斯阿拉莫斯
[1]
从低处看洛斯阿拉莫斯
[1]
当我说“从低处看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我是实话实说。在目前,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尽管我是个有点儿名气的人,可在当时,我完全不是个有名气的人。我开始参加“曼哈顿计划”的时候,甚至连个学位也没有。对你讲洛斯阿拉莫斯的故事的许多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对某些军国大计都忧心忡忡。没什么军国大计让我忧心忡忡。我总在下层扑腾。
有一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的房间里工作,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进来了,说他已经得到资金,要做一项秘密工作。他本不该对任何人提起这个,但他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知道他要干的是什么,我就会明白我非得入伙儿不可。因此,他告诉我,把铀的几种同位素分离开,最终为了造一个炸弹。他有一种办法,可以把铀的同位素分离开(和最终用来造炸弹的那一种不同),他想发展这种方法。他把这个告诉了我,说:“有个会……”
我说,我不想干这个。
他说:“那好吧,三点有个会。会上见。”
我说:“你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没关系,因为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不干。”
因此我就回头去忙我的学位论文了——忙了大约3分钟。然后,我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想这事儿。德国人有希特勒,他发展原子弹的可能性是明摆着的。他们在我们之前发展起这东西,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决定三点去开会。
到四点,我已经在一个屋子里伏案工作了。我在忙着计算,看这个特别的办法,是不是会受到从离子束中得到的电流总量的牵制,等等。我就不说得过细了。但我得在那儿工作,我得写论文。我尽可能卖力地工作,尽可能快地工作,好让那些在那儿建造设备的人马上进行实验。
这像是那种电影,你看到一台设备在“嘟、嘟、嘟”地响。我每次去看这设备,它就变大了些。当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所有的伙计都决定为此工作,都把他们的科研停了下来。在战争期间,全部的科研工作都停了,除了洛斯阿拉莫斯做的这一小块儿。这也不算什么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工程。
来自各种科研项目的全部设备,都凑一块儿,弄成了这么一个新设备,好做实验——分离铀的同位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把自己的工作停了,尽管过了一阵子之后,我确实休了6个星期的假,把学位论文写完了,刚好在到洛斯阿拉莫斯之前,拿到了学位——因此,我的地位并不像我让你相信的那样,低到那么个程度。
我在普林斯顿见到了许多大人物,这是我参加这个项目较早时候的有趣经历之一。我以前没见过几个大人物。但是,有个评估委员会,不得不一直帮我们的忙,并且帮我们在最后决定我们将用什么办法来分离铀的同位素。这个委员会有像康普顿
 、塔尔曼(Tolman)、史密斯(Smyth)、尤里
、塔尔曼(Tolman)、史密斯(Smyth)、尤里
 、拉比
、拉比
 、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
 这些人。我参加这个委员会,是因为我懂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的理论,因此他们要问我问题,跟我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人先提出一个论点。然后,比方说,康普顿会解释一个不同的论点。他会说,那个事儿会是这个样子,而他完全对。另一个家伙会说,那好,也许吧,但存在另一种与它相左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
这些人。我参加这个委员会,是因为我懂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的理论,因此他们要问我问题,跟我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人先提出一个论点。然后,比方说,康普顿会解释一个不同的论点。他会说,那个事儿会是这个样子,而他完全对。另一个家伙会说,那好,也许吧,但存在另一种与它相左的可能性,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
因此,满桌子的人,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康普顿不重复也不强调自己的论点,这叫我既吃惊,又不安。最后,塔尔曼,他是主席,会说:“好了,听了这么多论点,我猜康普顿的论点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干了。”
委员们可以提出一大堆想法,每个人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还得记住别的伙计们说的是什么,因此,到最后,决定是根据最好的看法做出的——把一切做了归纳——不需要说上三遍。看到这么个搞法,我深受震撼。这些人真是非常了不起。
最终的决定是:他们将用来分离铀的计划,不是这个计划。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将停下来,因为,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他们将启动一个真正用来制造那种炸弹的计划。将会有一些我们必须做的实验,也有理论上的工作要做。我做的是理论工作。其他伙计都做实验工作。
问题是——现在干什么?洛斯阿拉莫斯还没准备好。鲍勃·威尔逊想利用这段时间,除了其他的事情要办之外,派我到芝加哥去发现和这炸弹有关的任何东西和问题。接下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开始制造仪器、各种各样的计算器等东西。等我们到了洛斯阿拉莫斯,这些东西都会用得上。没时间可浪费了。
我受命到了芝加哥,到各个研究单位,告诉他们我会跟他们一起工作,让他们足够细致地为我解释某个问题,那样我才能真正坐下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一到这个程度,我就去找另一个家伙,问另一个问题。这样我就理解了一切事情的细节。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我有点儿歉疚,因为他们都要卖力气为我解释事情,而我拍拍屁股就走了,也不帮他们一把。但我很幸运。有个家伙对我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不在积分符号内取微分?”半小时后,他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他们已经为此忙活了3个月。因此,利用我的“与众不同的工具箱”,我也做了一点事儿。然后,我从芝加哥返回,把情况交代了一番——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这炸弹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我记得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朋友,保罗·奥拉姆(Paul Olum),一个数学家,事后过来对我说:“等人家为这事儿拍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会让那个从芝加哥回来的家伙,为普林斯顿那儿的人做一场关于这个炸弹的报告。他会穿一身西服,夹着公文包,如此这般——可现在,你袖子脏乎乎的,就跟我们讲这件惊天动地的事儿。”
似乎还得拖延,威尔逊赶到洛斯阿拉莫斯,看看到底什么事情扯了后腿。等他到了那儿,他发现,建筑公司很卖力气,剧院盖好了,几个他们明白的建筑也盖好了;可是,怎么盖实验室——需要几条煤气管道,供水量是多少,他们还没得到明确指示。威尔逊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当即告诉他们多少水、多少煤气等事情,告诉他们开始建造实验室。
等他回到我们这儿,大家都跃跃欲试,急不可待了。因此,他们都凑在了一起,决定我们无论如何该出发了,尽管那儿还没准备好。
顺便说一句,我们都是奥本海默和其他几个人招到这儿的。他可真沉得住气。每个人的困难,他都看在眼里。他为我妻子担心,她得了肺结核,那儿有没有医院,有没有这个那个。我这么亲密地跟他接触,这是第一次,他是个好人。
我们奉命要小心行事——比方说,不要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小站,如果大家都在普林斯顿买票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有人就会猜疑,有大事儿了。因此,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买的票,只有我是个例外,因为我琢磨着,如果人人都在别的地方买票……
因此,到了火车站,我说:“我要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那人说:“哦,这么说,那么多东西,全都是给你准备的!”成箱成箱的仪器,我们已经托运了好几个星期,没指望他们会注意地址是阿尔伯克基。因此,我至少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托运那些箱子;是我要去阿尔伯克基啊。
好了,我们到的时候,房子、宿舍什么的,还没准备好。实际上,连实验室也差得远。我们提前来,是催他们。因此,他们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把附近农场的房子都租了下来。我们先是待在一所农场的房子里,早晨开车去基地。第一个早晨,我开车的时候,印象太深刻了。美丽的景色,对一个不怎么旅行的东边人来说,真是大饱眼福啊。那儿有你或许在画里才能看到的万丈悬崖。你是从下边开车上来的,可在山顶的平地上极目四望,真令人瞠目结舌。在我往上走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我说,印第安人或许在那儿住过,开车的伙计把车停了,走过拐弯,指给我看你能看到的印第安人的一些洞穴。真令人兴奋。
等我第一次到了目的地,我看到有个技术区,那最后是应该用围栏围起来的,但仍然敞着。还应该有一个小镇子,也就得有大围栏把镇子围起来。但是,他们现在还在建造呢,我朋友保罗·奥拉姆,他是我的助手,手里拿着个写字夹板,站在门口,对出入的卡车进行检查,告诉他们该往哪边去,把材料卸在不同的地方。
走进实验室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些人,我在《物理评论》上看过他们的文章,那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是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他们说。其时有个家伙从铺着图纸的桌子后面站起来,挽着袖子,朝窗外喊,命令卡车和东西跟着建筑材料往不同的地方去。换句话说,在建筑和设备准备停当之前,实验物理学家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就去盖房子,或者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另一方面,理论物理学家,可以马上开始工作,因此事情决定了,他们不住在农舍里,而住在基地。我们当即开始工作。没有黑板,只有一个带轮子的黑板。当我们推着这个带轮子的黑板到处走的时候,罗伯特·瑟伯(Robert Serber)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对原子弹、核物理这类事情所做的思考。我对这些东西,知道得不很多;我以前干的是别的。因此,我要做的事情,太多。
我每天都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时流行肺结核。可我有点儿运气。全部的大腕儿,碰巧在那个时候都离开了,除了汉斯·贝特
 。贝特需要个人跟他谈话,跟他唱唱对台戏。好了,他到办公室找到了我这个小碎嘴子,开始论证,解释他的看法。我说:“不,不,不,你发疯啊。它是这么弄的。”他说:“稍等。”解释为什么说他没疯,我疯了。我们就这么不停地吵吵。你瞧,我听到有人讲物理,我满脑子全是物理,我忘记我在跟谁讲话,所以我就说些傻话:“不,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但结果证明,那正是他需要的。由于这个,我倒升了一级,在贝特手下当了个小组长,管着四个家伙。
。贝特需要个人跟他谈话,跟他唱唱对台戏。好了,他到办公室找到了我这个小碎嘴子,开始论证,解释他的看法。我说:“不,不,不,你发疯啊。它是这么弄的。”他说:“稍等。”解释为什么说他没疯,我疯了。我们就这么不停地吵吵。你瞧,我听到有人讲物理,我满脑子全是物理,我忘记我在跟谁讲话,所以我就说些傻话:“不,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但结果证明,那正是他需要的。由于这个,我倒升了一级,在贝特手下当了个小组长,管着四个家伙。
当我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宿舍还没准备好。但理论物理学家无论如何必须待在那儿。他们先是把我们扔到了一所老旧的学校建筑里——有个小伙子以前在那儿上学。我住在一座名叫“力学山居”的什么玩意儿里边。我们全挤在那里的双层床上,而且那儿不那么有秩序,罗伯特·克里斯蒂(Robert Christy)跟他老婆到浴室,必得经过我们的房间。因此,很不舒服。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就到分派房间的那地方,他们说,你可以挑房子了。你知道我怎么办的?我在看女孩儿们的宿舍在哪儿,然后我挑了一间正对着她们宿舍的房间——尽管我后来才发现,那个房间的窗户前边,正好有一棵大树。
他们告诉我,一个房间住两人,但那仅仅是暂时的。每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澡间,每个房间有一张双层床。但我不想两人住一个房间。
我住在那儿的那天晚上,没别人,我就企图把这个房间据为己有。我妻子在阿尔伯克基患着肺结核,但我有她的几箱子东西。于是我把一件小睡裙拿出来,把上床的被子扯开,把小睡裙漫不经心地放在那儿。我还拿出几双拖鞋,在洗澡间地上撒了一些扑面粉儿。我就是要弄得好像那儿有别人住似的。结果怎么样?哈,那本该是男宿舍,明白吧?因此,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的睡衣叠得好好的,放在枕头下,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下。女睡裙叠得好好的,放在枕头下,床都拾掇好了,整理好了,拖鞋放得整整齐齐。洗澡间地板上的扑面粉儿擦干净了,没人在上床上睡。
第二天晚上,照旧。起床的时候,我把上床弄乱,把睡衣邋里邋遢地扔在上面,在洗澡间撒了扑面粉儿,等等。我这么折腾了四个晚上,大家也都搬过来住了,没有往这房间再塞进一个人的危险了。每天晚上,每件东西都整理得整整齐齐,尽管这是一个男人的宿舍。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小小的诡计把我卷进了政治。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小帮派,这是当然的——家庭妇女帮,机修工帮,技术人员帮,如此等等。好了,住在这宿舍的单身汉和单身女,觉得他们也得有个帮,因为公布了一条新规定:“妇女不得留宿男宿舍。”哈,这绝对是荒唐嘛!毕竟,咱都是成年人!这是扯的什么淡啊?我们一定要采取政治行动。于是我们对这事儿进行了辩论,大家推举我,在镇议会里做住宿舍的这些人的代表。
到我来这里大约一年半,我对汉斯·贝特谈了点事儿。他一直在这个大议会里担当职务,我把我用我妻子的睡裙和拖鞋玩儿的那套把戏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原来你是这么混到镇议会里的。”
事儿得从头说起。有个女人在宿舍里打扫卫生,一不留神,出了个麻烦:有个女的在跟一个男人睡觉!她把这事儿向女工长打了报告,女工长又向中尉打了报告,中尉又向少校打了报告。就这么逐级上报,报告通过将军们,一直到了管理委员会那儿。
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会考虑这事儿,还能怎样!可是,与此同时,有指示通过总指挥,下达到少校,下达到中尉,下达到工长,下达到女工长。什么指示呢?“不要打草惊蛇,一切都照原样儿,把卫生收拾干净,静观其变。”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报告。过了四天,他们着急了,不知所措了。最后,他们宣布了一条规定:“妇女不得留宿男宿舍!”这使得下面的人大发牢骚,他们不得不推举一个人做代表……
我愿意告诉你一点儿关于那里的检查制度的事儿。他们决定做某种全然违法的事情,对美国人民的信件进行检查——他们是没权力这么办的。事情非常敏感,要立规矩,那也得出于自愿。大家往外发信的时候,都主动不把信封糊上;他们也可以随便检查发给我们的信。我们让信封敞着,如果信OK,他们就把信封糊上。如果在他们看来信不OK,他们就把信退给我们,还别上个纸条儿,说,根据我们的“谅解”,信里有一段违反了什么什么。
就这么着,在这些特别在乎思想自由的科学家中间,检查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条条杠杠多的是。我们可以对这种管理特色发表评论,因此我们也可以写信给我们的参议员,告诉他我们不喜欢这么个搞法。他们说,如果有什么不妥,他们会通知我们的。
规矩立起来了,检查制度执行的第一天到了:电话!丁零零零零!
我问:“什么事儿?”
“请过来一下儿。”
我过来了。
“这是什么?”
“家父书信。”
“那,这是什么?”
那是张印了横线的信纸,横线是小点点儿组成的——四个点儿在下头、一个点儿在上头、两个点儿在下头、一个点儿在上头,点儿在点儿下头——
“这是什么?”
我说:“密码。”
他们说:“是啊,是密码,可它说的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
他们说:“那好,解码表呢?你怎么翻它?”
我说:“哈,我不知道。”
他们说:“这是什么?”
我说,“拙荆来函——它说TJXYWZ TW1X3。”
“那是什么。”
我说:“另一套密码。”
“解码表呢?”
“我不知道。”
他们说:“你收到了密码,却不知道解码表?”
我说:“正是如此。我做了个游戏。我向他们挑战,任由他们给我发来什么密码,我都能破译,明白吧?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儿造密码,把密码发到这儿来,他们可不会把解码表告诉我。”
检查制度里有一条:要是你在信里写些一般的东西,他们一点儿也不会找你麻烦。因此,他们说:“好吧,你一定得告诉他们,请把解码表和密码一块儿寄来。”
我说:“我不想看解码表!”
他们说:“那好,我们会把解码表拿出来。”
于是我们就达成了这么个协议。行不行?没问题。第二天,我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信里说:“给你写信可真难,因为我老感觉那个……在我肩膀头上偷看呢。”那个词儿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用橡皮擦出来的污迹。
我因此到局子里去了一趟,我说:“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信,你们也不该在信上动手动脚啊。你们可以看,但你们不该把信上的什么东西弄没了。”
他们说:“不要无理取闹。你以为那是检查官的工作方式——用橡皮擦?他们是用剪刀把东西剪掉啊。”
我说,得。于是我给我妻子回了封信,说:“你用橡皮擦过你的信吗?”她回信说:“没有啊,我没用橡皮擦过我的信啊,那一定是……”——纸上给剪了个窟窿。
于是我就去找少校大发牢骚,他得负责所有这类事儿。你知道,这得费点时间,但我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代表啊,是非曲直,得搞明白。上校跟我解释说,那些身为检查官的人,我们教过他们怎么办事,但他们理解不了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我们必须非常细致才成。
不管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你认为我心肠不坏吧?”
我说:“是的,你心肠好得不得了,但我认为你没权力。”因为,你知道,他走马上任干这个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我倒要看看马王爷长了几只眼!”他抓起电话,一切都摆平了。没人再对信动剪刀了。
然而,还有另外许多麻烦。比方说,有一天我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带着检查官的条子:“里面的信是用密码写的,但没有解码表,因此我们把这封信保存在别处。”
那天我到阿尔伯克基去看我妻子的时候,她说:“那,那东西都哪儿去了啊?”
我说:“什么东西啊?”
她说:“一氧化铅,丙三醇,热狗,换洗衣服。”
我说:“稍等——是一个列表?”
她说:“是的。”
“那是密码啊,”我说,“他们都以为那是密码——一氧化铅,丙三醇,等等。”(她要一氧化铅和丙三醇来制造一种黏合剂,好修补她的玛瑙盒子。)
头几个星期,总有这种事儿,然后我们才把事情摆平了。无论如何,有一天我在摆弄计算器,我注意到一件很奇异的事。如果你用1除以243,得数是0.004115226337……这很好玩儿。你要是把小数点后的数一直写下去,那么到559之后,那数就有点儿歪歪扭扭了,但它很快就又整齐了,好好地重复自己。我认为这是个乐事儿。
好吧,我就把这个东西塞在信封里,寄出去,信又回到我这儿。这信没过关,小纸条儿说:“看第17条B款。”我看了第17条B款,是这么说的:“信件要用英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等语言来写。用任何其他语言来写信,必须得到许可。”然后,它还说:“不准用密码。”
于是我就给检查官写了一个小纸条儿,附上我的信,纸条儿说,我觉得这封信当然不可能是密码,因为如果你真的用1除以243,事实上你确实会得出那样的得数,因此,在0.004115226337……这个数中,难得有别的情报。如此等等。我因此就要求允许我在信里使用阿拉伯数字。我因此让那封信通过了。
来往信件总是遇到某种麻烦。比方说,我妻子老是提起她写信时的那种不自在劲儿,好像检查官老隔着她肩膀偷看。现在,作为一条规定,我们不准提检查制度的事儿。我们是不会提这个的,可他们怎么告诉她呢?因此,他们老是给我发条子:“你妻子提到了检查制度。”我妻子提到检查制度,那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最后给我发了个条子,说:“请通知你妻子,不要在她的信中提到检查制度。”于是我这么开始写信:“我得到了指示通知你,在你的信中不要提到检查制度。”哈,哈哈,这怎么又提啊!于是我写道:“我得到指示通知我妻子不要提到检查制度。可我怎么弄这个事儿?另外,我为什么必得指示她不要提到检查制度?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有趣的是,那个检查官自己不得不告诉我让我告诉我妻子不要告诉我她……但是,我们早有应对。我们说,是的,他们担心信件在从阿尔伯克基的来路上被截获,如果有个人看了信,他或许就会发现这里有检查制度,她能不能正常一点儿。
因此,我下次到阿尔伯克基,跟她说:“注意了,我们别再提检查制度了。”但我们有过这么多麻烦,我们最后真的想出了一种密码,这可是违法的。如果我在我的署名后边加一个小点儿,那意味着我又遇到了麻烦,她就采取她早已炮制好了的下一个步骤。她一天到晚坐着无事,因为她病了,会想出怎么办的办法。她最后办的一件事,是给我寄了一张广告。她发现这广告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您的男朋友寄一个拼字游戏。我们把空白组合卡卖给您,您在上面写信,然后打乱它,装进一个小袋子,寄出去。”我收到了这个,纸条上说:“我们没有时间玩游戏。请告诉你妻子自我约束,按常规方式写信。”
我们还准备了两个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改进了工作,我们也就不必用它了。我们为下一封信准备的东西是这样:信在开头说,“我希望你打开这信的时候小心点儿,因为我把给你的胃药粉末装在这信封里了。”那封信里会装满药粉儿。我猜他们在办公室拆信的时候会拆得很快,药粉儿会撒了一地,他们都会气坏了,因为你不想让任何人生气。他们还得把药粉儿收拾起来……但我们不必用那些药粉儿的。
有了这些和检查制度打交道的经验,我就完全知道什么信是通得过的,什么信是通不过的。没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因此还为此打赌,赢了一点儿小钱。
有一天,我发现住在远处的工人,想进来的时候,懒得绕远路走正门,就在围栏上扯了一个洞。我就从大门口出去,从那个洞进来,再出去,再进来,直到那个中士感觉到什么事儿不对劲了。这家伙,只见人出去,不见人归来,这是怎么搞的?当然,他自然的反应,是把中尉喊了来,想为此把我扔到监狱里。我解释说,有个洞。
你看,我总是帮助人家改进工作,因此,我跟一个人打赌,我可以把围栏上有个洞这回事儿写在信里,我就把信寄出去了。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做的方式,正像这里说的。你应该看到他们是怎么管理这地方的(我们得到允许,可以说这样的话)。离什么什么地方71英尺的地方,围栏上有个洞,有多么多么大,你可以走过去。
现在,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没办法跟我说,没这么个洞。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做什么?有这么个洞,算他们倒霉。他们应该把洞补上。因此,这封信通过了。
还有一封信也通过了,信里说的是在我小组里工作的一个小伙子,约翰·肯马尼(John Kemeny)。军队里的几个白痴,半夜里把他弄醒,拿灯晃着审问他,因为他们发现了和他父亲有关的什么事儿,相信他父亲是个共产党什么的。肯马尼现在是个有名的人。
还有另外一些事儿。跟指出围栏上的洞相似,我总想旁敲侧击地指出这些事儿。在这些我想指出的事儿当中,有一件,是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些极端重要的机密;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关于炸弹和铀的研究成果,这炸弹是怎么工作的,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写在文件里,放在木头文件柜里,柜上锁着普通的小锁。当然,有好些东西都是车间里造的,比方说,一个可以放下来的铁杆儿,然后用一把锁把它扣住,但搞来搞去不过是一把锁。再说,不必把锁弄开,你也可以把东西拿出来。你只要把柜子向后倾斜就办得到。下层的抽屉里有一根小铁杆儿,指望用它来把文件拢在一起,但在下面的木头之间,有一道又长又宽的缝隙。你可以从下边把文件拖出来。
因此,我总是把锁开开,指出这很容易办到。每次我们全体开会的时候,我都站起来说,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机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放在这种玩意儿里;我们需要好一点儿的锁。一天,特勒(Teller)
 在会上站起来,他对我说:“我没把我最重要的机密放在我的文件柜里;我把它保存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那该好些吧?”
在会上站起来,他对我说:“我没把我最重要的机密放在我的文件柜里;我把它保存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那该好些吧?”
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见过你的写字台呢。”
他靠前坐着,我坐得很靠后。会议还在继续,我溜了出去,去见识一下他的写字台。
我甚至不需要把抽屉上的锁开开。结果是这样:如果你把手从下边把手伸进去,你可以像从圈儿上扯卫生纸那样把文件拿出来。你拖出一份儿,它又连着另一份儿,它再连着另外一份儿——我把这破抽屉弄个精光,把全部东西都放在一边,回到了楼上。
会快开完了,大家都往外走,我走进人群里,跑过去扯住特勒,说:“哦,让我顺便看看你的写字台。”
“没问题。”他说,让我看他的写字台。
我看了看,说:“看起来蛮不错。让我看看你藏了些什么宝贝。”
“我很高兴给你展览展览。”他说,把钥匙插进去,打开抽屉。“如果,”他说,“你自己没看过的话。”
跟像特勒这样有高度智力的人恶作剧,有个麻烦:从他琢磨出好像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到他明白了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儿之间,时间太短,你都来不及乐一下儿!
我在洛斯阿拉莫斯遇到的一些特别的麻烦,特别有趣。其中的一件事,是和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关。洛斯阿拉莫斯在准备制造原子弹,但是橡树岭却在想办法分离铀的同位素——铀238和铀235(会爆炸的那种)。他们才刚刚从实验中提取了一丁点儿235,一边还要熟悉其中的化学原理。他们将要建造一个大厂子,生产出大桶大桶的东西,然后他们要把提炼过的东西再次提炼,好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准备。(你不得不经过好几个阶段来提炼它。)因此,他们一方面要熟悉程序,另一方面用一个实验设备提取了一丁点儿铀235。他们在努力学习怎么对它进行化验,搞清楚那东西里有多少铀235。尽管我们把技术指南发给了他们,他们还是理解不透。
因此,最后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 Segrè)
 说,把事情搞妥,唯一可能的办法,是他下去看看他们在捣鼓什么。军队里的人说:“不行,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任何情报传到别的地方。”
说,把事情搞妥,唯一可能的办法,是他下去看看他们在捣鼓什么。军队里的人说:“不行,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把洛斯阿拉莫斯的任何情报传到别的地方。”
橡树岭的人不知道铀235要派什么用处;他们只知道努力埋头干他们的活儿。我的意思是,高层的人知道他们在分离铀,但他们不知道那种炸弹有多么厉害,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道理。下边儿的人完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军队希望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信息交流。但塞格雷竭力强调他们做不好化验,整个事情要泡汤的。因此,他到底是下去了,看他们在捣鼓什么。他在厂子里走的时候,看见他们用手推车在运大桶的水,绿色的水——那是硝酸铀溶液。
他说:“啊啊,等到这东西再次提炼之后,你们也这么推来推去?你们准备这么个搞法?”
他们说:“那是——不行吗?”
“不会爆炸吗?”他说。
啊!爆炸?
于是,军队里的人说:“你看!我们什么也不该让他们知道!现在可好,他们都慌了神儿了。”
需要多少原料才够造炸弹,军方原来已经知道了——怎么也得20千克——他们也知道,这么多提炼好的原料,怎么也不会放在厂子里,因此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子在水里的运动速度会慢下来,但其效力会大大增加。在水里,它发生反应放出辐射所需要的原料,不到十分之一——不,不到百分之一。它会把周围的人和其他什么杀死。它十分危险,而他们对安全问题完全漫不经心。
因此,一封电报从奥本海默那儿发给了塞格雷:“对整个工厂进行检查。根据他们设计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在什么地方。我们同时要计算出,多少材料集中在一起才不会发生爆炸。”
两个小组为此展开工作。克里斯蒂小组调查水溶液,我的小组调查装在箱子里的干粉。我们在计算可以把多少原料集中在一起,才安全。克里斯蒂打算到橡树岭,把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整个事情要失去控制了,我们必须去告诉他们。因此我高高兴兴地把全部数据交给了克里斯蒂,说,东西齐了,去吧。克里斯蒂得了肺炎,必得我去了。
我以前从来没坐飞机旅行。他们把机密放在一个小玩意儿里,绑在我背上!在那年头,飞机就跟公共汽车似的,只是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要大些。遇到站,得落下来,停在那儿等人上来。
站在我后面的那家伙,手里甩着个链子,说了这么一种意思:“这些日子,没优先权想坐飞机,难透了。”
他说得没错儿。我说:“哦,我不知道。我有优先权。”
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要来些将军。他们会把咱们挤到三等舱。”
“没关系,”我说,“我在二等舱。”
他多半会给他的众议员写信——如果他自己不是众议员的话,他说:“在战争期间,他们干吗让这些小毛孩子到处乱转悠,还坐二等舱?”
无论如何,我是到了橡树岭。我让他们做的头一件事,是带我去工厂。我什么也不说,只是什么都看。我发现,情况比克里斯蒂的报告还糟糕,因为他注意到一个房间里摞着许多箱子,但没注意到在隔壁房间里,挨着同一面墙,还摞着许多箱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你把过多的原料放在一块儿,砰地一声,你明白吗?
我走遍了整个工厂。我记性很差,但我高强度工作的时候,短期记忆还不错。所以我记得从90~207号楼,以及多少多少号桶等各种各样的发疯的事情。
当晚我回到房间,把整个事情理了一遍,对他们解释,危险在哪儿,应该怎么补救。事情很简单。你把镉加在溶液里,把水里的中子吸收掉;按照规定,把箱子分开放置,别放得太密集。
第二天,要开个很大的会。我忘了说一件事儿:我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听着,在橡树岭那边,如下人员是懂技术的:朱利安·韦伯(Julian Webb)先生、什么什么先生、什么什么先生。我希望你一定让这些人来开会,告诉他们,事情怎么办才安全,那样他们才真能听得明白。”
我说:“如果他们不能到会,那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说:“那你就说:洛斯阿拉莫斯方面将不为橡树岭工厂的安全问题负责,除非……!”
我说:“你的意思是,小小的费曼,到那儿去,对他们说……?”
他说:“是的,小小的费曼,你去,就这么办。”
我长得实在太快了!
等我到会场的时候,果不出所料,我想见到的公司里的大腕儿、技术人员,都在。将军们,还有那些对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在。这很好,因为,如果没人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这工厂会被炸上天。那儿有个赞姆沃尔特(Zumwalt)中尉,负责照顾我。他告诉我,少校说我不应该告诉他们中子是怎么工作的,也不要说任何细节,因为我们是想把东西分开,因此只告诉他们怎么保障安全,就行了。
我说:“照我看,除非他们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否则要他们遵守一大堆规则,那是不可能的。照我看,只有我告诉他们,他们才能知道怎么工作,洛斯阿拉莫斯方面将不为橡树岭工厂的安全问题负责,除非他们完全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这感觉不错。中尉把我领到上校那儿,对他重复了一遍我的看法。上校说:“给我5分钟。”然后他走到窗口那儿,站在那儿,思考。这是他们很拿手的事儿——决策。关于原子弹工作原理的信息,应该不应该传达到橡树岭的工厂这问题,必须而且也能够在5分钟内得到决定,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因此对军队里的这些家伙们肃然起敬,因为要是让我来决定任何重大的事儿,无论给我多长时间,我也决定不了。
5分钟之后,他说:“好吧,费曼先生,照你说的办吧。”
我坐下来,我把中子的事儿都告诉了他们,中子是怎么工作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太多的中子都凑在一块儿了,你们一定得把原料分开放啊,用镉吸收啊,噼里啪啦讲了一通——在洛斯阿拉莫斯,这都是些基础的东西,他们可是闻所未闻,因此在他们看来,我跟个大天才似的。
结果,他们决定成立许多小组,自己计算,学习怎么弄。他们开始重新设计厂房,而且工厂的设计师在场,建筑设计师,机械师,化学工程师,都在忙活新工厂怎么把原料分开。
他们告诉我,过几个月再来;等工程师们完成了工厂的设计的时候,我就又来了。现在,我该看看工厂了。
这工厂还没盖呢,你怎么看啊?我不知道。赞姆沃尔特中尉,老在我周围转悠,因为我在哪儿,都得有人跟着。他带我到一个屋子里,里头有两个工程师,和一张好长好长好长的桌子,上头放着一堆图纸,告诉拟建的工厂每层楼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校里学过机械制图,但我不太会识图。于是他们就把那一堆图纸铺开,开始为我解释,以为我是个天才。在这个厂房中,他们应该避免的事情之一,是不要把原料堆积起来。他们有些麻烦,比方说,有干燥器在工作的地方,干燥器就趋向于把过多的原料积累起来;如果阀门卡住了什么的,过多的原料就积聚起来,那就会爆炸。于是他们对我解释说,这个厂房设计成这样:如果有一个阀门把原料卡住了,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每个地方都需要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解释这是怎么工作的。四氯化碳从这儿进来,硝酸铀从这儿进到这儿,它往上,再往下,它穿过地板上了楼,通过管道上来,是从二楼上来的,啪啦啪啦啪啦——一张一张地翻图纸,下去上来,下去上来,说得很快,解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化学工厂。
我整个晕了。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图纸上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有个什么玩意儿,我开始还以为是窗户呢。那是小方框儿,中间打个叉儿,到处都画这鬼东西。我以为是窗户,但不是啊,不可能是窗户,因为它不总在边上。我想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
想必你也曾经处境如此尴尬:后悔你不早问。不懂就问,早没事儿了。可现在,人家都讲了那么一大堆了。你也犹豫了老长时间。要是你现在才问,他们会说:“你浪费我这么长时间,什么意思啊?”
我可该怎么办啊?我有了个主意。那或许是个阀门。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把它压在第三页图纸中间的那个神秘的小叉儿上,说,“如果这个阀门给卡住了,那会怎么样?”——我心里盘算着他们会说:“那不是个阀门,先生,是个窗户。”
于是,两个人面面相觑,说:“那个,如果那个阀门卡住了——”在图纸上,一个人上上下下地比画,另一个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比画,他俩都看着对方。他们转过来,看着我,张着口,像受了惊吓的鱼,说:“您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把图纸卷起来,离开了,我们也走了出来。赞姆沃尔特先生,一直跟着我,说:“您是个天才。您在厂子里走一趟,第二天早晨就能跟他们讲90~207号楼里C-21干燥器的事儿,我当时就知道您是个天才。”他说:“您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办到的?”
我告诉他,搞清楚那玩意儿是不是个阀门,就行了。
我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不得不用玛珍(Marchant)计算机来进行大量计算。顺便插一句,让你对洛斯阿拉莫斯有个印象:这些玛珍计算机是手摇的,上头有许多数码儿。你拿手摇它,它就加减乘除什么的,但不像如今那么容易。它是机械的玩意儿,经常在关键时候掉链子,那就必得送回工厂修理。我们有几个人把计算机的外壳卸掉了。(我们不该这么干的。上头有警告写得明白:“如果把外壳拆除,我们便不负责……”)我们把外壳卸掉,就学会了怎么修它;因为修的部位越精细,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它。我们遇到太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就把它送回厂子;但容易修的,我们自己修,活儿也不耽误。结果,所有的计算机都由我来修,可车间里有个负责维修打字机的家伙。
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很准,那个大问题——就是精确地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你得精确地计算出有多少能量释放出来这类事儿——这需要很多计算,多得我们招架不过来。有个叫斯坦利·弗兰克(Stanley Frankel)的聪明伙计,意识到这事儿用IBM的机器或许能办得了。IBM有些商用机器,名叫制表机的加法机器;还有个乘法机,你可以把卡片放进去,它就能把一张卡上的两个数乘起来。还有校对机和分类机什么的。
弗兰克就琢磨出了一个很妙的方案。如果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摆的这种机器足够多,我们转着圈儿地往机器里放卡片。搞计数的人都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但这在当初还是新生事物——用机器进行的大规模生产。我们在加法机上干过这样的事。你通常是一口气把一个步骤计算完,事儿都是你一个人做的。但这个方案有所不同——你先去用加法机,然后用乘法机,然后用加法机,等等。弗兰克因此就设计了这么一个系统,从IBM公司订了许多机器,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我们需要有个人来修理这些机器,别让这些机器停摆。军队总是把他们的一个人派来,而他总是姗姗来迟。现在,我们的活儿总是急的。我们做的每一样事儿,我们都得尽快地干。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我们把打算让机器干的所有计算步骤都搞出来了——乘以这个,然后干这个,然后除以那个。我们把程序搞出来了,可没有机器来试验。于是,我们腾了一个屋子,弄了些女孩儿在里面。每个女孩儿都有一台玛珍:一个管乘法,另一个管加法。这一位是算立方——她只管把索引卡上的数的立方算出来,然后传给下一个女孩儿。
我们如此这般转圈儿地试验,最后把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小瑕疵都去掉了。结果证明,其速度要比老方式,即每个人单独完成所有的计算步骤,快多了。我们这个系统的速度,赶得上IBM机器的设计速度。唯一的不同,是IBM机器不知疲倦,不用三班倒。可我们的女孩儿,过一阵子,都累倒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把程序的毛病都克服了,最后机器到了,可维修工没到。这是那个时代技术最复杂的机器,都是些大家伙,得拆卸了,一块儿一块儿地运来,许多许多电线,还有图纸告诉你怎么做。斯坦利·弗兰克、我和另外一个伙计,我们自己动手,把机器组装起来,但我们遇到了麻烦。最大的麻烦,是那些大腕儿们总是过来说:“要把东西搞坏的啊!”
我们把机器装起来了,有的时候,它运行正常,有的时候组装错了,不转了。最后我捣鼓乘法机,我看到它里面有个零件弯曲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为它可能啪地一下子断了——人家一直对咱说,咱非得弄出点儿不可挽回的事儿不可。到修理工来了的时候,他把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机器装了起来,一切正常。但那台让我遇到麻烦的机器,他也觉得麻烦。三天之后,他仍然在跟这最后一台机器忙活。
我凑过去,说:“哎,我发现那个玩意儿弯了。”
他说:“啊,可不是嘛,都是它惹的祸!”扳直了!一切正常了。这么说是它惹的祸啊。
哈,弗兰克先生,发起这个方案的,就是这主,得了计算机病,如今玩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这种病。这病很严重,会完全妨碍正经事儿。和计算机有关的麻烦,是你和它玩。计算机可太妙了。按钮都由你掌握着——你按这个,它就是个偶数,你按那个,它就是个奇数——如果你聪明,用这么一台机器,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干越来越老道的事儿。
过了一阵子,整个系统崩溃了。弗兰克心不在焉,没监督着大家。系统运行得很慢很慢——此时此刻,他却坐在另一个屋子里,琢磨怎么让一台制表机自动打印出角度X的反正切,那样机器就开始运行,打印纵表,然后,吱、吱、吱,一边打印,一边通过积分计算把反正切值计算出来。一次运行,就弄出一整套反正切表来。
绝对是吃饱了撑的。我们有反正切表嘛。但是,只要你曾经用计算机工作过,你就理解这种病——它能让你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这是一乐子!但他是第一个得这病的人,这个作茧自缚的可怜家伙。
领导要我把在小组里的工作放下,接管IBM小组。我竭力避免染上那种病。尽管在9个月里只解决了3个问题,但我这个小组还是很不错的。
真正的麻烦,是没人告诉这些伙计任何事情。军队从全国选了他们这帮人来,说是来做所谓“特遣工程”的事儿——都是些有工程能力的高中生。他们被派到洛斯阿拉莫斯来,住在兵营里,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他们来工作了,他们用IBM机器工作——打孔,那是些他们不知何物的数字。没人告诉他们那是什么。事情做得很慢。我说,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是让这些懂技术的家伙,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奥本海默去跟安全部门谈了谈,得到了特别许可,这样我才去讲了很好的一堂课,告诉他们,我们在干什么。他们欢呼雀跃:“我们在打仗啊!我们明白那是什么!”他们知道了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计算出的压力高,那就意味着释放出的能量大,等等。他们知道了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整个变了!他们开始发明一些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他们改善了程序。他们加夜班。在晚上也不必有人监督他们;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他们什么都理解;他们发明了我们需要的好几种程序。
因此,我的小伙子们出息了,只需要告诉他们那是什么,就成了。结果,尽管他们以前花费了9个月解决了3个问题,现在我们用3个月解决了9个问题,几乎快了10倍。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秘密方式之一,是这样:一捆卡片,都得走一圈儿。首先是加法,然后是乘法——这样,它得在这屋子里经过一圈儿机器,很慢的,因为它老这么转来转去。于是我们琢磨出了一个办法,把另一套不同颜色的卡片也加到转圈儿计算中,但时间和前一套不一致。我们一次就可以解决两三个问题。
但这让我们有了另外一个麻烦。比方说,接近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在我们在阿尔伯克基试爆之前,来了问题:释放的能量有多少?我们已经计算过好几种设计不同的炸弹的能量释放,但还没计算过最终用来试爆的这一种。因此,克里斯蒂来跟我们说:“我们在1个月之内,想知道这东西炸起来有什么结果”——这么说吧,很短的时间,比方说3个星期。
我说:“不可能。”
他说:“什么呀,你们1个月解决了两个问题。每个问题,只需要2个星期,或者3个星期。”
我说:“我知道。解决问题,实际上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们是平行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没办法更快了。”
他出去了,我开始想。有没有办法让它转得更快?没有别的事情来占着机器,没别的事情来打岔儿,办得到吗?我在黑板上写了“我们办得到吗?”向小伙子们挑战。他们全喊起来,“办得到,我们干两班儿,我们加班加点。”都这么个说法。“办了!办了!”
有了规定:别的问题都放下。只有一个问题,全力以赴解决这一个。于是他们开始投入工作。
我妻子阿琳患了肺结核——病得确实厉害。好像任何时候都会出事儿,因此我提前做了准备,借了宿舍里的一个朋友的汽车,以便到时候好紧急赶往阿尔伯克基。他名叫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
 。他是个间谍,用他的汽车把原子弹机密从洛斯阿拉莫斯送到了圣达菲(Santa Fe)
。他是个间谍,用他的汽车把原子弹机密从洛斯阿拉莫斯送到了圣达菲(Santa Fe)
 。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
。但当时没人知道这个。
阿琳病危的时刻来临了。我借了富克斯的车,捎带了两个搭便车的,以免这车在往阿尔伯克基的路上出问题。不出所料,我们一到圣达菲,就爆了胎。那两个家伙帮我换胎,正当我们准备离开圣达菲的时候,另一个轮子又爆了。我们就把车推到了附近的一家加油站。
加油站的家伙在修另一个人的车,我们得等上一阵子,才能轮到他来帮我们的忙。我甚至不想说什么,倒是那两个搭便车的,到加油站那里跟他说明了情况。我们很快就有了一个新轮胎(但没有备用的了——在战时,轮胎很难搞到)。
大约离阿尔伯克基50千米的地方,第三个轮子瘪了。我就把车扔在路上,搭便车走完余下的路。我给一家修车行打了电话,让他们过来把车弄走,与此同时,我去了医院看我妻子。
我赶到之后才几小时,阿琳死了。一个护士进来填写死亡证明书,又出去了。我和我妻子多待了一会儿。我看了看我7年前送给她的那个钟,那时她刚刚患了肺结核。在那年头,这算是个好东西:那是个用数码显示的电子钟;随着机械部分的运转,数码会变化。这钟很娇气,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停摆——我必须时不时地修修它——但在那些年月中,我没让它停过。现在,它又停了——停在9:22,死亡证明书上写的就是这个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的房子里,冷不丁地,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法:我祖母死了。接着就来了电话,事儿是这种事儿,却是打给彼得·伯内斯(Pete Bernays)的——我的祖母还活着。我记得这事儿,万一这电话就是打给我的呢?我琢磨着,这种事儿,有时候碰巧会发生——我祖母毕竟也是风烛残年了——尽管大家或许相信,这种事儿的发生,是某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在生病期间,一直把这钟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现在,它停在她死去的那一刻。有的人,对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将信将疑,没有善于怀疑的头脑——尤其身在那样的情势之下——一时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是会这样解释的:没人动过那个钟,把它解释成寻常现象,是不可能的。我很能理解他们这种想法。但钟不过是停了而已。这就成了那些匪夷所思的现象的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例证。
我看到房间里光线很暗,我记得当时那个护士把钟拿起来,转到灯光这边儿,看钟面好看得清楚些。这就很容易把钟弄停。
我到外边走走。或许我在自欺欺人,但让我惊讶的是,我没有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有的那种感觉。我没有高兴,但也没觉得特别难过,这或许是因为,7年来,我已经知道这事儿是免不了的了。
我不知道我如何面对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希望大家拉长着脸跟我谈这事儿。当我返回的时候(在路上又爆了一个胎),他们都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她死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了,我不想为此终日哀伤。
(我显然为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安慰的事:现实是重要的——我一定要理解,从生理学上说,阿琳究竟是怎么了;我没哭,直到几个月之后。当时我在橡树岭,我正走过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头挂着女式服装,我想阿琳或许喜欢其中的一件。此时此刻,我不胜悲戚。)
等我回去进行计算工作时,我发现那里一团糟。有白色的卡,有蓝色的卡,有黄色的卡,我开始说:“没人要你们解决另外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嘛!”他们说:“出去、出去、出去。稍安勿躁——我们会把一切解释清楚。”
那我就稍安勿躁,事情是这样的:当卡片在里面走的时候,这机器有时会出错儿,或者他们也可能把卡片塞错了。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们以前通常的搞法,是返回去,从头再来。但他们注意到,在一圈儿计算的某一点上发生的一个错误,仅仅影响附近的几个数,下一圈儿也影响附近的几个数,如此等等。它是论每包卡片计算的。如果你有50张卡,你在39号卡那儿出了个错误,它会影响37、38、39号卡。下一圈儿受影响的,是36、37、38、39和40号卡。下一次,这错误就像一种病那样蔓延开来。
他们往回走一段儿,发现了一个错误,于是就得到一个主意。他们只计算那个错误周围的一小叠卡片。因为往机器里塞10张卡,要比塞50张的一叠卡,快得多,所以他们在继续计算那传播疾病的50张卡的同时,快速地计算10张卡的那一叠。因为10张卡的那一叠计算得很快,他们就把它封起来,并纠正它的错误。好聪明啊。
这帮家伙干得如此神速,靠的就是这办法。假如他们停下来从头再来,我们就损失了时间。我不一定能想出这法子啊。他们却在做这不一定的事儿。
当然,正当他们在忙活的时候,发生了个事儿。他们在蓝色的那叠卡里发现了一个错误。于是他们弄了张数少一些的黄色的一叠卡;这黄的一叠比蓝的一叠走得快。正当他们为此疯魔的时候——因为在他们把这个弄好了之后,他们不得不去纠正那一叠白卡里的错误——我这当老板的踱进来了。
“别来烦我们。”他们说。我不去烦他们了,一切都搞妥了。我们及时解决了问题。事儿就是这么办成的。
起初我是个小卒子。过了一阵子,我当了小组长。我见到了一些大人物。见到那些魅力四射的物理学家,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经历之一。
其中当然有恩里科·费米
 。他曾经从芝加哥来了一趟,稍微问了问情况;如果我们有问题,他就帮我们。我们曾经和他开了个会,我一直在搞计算,也取得了一些结果。那些计算太精细了,非常难。在这方面,我通常是专家;我总是能告诉你结果会是怎么个样子;在我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个结果。但是,现在的事情太复杂,结果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我解释不了了。
。他曾经从芝加哥来了一趟,稍微问了问情况;如果我们有问题,他就帮我们。我们曾经和他开了个会,我一直在搞计算,也取得了一些结果。那些计算太精细了,非常难。在这方面,我通常是专家;我总是能告诉你结果会是怎么个样子;在我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也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个结果。但是,现在的事情太复杂,结果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我解释不了了。
因此,我告诉费米我正在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开始解释那些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结果之前,让我想想。结果会是这个样子(他说对了),结果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这太明显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他这一招儿,本该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他比我强十倍。真是山外有山啊。
接着是约翰·冯·诺伊曼,大数学家。我们通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我们在峡谷里走,贝特和鲍勃·巴舍尔也经常入伙儿。那真是一乐子。冯·诺伊曼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为你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负责。由于冯·诺伊曼的这个建议,我形成了对社会强烈的不负责任感。这使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是冯·诺伊曼播下了这颗种子,这种子在我的思想里长成了活跃的不负责任感!
我还见到了尼尔斯·玻尔
 。他那时名叫尼古拉斯·贝克(Nicholas Baker),他是和他儿子吉米·贝克(Jim Baker),他的名字实际上叫亚奇·玻尔(Aage Bohr),一起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他们是从丹麦来的,父子俩都是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这个你都知道。即使对那些大腕的家伙来说,玻尔也是一尊大神。
。他那时名叫尼古拉斯·贝克(Nicholas Baker),他是和他儿子吉米·贝克(Jim Baker),他的名字实际上叫亚奇·玻尔(Aage Bohr),一起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他们是从丹麦来的,父子俩都是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这个你都知道。即使对那些大腕的家伙来说,玻尔也是一尊大神。
我们一起开过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人都想一睹伟大的玻尔的风采。因此那儿人很多,当时我们在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边哪个角落里。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只能从大家脑袋之间的缝隙看他。
在他第二次来的那天早晨,我接到了个电话。
“喂——费曼吗?”
“是我。”
“我是吉米·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说说话。”
“和我?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好了,好了。八点可以吗?”
因此,在早晨八点,在大家醒来之前,我去了那地方。我们进了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让这炸弹更有威力,我们考虑的是下面这个看法。”
我说:“不成,那不管用。那没威力……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于是他说:“如此这般,怎么样?”
我说:“那听上去好那么一点儿,但透着点儿蠢劲。”
就这么谈了大约两小时,来来往往地说了很多想法,还发生了争论呢。伟大的玻尔,不断拿火点他的烟斗,烟斗总是灭。他讲话的方式,不大好懂,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很难听明白。他儿子的话,我听得比较清楚。
“好吧,”他最后点着烟斗说,“现在,我猜我们可以把那些大腕们招呼来了。”于是他们把别的家伙们都叫来了,和他们讨论。
后来,他儿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上次他来的时候,玻尔对他儿子说:“还记得坐在后边那个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吗?就他这么一个家伙,不怕我。我想法走火入魔的时候,他敢直言。因此,下次咱们想讨论的时候,不能和那些张口闭口是的、是的玻尔博士的家伙们说了。把那小子找来,咱们先跟他聊聊。”
我总是这么傻乎乎的。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讲话。我总是为物理学操心。如果那个想法看起来糟糕,我就说它看起来糟糕。如果它看起来好,我就说它看起来好。我不会拐弯抹角。
我总像这样过日子。这很好,很快乐——但愿你也能这么办。在我的一生中,我很幸运,可以这么办。
我们把计算搞出来了,下一件事儿,当然,就是试爆。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在家里休了一个很短的假期,那是在我妻子去世不久,传来消息说:“小宝宝在哪天哪天要降生了。”
我飞了回去,我到的时候,大巴刚刚要开,所以我就直接去了现场。我们在那儿等着,在30千米开外。我们有个收音机,他们该告诉我们这东西什么时候爆炸之类的,可收音机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就在它应该爆炸的前几分钟,收音机好了,那边告诉我们还有20来秒,这是对我们这些站在远处的人而言的。另一些人,靠得比较近,在10千米的地方。
大家发了墨镜,好戴着墨镜看。墨镜啊!30千米之外,透过墨镜,你啥玩意儿也看不到。我琢磨着,真对你眼有害的(亮光怎么也伤不了眼),只有紫外线。我坐在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的后边儿,因为紫外线穿不透玻璃,这该安全吧,这样我才好看那个鬼东西。
时候到了,那边一团巨大的闪光,晃得我猫下腰去,我却在卡车的底板上看到一片紫色。我说:“不对劲。这是视觉残留的余像。”我于是抬起头,看到白光变成了黄的,又变成了橘红的。云朵形成又消散——这是冲击波压缩和膨胀的结果。
最后,一个橘红的大球,中心明亮异常,它变成了一个橘红的球,开始升腾,稍作汹涌状,边缘稍微黑了一点儿,然后你看到它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大烟团,内部的火突突窜出,还有热。
这一切持续了大约1分钟。那是一个由明到暗的序列,我都看见了。或许我是看清楚了这鬼东西的唯一的一个人——第一次“三合一”试爆。别人都戴着墨镜;10千米处的人,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们按照指示趴在地上。我多半是用肉眼看它的唯一的家伙。
最后,大约一分半钟,突然,一声巨响——嘣,然后作隆隆之声,犹如滚雷一般——这声音让我心里有底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没人说一句话。我们只是默默地看。但这声音,让大家如释重负——特别让我如释重负,因为,这声音,从那么远传来,厚实,这意味着,事儿真的成了。
站在我旁边的那人,说:“那什么玩意儿?”
我说:“那就是那炸弹了。”
那人是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在那儿,是为了写一篇文章来讲述整个情况。我本是负责带他到各处看的。后来发现,事情对他来说,太技术性了,因此后来来了个史密斯(H.D.Smyth),我就带他到处看。我们做过的一件事,是我们到了一个房间,在一个窄窄的基座的顶上,有一个镀银的小球。你可以把手放在这球上。它热乎乎的。它有放射性。它是钚。我们站在这房间的门口,在谈论它。这是一种人造的新元素,在地球上是前所未有的,或许它只在地球刚形成的时候,存在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此时此地,它被分离了出来,有放射性等性质。我们把它造出来了,因此,它是个无价之宝。
与此同时,你知道大家在谈话的时候,都是个什么德性——浑身乱动什么的。他在踢那个制门器,我说,你明白吧。“没错,这制门器和这门可真是太般配了。”这个制门器是个直径25厘米的黄灿灿的金属半球——金的,真的。
话得从头说起:我们需要做一个实验,看看不同的材料能把多少中子反射回来,这为的是节约中子,那样我们就不必用掉那么多材料了。我们试过许多不同的材料。我们试过白金,我们试过锌,我们试过黄铜,我们试过金。因此,在用金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些碎金子。某人出了这么个聪明的点子,用这个大金球当存放钚的那房间的制门器。
这玩意儿爆炸了以后,洛斯阿拉莫斯一片兴奋。大家都在聚会,我们到处乱跑。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打鼓什么的。只有一个人,罗伯特·威尔逊,坐在那儿,闷闷不乐。
我说:“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他说:“那是个可怕的东西,我们造的。”
我说:“这可是你挑头儿的。你把我们大伙都扯了进来。”
你瞧:我都干了什么——这其余的人都干了什么——我们蛮有理由,就动手干了,然后你卖劲干活儿,弄成了一个东西,这很快乐,很刺激。你知道,你停止思想了;你就是停止思想了嘛。此时此刻,只有罗伯特·威尔逊一个人,还在那儿思考这事儿。
此后不久,我返回了文明世界,到康奈尔大学教书。我的第一感觉很奇怪。我不理解那种感觉,但当时是很强烈的。我坐在纽约的一家饭店里,比方说,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开始想,你知道,广岛原子弹的破坏半径有多大……第34大街离这儿多远……所有那些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等等。我一边走,一边看有人在造大桥,或者在铺新路,我想,他们都疯了,他们就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造新东西?都在瞎忙活。
但幸运的是,这种瞎忙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不是吗?因此,说造大桥是瞎忙活,可见是错了;别人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