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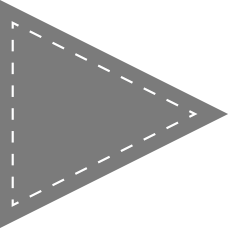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考验猎犬
考验猎犬
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有点儿闲工夫,经常坐几小时的车,去看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住院的妻子阿琳(Arlene)。有一次我去看她,不能马上进病房,于是我就到医院图书馆看书。
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关于猎犬的文章,说它们的嗅觉如何了得。作者说了他们做得好几个实验——猎犬能确定哪些物件被人动过,等等——我开始想:闻东西,猎犬确实是非同凡响,能追踪人留下的气味儿,诸如此类;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
到可以看我妻子的时候,我就去看她了,说:“我们做个实验。那里的那些可乐瓶子(她积了六捆空可乐瓶子,好一起送出去)。你好几天没动它们了,对吧?”
“对啊。”
我把六捆瓶子拿到她那儿,手没碰瓶子,说:“好了。我现在出去,你拿一只瓶子,在手里摩挲大约两分钟,然后放回去。然后,我回来,看能不能说得上来是哪只瓶子。”
于是我就出去了,她拿起一只瓶子,摩挲了好长时间,因为我可不是猎狗啊!照那文章上的说法,你就触摸一下,猎狗也嗅得出来。
然后,我回来了,绝对明显!我甚至不必闻那破玩意儿,因为温度当然就不同。气味儿也很明显。你一把它凑近你脸边,你就闻得出来它潮乎乎的,热乎乎的。因此,那个实验不算数儿,因为太明显了。
然后,我看了看书架,说:“那些书,你有日子没看了,是不是?这次,我出去的时候,你从架子上拿一本书,就那么一翻——别再干别的——再合上,放回去。”
我又出去了,她拿了一本书,翻开,合上,放回原处。我进来了——这也没什么!容易。你只要闻闻那些书就行了。这很难解释,因为我们通常不谈论这个。你把每本书凑近鼻子,嗅几次,你就认得出来。那是很不同的。一本书,在那里放了一阵子,有一种干燥无趣的味儿。但是有一只手动过它,就有湿度,就有一种明显的气味儿。
我们又另外做了几个实验,我发现,猎犬确实是能耐不小,可人类也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无能:只是人的鼻子离地面太高罢了!
(我注意到,我的狗闻闻我的脚印,就能正确地认出我在家里走的路线,特别是在我赤脚的时候。因此,我也想试试这个:我手脚并用,在地上爬,一边还嗅着,想看看我能不能认得我走过的和没走过的地方有什么不同,而我发现不可能。因此,狗比我强得多。)
许多年后,在我初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在巴舍尔(Bacher)教授家里有个聚会,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人都在那儿。我不知道怎么提到了这事儿,但是我把闻瓶子、嗅书的故事告诉了他们。自然,他们一个字儿也不相信,因为他们总以为我弄虚作假。我就不得不演示一番了。
我们小心地从架子上取下八九本书,没直接用手动,然后我出去了。三个不同的人动了三本不同的书:他们各自拿起一本书,打开,合上,放回去。
然后,我回来了,闻闻每个人的手,然后把那几书都闻遍了——我忘记先闻的是哪一本——丝毫不差地找到了那三本书;但把一个人认错了。
他们仍然不相信我;他们以为我在变什么戏法。他们不停地琢磨我是怎么弄的。这种把戏人尽皆知,人群里有个托儿,给你发暗号儿,他们都在琢磨谁是托儿。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牌戏:拿一副纸牌,让一个人抽出一张,再放回去,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你说:“我会告诉你,你抽的是哪一张,因为我是一只猎犬:我要把每一张牌都嗅一嗅,然后告诉你抽的是哪一张。”当然,你这么喋喋不休的,大家就一时不会相信你实际上做的那件事!
人的手,其味殊异——所以狗能辨人;你可得试试!全部的手,都有一种潮乎乎的味儿。一个烟民的手,其味儿大不同于不抽烟的。女士所用的香水常常不同,诸如此类。如果有人碰巧口袋里装着硬币,碰巧他在口袋里玩弄那些硬币,你也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