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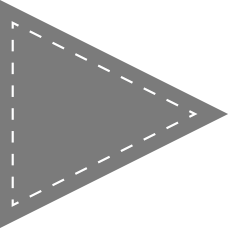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测心术
测心术
我爸爸一直对魔术和狂欢节上演的那些把戏感兴趣,想知道那是怎么弄的。他知道的一件事,是测心术。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是在长岛(Long Island)中间的一个叫帕查崮(Patchogue)的小镇子上长大的。到处都是海报,说下个星期三,有个测心术的要来。海报上说,几个有名望的市民——市长、一个法官,还有一个银行家——要把一张五块的票子藏在个什么地方。等那个测心术的一来,就能找到它。
他来的时候,大家都围拢过来,看他显本事。他一只手拉着法官,一只手拉着银行家,票子就是他俩藏的,开始沿着街道走下来。他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转过街角,走到了另一条街上,然后又走到另一条街上,进了该进的那个房子里。他是跟他俩一道儿走的,总拉着他俩的手,进了房子,上了二楼,进了那个该进的房间,走到一张办公桌前,撒开那两位的手,拉开该开的抽屉,五块的票子果然在此。神哈!
那年头,要受到好的教育,难了;因此,这个测心术士就被雇来当我爸爸的私塾先生。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爸爸就问他,没人告诉他钱在哪儿,他是怎么把钱找到的。
测心术士是这么解释的:你拉着他们两人的手,松松垮垮地拉着,你走的时候,轻轻摇晃着。你到了个十字路口,你往哪儿去,往左,还是往右。你往左稍微那么一摇晃,如果不对,你能感觉出那么一点儿抵触,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去那边儿。但是,当你往正确的方向上走的时候,因为他们认为你或许真能知道该往哪儿走,他们比较会顺水推舟,没什么抵触。因此,你必须总是稍微那么摇晃着点儿,试探着往哪边儿走看来最少抵触。
我爸爸把这故事讲给我听了,他说那还是需要不少的练习。他自己从来也没试过。
后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有个伙计名叫比尔·伍德沃德(Bill Woodward),我决定拿他来试试。我突然宣布我会测心术,能猜透他的心思。我告诉他到那个“实验室”里——一大间房子,里头有好几排桌子,桌子上满是各种各样的设备、电路、工具,到处都是垃圾——在什么地方,挑出一件什么东西,再出来。我跟他解释为什么让他干这个,“现在我测你的心,把你带到那物件那儿”。
他进了实验室,记下了一个特别的东西,然后出来了。我拉着他的手,开始摇晃。我们走过这条走道,再走过另一条,果真就走到了那东西那儿。我们试了三次。其中有一次,我找到了那个东西——它混在一大堆东西中间。另一次,地方我是去对了,但错过那东西才几寸——东西找错了。第三次,不知哪儿出毛病了。但是,总的说来,结果比我原来想的好。很容易的。
那次之后,当时我大约26岁,我爸爸和我去了亚特兰大市。那儿狂欢节在室外变戏法的,五花八门。我爸爸去办什么事儿了,我就去看一个玩测心术的。他坐在台子上,背对观众,穿着长袍,扎着穆斯林的那种大头巾。他有个助手,一个小个子家伙在观众中间跑来跑去,喊着类似这么一些话,“哦,大师,这个笔记本是什么颜色?”
“蓝色的!”大师说。
“啊,了不起啊先生,那么这位妇女叫什么名字啊?”
“玛丽!”
有个家伙站起来:“我叫什么名字?”
“亨利。”
我站起来说:“我叫什么名字?”
他没回答。那个家伙显然是个托儿,但我琢磨不透这个测心术士是怎么玩的另外一些把戏,像说出笔记本的颜色。他在大头巾下面戴着耳机吗?
在我和我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把这个告诉了他。他说:“他们设计了一些暗号,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暗号。咱们回去看个究竟。”
我们回到了那个地方,我爸爸对我说:“这里是五毛钱,你到那边算命摊子上算算命吧,半小时以后见面。”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去给那个人讲个故事,要是他儿子不在那儿不停地“嚯!嚯!”,那会顺利些。他不得不把我打发到一边儿去。
他回来的时候,把暗号整个告诉了我:“蓝色是‘哦,大师’,绿色是‘哦,无所不知的人’,如此等等。”他解释说,“我到了他那儿,后来呢,告诉他我以前在帕查崮摆摊儿卖艺,我们也有一套暗号,但算不了那么大的数,能说的颜色也没那么多,我问他,‘你怎么能记得住这么多东西啊?’”
这位测心术士对自己的暗号很是自豪,坐下来,把他的那一整套对我爸爸一五一十地讲了个透彻。我爸爸就有这个本事,我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