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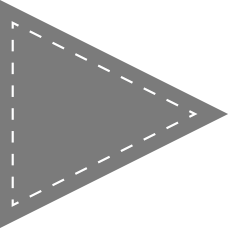 魔鬼头脑
魔鬼头脑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约翰·惠勒手下做研究助手。他要我解决个问题,这问题难了,我毫无进展。因此,我想起了我早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有的一个想法。这想法是:电子不对自己发生作用,只对其他电子发生作用。
有这么个问题:在你振动一个电子的时候,它就辐射出能量,于是它就失去了一点儿能量。这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力作用于它。当这个电子带电荷的时候,和它不带电荷的时候,那个力必定是不同的。(如果电子在带电荷和不带电荷的时候,力是严格一样的,在一个情形中它失去能量,而在另一个情形中不失去能量。你对同一个问题,不能有两个不同的答案。)
标准理论是这样:电子依靠自己活动,这才产生了那个力(所谓辐射反应力),但我看到的是,电子只有依靠别的电子才活动。因此,当时我意识到,我麻烦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但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到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个问题。)
我想的东西是这样:我将振动这个电子。它将使附近的某个电子也振动,从附近某个电子返回来的效应,或许就是辐射反应力的来源吧。因此我做了一些计算,把结果送给了惠勒。
惠勒立刻就说,“呵,那不对,因为,你的意思是,它与其他电子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然而,它完全不应该决定于这些变量中的任何变量。照你那么说,它还与其他电子的质量成反比呢;它还与其他电子的电荷成正比呢。”
让我闹心的是,我以为他想必一定做过这个计算。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像惠勒这样一个人,你一把那个问题给他,他一眼就能看明白所有的东西。我必得计算,可他看看就明白。
然后,他说,“它将会被延迟——波返回得晚——所以,你说的这些,不过是反射光而已。”
“哦!当然。”我说。
“可是,等一下,”他说,“让我们假定反射光是以超前波(及时返回来的反作用力)的方式返回来的,因此它就会立刻返回。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效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假定有许多电子,都在空间当中:其数量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也许我们能够把它整个都抵消了。”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能那么做。结果非常好,正如所料。这是一种也许正确的经典理论,尽管它和麦克斯韦
 或者洛伦兹
或者洛伦兹
 的标准理论不同。它没有电子自作用论的那种无限性的麻烦,它很巧妙。它有作用和延迟,有时间上的向前和退后——我们把它叫作“半超前与半延迟势位”。
的标准理论不同。它没有电子自作用论的那种无限性的麻烦,它很巧妙。它有作用和延迟,有时间上的向前和退后——我们把它叫作“半超前与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想,下一个问题将转到关于电动力学的量子论上,这个理论(我想)和电子的自作用有麻烦。我们盘算着,如果我们能够先把经典物理学中的这个麻烦消除掉,然后从中搞出一个量子论,我们也能同样把量子论弄妥当。
既然我们已经把经典理论搞妥帖了,惠勒说,“费曼,你是个年轻的伙计——你应该为此开一个讨论会。在讲话方面,你是需要经验的。我也会解决量子论的部分,晚些时候,我也开一个讨论会。”
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专业讲话,惠勒和尤金·魏格纳
 做了安排,把这个讨论会加在了例行的讨论会计划中。
做了安排,把这个讨论会加在了例行的讨论会计划中。
在讲话前的一两天,我在餐厅里见到了魏格纳。“费曼,”他说,“我想你和惠勒的工作很有意思,因此我已经邀请了罗素来参加讨论会。”亨利·诺里斯·罗素
 ,当时著名的大天文学家,来参加讲座!
,当时著名的大天文学家,来参加讲座!
魏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伊曼教授,也有兴趣。”约翰·冯·诺伊曼
 在哪儿都是最伟大的数学家。“另外,泡利
在哪儿都是最伟大的数学家。“另外,泡利
 教授眼下从瑞士到这儿访问,事儿凑巧了,所以我也邀请了泡利教授过来。”——泡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到了这个时候,我脸都黄了。最后,魏格纳说:“只是爱因斯坦
教授眼下从瑞士到这儿访问,事儿凑巧了,所以我也邀请了泡利教授过来。”——泡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到了这个时候,我脸都黄了。最后,魏格纳说:“只是爱因斯坦
 教授难得光临我们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但你的工作太有意思了,我也特别请了他,所以他也过来了。”
教授难得光临我们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但你的工作太有意思了,我也特别请了他,所以他也过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脸都绿了,因为魏格纳说:“别,别!别担心!但我只是想警告你:如果罗素教授睡着了——他肯定会睡着的——那不意味着这个讨论会很糟糕;他开什么讨论会都睡觉。另一方面,如果泡利教授不停地点头,好像从头到尾都对这个讨论会表示首肯似的,你也不必得意。泡利教授点头,是因为他有肌肉麻痹症。”
我回到惠勒教授那儿,一五一十地把这些有名的大人物数给他听,他们都来参加他让我弄的这个讲话,告诉他我六神无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别担心。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回答。”
于是我就准备着讲话,等那天来了的时候,我走进去,做了某种没有讲话经验的年轻人经常做的事儿——我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你瞧,人年轻啊,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当然,那个是反比,这个是这么搞的……”因为在座诸位都已经知道这些;他们一看就明白。但是,他却不明白。他实际上只能正儿八经地通过搞这些个代数计算来弄出结果——因此,就这么一片方程式。
正当我提前把这些方程式写得满黑板都是的时候,爱因斯坦进来了,兴味儿十足地说:“哈喽,我参加你们的讨论会来了。可首先,这茶在哪儿啊?”
我告诉他茶在哪儿,接着继续写方程式。
然后,讲话的时间到了,就在这里,这些魔鬼头脑就在我面前,等着呢!我的第一次技术性讲话,就有这么一帮子听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把我压到榨汁机里!我记得很清楚,当他们从牛皮纸信封里把我的稿子拿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双手在哆嗦呢。
可是,有个奇迹发生了;在我一生中,这种奇迹一而再地发生。对我来说,太幸运了:从我开始思考物理学的那一刻起,我不得不把精神集中在我正在解释的东西上面,我脑子里什么杂念也没有了——我完全对神经兮兮产生了免疫力。因此,在我发动起来之后,我简直不知道在这屋子里的都是谁。我只是在解释这个想法,没别的。
但是,在讨论会的末尾,提问的时候到了。泡利,他挨着爱因斯坦坐着,立刻站起来说:“我银为这嘎理论不可能对,银为这噶、这噶,还有这噶,”他转向爱因斯坦说,“你同意吗,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同——意。”和和气气的,德国味儿的“不同意”,很礼貌的。“我只是发现,要为引力相互作用搞出一种相应的理论,会是很困难的。”他说的引力相互作用,意思是他的广义相对论,那是他的小宝宝。他继续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实验证据,我对正确的引力理论,还没有绝对的把握。”爱因斯坦坦然承认,事情或许会和他的理论所说的不同;他对别的观念很宽容。
我希望我能记得泡利说了什么,因为,若干年后,我发现,当这个理论用来建立量子论的时候,它不能令人满意。可能是这样:这个大腕儿立刻就注意到了麻烦所在,接着就为我解释成问题的东西,但我不必回答问题,这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以至于我没有仔细听他们说什么。我确实记得我和泡利一起走上了帕尔默图书馆(Palmer Library)的台阶,他对我说:“到惠勒演讲的时候,关于量子论,他会说些什么呢?”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他单打独斗。”
“哦?”他说,“这人干活儿却不告诉助手,他在为量子论搞些什么?”他走近一点儿,用低沉而神秘的声音说,“惠勒永远不会开那个讨论会的。”
他说准了。惠勒没开那个讨论会。他认为,把量子的部分搞出来,应该是容易的;他认为自己几乎把它搞出来了。但他没有。到讨论会该开了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不知道怎么弄了,因此没啥可说。
我也没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关于半超前与半延迟势位的量子论——我为此工作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