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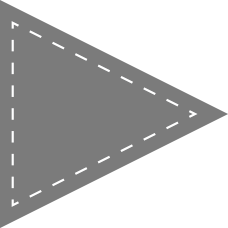 猫地图?
猫地图?
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餐厅里,人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我和学物理的闲坐,但过了一阵子,我想:去看看这世界上别的地方搞些什么名堂,或许好玩儿吧。于是,我每一两个星期,就去别的圈子坐坐。
我和学哲学的坐一块儿的时候,我听他们相当严肃地讨论一本书,叫《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怀特海
 写的。他们的措辞,好玩儿,我听不大明白他们说的啥。我现在不想打搅人家的谈话,不想没完没了地要求人家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倒有几次,我要他们解释,他们也乐意为我解释,可我还是摸不着头脑。最后,他们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会。
写的。他们的措辞,好玩儿,我听不大明白他们说的啥。我现在不想打搅人家的谈话,不想没完没了地要求人家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倒有几次,我要他们解释,他们也乐意为我解释,可我还是摸不着头脑。最后,他们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会。
他们的讨论会,像是上课。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几章《过程与现实》——某个家伙先发表一个关于这书的报告,接着是讨论。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对自己下了保证,把嘴闭上,时时提醒自己对这个学科一无所知;我到那儿,看景儿而已。
那儿发生的事儿,够典型的——典型到难以置信,却是真的。首先,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这就难以置信,但也是真的。一个学生做了个报告,说的是那周要讨论的那章书。在书里,怀特海不停地使用“本质对象”(“essential object”)这词儿,使用的方式很技术化,他想必是对这个词儿定义过,但我听不懂。
在讨论了一阵子之后,关于“本质对象”是个什么意思,主持讨论会的教授说了些什么话,意在澄清一些东西,还在黑板上画了一种像是闪电的玩意儿。“费曼先生,”他说,“你说,电子是‘本质对象’吗?”
哦,我麻烦来了。我承认,我没读过这书;怀特海用这个短语是个什么意思,我一点儿不明白。我到这儿来,仅仅是看看热闹。“但是,”我说,“如果教授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我将努力回答教授的问题。砖头是本质对象吗?”
我想做的,是想发现他们认不认为理论构想是本质对象。电子是一种我们使用的理论;在理解自然运行的方式上,它太有用了,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真实的。通过类比,我想把关于理论的一个看法讲清楚。说到砖头,我下一个问题将是:“砖头的里面是怎样的?”——我将指出,没有人曾经看到过砖头里面是怎样的。你每次把砖头打碎,你只能看到表面。砖头有一个里面,仅仅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理解得好一点儿。关于电子的理论,是类比性质的。因此,开始的时候,我问:“砖头是本质对象吗?”
几个回答于是就出来了。有个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头,作为一块个别的、特殊的砖头,那就是怀特海说的本质对象的意思。”
另一个人说:“不对啊,一块个别的砖头,可不是本质对象;所有砖头共同具有的那种一般特性——即它们的‘砖性’——才是本质对象。”
又有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本质对象’不在砖头自身。‘本质对象’,意思是心灵里的一个观念;当你思考砖头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观念。”
又一个家伙站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我告诉你,看一块砖头,竟然有这么多别出心裁的不同方式,我以前可是闻所未闻。而且,正如在那些关于哲学家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这讨论会在完全的混乱中结束。在他们以前的全部讨论中,他们甚至不曾问过自己,像砖头这么简单的对象,像电子这么更简单的对象,是不是“本质对象”。
在那之后,在晚饭时间,我就去了生物学那桌转悠。我一直对生物学有些兴趣,那些家伙谈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有几位邀请我来听听他们的细胞生理学。对生物学,我略知一二,但这是个研究生的课。“你认为我招架得住吗?教授让我进去吗?”我问。
我们问过那位讲师,牛顿·哈维(H.Newton Harvey),这人做了许多关于发光细菌的研究。哈维说,我可以参加这个特别的、高等的课程,但有一样——我要做全部的作业,要交书面报告,与别人一视同仁。
还没上第一节课之前,那些请我来上课的家伙,想给我看看显微镜下面的什么东西。他们在那里放了一些植物细胞,你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绿点子,那叫叶绿体(阳光照在上面,它就制造糖),在那里兜圈子。我看了看,抬起头问:“它是怎么兜圈子的?什么玩意儿推着它转?”
没人知道。后来我知道,在那个时候,这种兜圈子还没有被大家理解。因此,我立刻就发现了生物学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却没人知道它的答案。在物理学那里,你一定要走得深入一点儿,你才能发现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有意思的问题。
开课了,哈维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很棒的大画儿,画的是细胞,为细胞里全部东西都加了标签。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些东西,他讲的,大部分我都能懂。
画儿讲完了,那个请我来上课的家伙说:“喂,怎么样?”
“还行,”我说,“我唯一不明白的,是卵磷脂的那一部分。什么是卵磷脂?”
这家伙就开始用那种单调乏味的声音解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植物和动物都一样,都是由跟小砖头似的东西构成的,那叫‘细胞’……”
“听着,”我不耐烦了,“那个,我知道;否则我不来上这课了。什么是卵磷脂?”
“我不知道。”
我必须和别人一样递交书面报告,布置给我的第一个报告,是关于作用于细胞上的压力效果——哈维给我选了这么个题目,是因为它和物理学有关。尽管我理解我做的事情,但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把术语都念错了。在我谈论“分裂蛋儿”而不是“分裂球儿”以及别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时候,全班总是笑得前仰后合。
给我选的第二篇文章,是亚德里安
 和布朗克
和布朗克
 写的。他们表明,神经脉冲是一种尖锐的单脉冲现象。他们曾经拿猫做过试验,测量过神经上的电压。
写的。他们表明,神经脉冲是一种尖锐的单脉冲现象。他们曾经拿猫做过试验,测量过神经上的电压。
我开始读这篇论文。这文章老是谈伸肌、屈肌、腓肠肌之类的东西。这块肌肉,那块肌肉,都是有名字的,但这些肌肉在神经的什么位置上,或者在猫的哪块,我整个是一头雾水。于是我就去找生物学部的图书馆员,问她能不能给我找一张猫地图。
“猫地图,先生?”她相当恐怖地问我,“您的意思是,一张动物园的导游图!”从此以后,就起了传言,说是有个学生物的傻瓜学生,在找一张“猫地图”。
到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开始画了一幅猫的轮廓,把许多肌肉都标上名字。
班上别的学生打断了我:“那些东西我们都知道!”
“哦,”我说,“你们知道?怪不得我能这么快就赶上你们这些学了四年生物的。”15分钟能找得到的东西,他们却把时间都浪费在死记硬背这种东西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个夏天我都可以开车到美国的什么地方旅游。有一年,在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后,我想:“这个夏天,我不再到不同的地方了,我要到一个不同的领域。”
那时正是华生和克里克
 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之后不久。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些很棒的生物学家,因为德尔布鲁克
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之后不久。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些很棒的生物学家,因为德尔布鲁克
 的实验室就在那儿,华生也来加州理工学院做DNA密码系统的讲座。我听了他的讲座,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讨论会,热情十足。那是生物学领域非常令人振奋的时代。待在加州理工学院,真是妙啊。
的实验室就在那儿,华生也来加州理工学院做DNA密码系统的讲座。我听了他的讲座,也参加了生物系的讨论会,热情十足。那是生物学领域非常令人振奋的时代。待在加州理工学院,真是妙啊。
我不认为我会真的做一些生物学的研究,因此,我在夏天去访问生物学领域的时候,我不过是在生物学实验室里磨蹭,“洗洗盘子”而已,顺便也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我去了生物学实验室,把我这想法告诉了他们。罗伯特·埃德加(Robert Edgar),一个年轻的博士后,在那里负点儿什么责任,说他不会让我这么干。他说:“你必得真的做点儿研究才成,像研究生那样,我们就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干。”正中下怀。
我听了一门抗生素的课,告诉我们怎么怎么进行抗生素的研究(噬菌体是一种病毒,它有DNA,攻击细菌)。我立刻发现,我免除了不少麻烦,因为我懂一些物理学和数学。我知道原子在液体里是怎么回事,因此离心机是怎么工作的,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我知道的统计学,足够让我在数培养皿上的小点点的时候,理解统计学上的偏差。正当生物学的家伙们在费劲理解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可以把时间用于学习生物学的部分。
有一个有用的试验技巧,是我从那个课上学会的,今天我仍然用得上。他们教给我们怎么用一只手拿试管,还得把试管帽取下来(用中指和食指),把另一只手腾出来干别的(比方说用吸管来吸氰化物)。现在,我能用一只手拿牙刷,而用另一只手拿牙膏,把帽儿扭下来,扭上去。
已经发现,抗生素能够发生突变,这种突变能够影响它们对细菌的攻击力,我们的任务是研究那些突变。还有一些抗生素,会发生二次突变,能使它们重新组织起对细菌的攻击力。有些抗生素突变回去了,跟它们以前一模一样。另外一些不是这样:它们对细菌的作用,有一点儿轻微的改变——它们的行动,会比通常的快些或者慢些,细菌也比通常生长得慢些或者快些。换句话说,存在一些“后转突变”,但这些突变并不总是完美的;有时抗生素仅仅会部分地恢复它们失去的能力。
埃德加建议我做一个试验,发现这种后转突变,是否发生在DNA螺旋体的同一个地方。小心翼翼,加上大量单调的工作,我发现了后转突变的三个例子,发生的地方非常靠近——比目前他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靠近——这三个突变也使抗生素的作用能力得到部分的恢复。这工作做得很慢,好像是守株待兔:你不得不等啊等啊,直等到你遇到个很稀奇的二次突变。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如何让抗生素更经常地突变,如何更快地侦察到突变;但是,我还没赶上掌握一种好技术,夏天完了,而我也不想继续研究这问题了。
可是,我的休假年来了,因此我打算继续在这个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但研究另外一个题目。我和马特·梅瑟尔森(Matt Meselson)工作了一阵子,然后从英国来了个挺不错的伙计,叫史密斯(J.D.Smith)。这课题和核糖体
 有关。核糖体是细胞里的“机器”,它用我们现在叫作信使RNA的那种东西来制造蛋白质。用放射性物质,我们可以证明RNA能够从核糖体中出来,也能回去。
有关。核糖体是细胞里的“机器”,它用我们现在叫作信使RNA的那种东西来制造蛋白质。用放射性物质,我们可以证明RNA能够从核糖体中出来,也能回去。
我小心翼翼地测量和控制一切,但花费了我8个月的时间,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步骤做得毛糙了。在准备细菌的时候,要把核糖体从细菌里弄出去,在那年头细菌是依附在氧化铝上在研钵里研磨的。除了研钵,别的东西都是化学的,都在控制之下;但是,在你研磨细菌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两次完全重复研杵的动作。因此,这种试验弄不出什么结果。
我想我一定要讲讲那次我和希尔迪噶德·兰姆弗罗姆(Hildegarde Lamfrom),想发现豌豆是不是也和细菌一样能利用核糖体。问题是:细菌的核糖体,是否可以制造人类或者其他生物体的蛋白质。她刚刚搞出了一个方法,能从豌豆中提取出核糖体,并且给豌豆核糖体信使RNA,这样豌豆核糖体就会制造豌豆的蛋白质。我们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即如果我们把豌豆的信使RNA给细菌的核糖体,那么这个细菌的核糖体会制造豌豆蛋白质还是细菌蛋白质。那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和根本性的实验。
希尔迪噶德说:“我需要大量细菌核糖体。”
梅瑟尔森和我从大肠杆菌提取了大量核糖体,好用来做其他实验。我说:“该死,我会把我们弄到的核糖体给你的。我们有的是,在我实验室的冰箱里。”
如果我是一个很棒的生物学家,那将会是一个令人叫绝的大发现。但我不是个很棒的生物学家。我们想法很棒,实验很棒,设备合用,但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给她的是被感染了的核糖体——在那种实验中,那是你可能犯的最低级的错误。我的核糖体在冰箱里放了差不多一个月,被某种别的生物体污染了。假如我重新赶紧准备好核糖体,交给她的时候,当心点儿、小心点儿,把什么事情都控制好,那个实验是会有结果的,我们也会第一个发现生命一致性(uniformity):制造蛋白质的机器,即核糖体,在每个生物中都是相同的。我们站的位置没错儿,我们做的事儿没错儿,但是我做事儿像个外行——愚蠢不堪、邋里邋遢。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事儿?福楼拜书里的包法利夫人的老公,一个蠢笨的乡村郎中,冒出个念头,要给人家治歪脚,他的搞法不过是拿着大伙儿穷折腾。我和这位缺乏训练的医生,差不多。
和抗生素有关的另外一个工作,我从来也没写下来——埃德加一直要求我写下来,可我就是没腾出工夫考虑。你不在自己的领域里,就有这毛病:你不把它当回事儿。
我倒也马马虎虎地写了个东西。我把它寄给了埃德加。他读的时候,笑得喷茶。那东西没按照生物学家的套路来写——首先是,程序,如此等等。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解释所有生物学家都知道的事情。埃德加搞了个缩写本,我却看不懂了。我想他们没把它发表。我可从来没直接那样发表。
华生认为我用抗生素搞的那些东西,有点儿意思,所以他邀请我到了哈佛。我给生物系讲了个话,谈的是二次突变发生得那么靠近。我告诉他们,我的猜测,是一个突变在蛋白质里造成了变化,比方说,改变了氨基酸的pH,而另外一个突变在同一个蛋白质分子里的氨基酸那里制造了一个相反的变化,因此它部分地平衡了第一个突变——平衡得不太完美,但足以使抗生素重新运作起来。我认为那是在同一个蛋白质分子里的两个变化,它们在化学上互相抵消了。
结果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儿。几年后,毫无疑问,有人搞出了一种技术,能更快地制造突变和侦察到突变,他们发现,第一个突变是这样一个突变:其中的DNA碱基全部丢失了。这样,“密码”移位了,再也不能被“识别”。在第二个突变当中,或者是一个额外的碱基被放回去了,或者是又有两个碱基给弄出去了。现在,密码又能识别了。第二个突变发生得离第一个突变越近,被这种二次突变改变的信息就越少,抗生素一度失去的能力就恢复得越完全。每个氨基酸分子,要由三个“字母”来编码,这个事实于是昭然若揭。
我在哈佛的那个星期,华生提起了个什么事情,我们就一起做了几天的实验。那实验没做完,但我从世界上最棒的人那里,学到了一些新的实验技巧。
但那可是我了不得的时刻:我给哈佛的生物系上了一课!我总是这么干,一头扎在什么东西里,看看我能走得多远。
我学到了许多生物学的东西,得到了许多经验。生物学术语的发音发得准了一点儿,知道在论文里和讨论会上不能什么都说,还察觉到了实验里的一个技巧上的弱点。但我爱物理学,我愿意重新投身到物理学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