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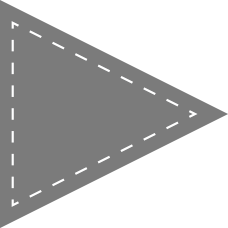 菜豆
菜豆
那年,我在我姑妈开的旅馆干活儿的时候,一定有十七八岁。我不知道我能赚多少钱——我想是每月22美元吧——我交替着一天工作十一小时,第二天工作十三小时,站柜台,或者在餐厅端盘子洗碗。下午,你站柜台的时候,还得给那个迪什么夫人送牛奶,一个病病殃殃的女人,从来不给小费。世上的事儿就这样:你没白没黑地干,却什么也得不到,天天如此。
这个旅馆在旅游胜地,紧挨着海滩,就在纽约郊外。男人们到城里去干活,把一帮老婆留在那儿打牌,因此你得把桥牌桌摆好。然后,到了晚上,男人们打扑克,你得把桌子给他们预备好了——倒烟灰缸什么的。我总是熬到深夜,两点钟的样子,因此,实际上我确确实实是一天干十三或者十一小时。
有些事情,我不喜欢,比方说小费。我觉得应该多开点钱给我们,那就不必要小费了。可是,当我给老板娘提了这么个建议的时候,除了嘲笑之外,我一无所得。她逢人便说:“理查德不想要他的小费,嘻嘻,嘻嘻,嘻嘻;他不想要小费,哈哈,哈哈,哈哈。”这种二百五,满世界都是,连我的话也听不明白。
无论怎么说吧,有段时间,一帮男人,从城里干活回来,一来就要冰块儿,好放在喝的东西里面。跟我一块儿干活的那家伙,原来确实一直是个站柜台的。他比我大,也比我内行得多。有次他对我说:“听着,我们总给安嘎那家伙送冰块,而他向来是一毛不拔——连一毛钱也不给。下次,他要冰的时候,别理他。他呢,就会叫你过去给他上冰块,在他叫你过去的时候,你就说,‘哦,抱歉,瞧我这记性。人人都有忘事儿的时候。’”
我就如法行事,安嘎给了我一毛五!可是,现在,回想此事,我才意识到,站柜台的那主儿,就是内行的那个,确实会来事儿——让别人去冒险找不自在。他派了个活儿给我,就是去训练那家伙给小费。他自己可一声不吭;他倒让我去做!
我必得像个打杂的那样收拾餐厅里的桌子。你把从桌子上撤下来的那些东西,都摞在边上的一个大托盘里,摞得足够高的时候,就端到厨房里去。这样你再拿一个新托盘回来,对吧?你应该分两步来干这事儿——把原先那个托盘端走,再拿一个新的回来——但是,我琢磨着,“我得两步并做一步走。”于是我就想把新托盘垫在下边,同时把原先那个托盘抽出来,可是它滑到一边了——咣当!盘子碗儿奔地板那儿去了。接着,自然而然,问题来了,“你捣鼓个啥啊?怎么弄掉的啊?”嗨,我想发明一种新的端托盘的方法,可这事儿怎么解释啊?
甜点中有一种早餐点心,漂漂亮亮地放在小垫盒上,搁在盘子里。要是你到后边去,你会看到一个人,大家叫他配餐员。他的麻烦,是把东西准备妥当,好用来上甜点。这人以前必定是个矿工什么的——大块头,手指头又短又粗又硬又圆。他端着一叠小垫盒,用某种冲压工艺制造的那种小垫盒,全都扣在一块儿,他得用他那短而粗的手指头把它们掰开,好放在盘子上。我总听他说:“这些个倒霉的垫盒!”在他这么忙活的时候,我记得我心里在想,“多么鲜明的对比——有人守着桌子坐着,享受放在垫盒里可爱的小点心,这位手指头短而粗的配餐员呢,在后面那儿嘟囔‘这些个倒霉的垫盒!’”世界真的是怎么样,和它瞧上去是怎么样,这两者之间,就有这个区别。
我来干配餐这活儿的第一天,配餐的那女的解释说,她通常是做火腿三明治的,为那些上夜班的家伙们做。我说,我喜欢吃甜点,要是晚饭剩下甜点的话,就给我吧。第二天晚上,我上夜班到凌晨两点,伺候那些打扑克的家伙。我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没事儿可干,百无聊赖,猛然想起有甜点可吃。我就到冰箱那儿,开了门,她在里边放了六份甜点!一块巧克力布丁,一块点心,一些桃片,一些米饭布丁,一些果冻——全了简直!于是我就坐下来,吃这六份甜点——棒极了!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给你留了份甜点……”
“妙,”我说,“绝妙!”
“但我给你留了六份,可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打那以后,她就留六份甜点。每天晚上,我来六份甜点。天天晚上不重样儿,但总是六份。
有一次,还是我站柜台的时候,一个女孩儿去吃饭,把一本书忘在柜台的电话机旁边,我就看这书。那是一本《达·芬奇的一生》,我不可能不看它;那女孩儿就把书借给了我,我把整本书都看了。
我在旅馆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你离开屋子,得费心把灯关了,可我连这个都记不住。受了达·芬奇那本书的启发,我制造了一个小玩意儿,那是一个由绳子和重锤(可乐瓶子装上水)组成的系统。我一开门,它就运作,拽动开关拉绳把里面的灯拉亮。你开门,这玩意儿就动,把灯弄亮;然后你把门关上,灯就灭。但我真正的成就还在后头呢。
我通常在厨房里切菜。菜豆必得切成一寸长。你干这活儿的方法本来是这样:你把菜豆抓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操刀,你把刀抵着菜豆和大拇指,弄不好就要把大拇指切掉。这切起来很慢的。于是我就在上面用了点儿心思,我想起了个好主意。我在厨房外边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把一只碗夹在我膝盖中间,把一把快刀以背对我45度角插在桌子上。然后,我在刀两边各放了一堆菜豆,我拿了一根菜豆,一只手拿一根,然后飞快地往我这边拉,一拉菜豆就切断了,切断的菜豆就滑到夹在我膝盖中间的碗里。
我就这样一根一根地切菜豆—— 嚓、嚓、嚓、嚓、嚓 ——大家都把菜豆给了我,到我快切到第六十根的时候,老板过来了,“你捣鼓什么啊?”
我说:“瞧瞧我这切菜豆的招数!”——说时迟那时快,横在刀刃上的,不是一根菜豆,而是一根指头。血出来了,流到了菜豆上,这下可炸了锅:“瞧瞧,糟蹋了多少菜豆!这么干活儿,傻不傻啊!”杂七杂八的就来了。这样我就不可能进行改进了,而那很容易——弄个护板什么的——可是完了,没什么机会进行技术改造了。
我还有一项发明,困难也是相似的。土豆煮熟了,要切成片儿,好做某种土豆色拉。土豆黏糊糊的,颇难操作。我想到,用一大堆刀,平行地固定在架板上,往下一切,整个土豆就一下子成了片儿。我考虑这事儿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想了个主意,我可以把铁丝这样固定在架子上啊。
于是我就到廉价商店打算买些刀或者铁丝,却真真地看到了我想要的那种玩意儿:是用来切鸡蛋的。下次来了土豆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的切蛋器,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全部的土豆切完了,然后送给厨子。厨子是个德国人,一个大胖子,厨房里的国王,他暴跳如雷,脖子筋都暴出来了,紫青的:“土豆怎么了啊?”他说:“怎么没切啊!”
我切了,但都粘在一块儿。他说:“你叫我怎么把它弄开?”
“扔到水里。”我提了个建议。
“扔水里? 哦、哦、哦、哦哦哦哦呵呵呵呵! ”
又有一次,我有了个实在好的主意。当我站柜台的时候,我得接电话。有人打进来的时候,一个什么玩意儿嗡嗡地叫,总机上一个薄片儿吧嗒垂下来,这样你就知道是哪条线。有时候,就在我帮女人们摆桥牌桌的时候,或者在下午三点来钟(那时电话不多)我坐在前门廊里的时候,突然有了电话,而我离总机还有一段距离。我就不得不跑着过去接,但是你必须从柜台后的走道上才能跑到总机那儿,先往下跑,然后转弯儿,再到柜台后边儿,这多跑了不少路,你这才看到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这花了些额外的时间。
于是我想起了个好主意。我在总机上的那些薄片上系了一些线,这些线越过柜台垂下来,然后我在每根线上系上个小纸片。然后我把电话的受话筒向上放在柜台上,这样我从柜台外也够得着。现在,有人打进电话的时候,我一看哪个纸片儿往上走,就知道总机上哪个薄片儿垂下来,我就能及时接电话了,从柜台外接,省了时间。当然,我还是要绕回去接线,但至少我可以先搭句话。我说,“稍等片刻”,然后转过去接线。
我觉得这很完美,但是有一天老板娘过来了,她想接电话,可她琢磨不透——这也太复杂了。“这些个纸片儿,怎么回事儿?电话怎么搁到这边来了?你为什么不……哎哟喂、哎哟喂!”
我想解释——老板娘是我姑妈——想跟她解释这么做很有道理,但是对一个 聪明人 ,一个 经营这家旅馆 的聪明人,这话说不得!那时我明白了:在现实世界,发明创造,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