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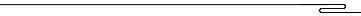
考虑中国发展要因时,笔者脑海中浮现的是“战略的强大和构想的大胆”。中国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通过引进市场经济手段,推进改革开放,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战略。
人们往往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就会产生保守心理,缺乏变革的勇气。
但是,如果不能脱去旧的躯壳,新生事物就无法萌芽。这是一种破茧重生。中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实现了大发展。
在探寻中国经济成长轨迹时,我们可以发现战略的巧妙随处可见。改革开放时设立的“深圳特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浦东大开发”都是非常巧妙的战略。“大胆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土地使用权制度”也是巧妙的战略。
高速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在支持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下开始推进的。高铁和“一带一路”有机关联,成为“经济发展走廊”。对移动网络社会的应对也是一种战略。中国以远超日本的速度在城市里实现了“无现金支付社会”。
中国“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经常受到批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对这个战略的批评是因为未能用发展的眼光观察中国。“投资是对未来的消费”,通过大胆的投资战略,营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战略源于预判和决断。战略强大意味着判断力、决断力的强大。中国政治家在判断力和决断力方面比较强大有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地理因素;二是从零起步;三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四是务实的政治。
地理因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陆地边境与多国接壤,因此国防、外交能力会比较强。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与东南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和伊斯兰各国、中亚各国、俄罗斯,甚至朝鲜,以及没有陆地接壤的韩国、日本的关系等,在中国的政治中往往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上也曾通过丝绸之路从外界获取人才、物资和其他信息。通过处理与接壤国家的关系,中国成为在战略制定上比较擅长的国家。这种战略和智慧延续到“一带一路”上。
与此相比,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没有陆地接壤的邻国,所以也缺乏提升外交能力的条件。早上看着太阳从大海上升起,晚上看着海上日落,自然会觉得一帆风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都容易缺乏奋进的动力,会产生随遇而安的想法。而且,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至今仍有驻日美军。在政治上,日本追随美国,容易忽视日本海、黄海沿岸这一侧,仅重视太平洋的另一侧。从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来看,日本都难以产生伟大的战略。
“从零起步”意味着“已经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笔者在出席《朝日新闻》2002年举办的研讨会时,曾有幸见到了东软集团的刘积仁总裁,他提到中国人在推进改革开放时考虑的是“反正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笔者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刘总裁还提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企业既没有销售人员,也没有市场,而是根据政府的指令安排生产。在那个年代,企业连R&D这一想法都不曾有过。零是一个通往无限,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数字。
中国的改革开放纯粹是从让国民变得富裕这一理念出发的。为了变得富裕,就需要坦率地学习、吸收。邓小平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坦率地向国外学习,并注重独创性的开放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在政府和民间层面都形成了勇于挑战的氛围。半途而废的想法是无法孕育出伟大战略的。
只有否定“保守的心态”,才能孕育出勇敢挑战的精神。从零起步的想法成为勇于挑战的前提。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经济高速发展,经历“1亿人口全是中产阶级”的时期,已经成为“可失去的东西非常多”的社会。所以,很多日本人不喜欢变化,思想比较保守。
“保守的心态”和“规避风险的应对方式”,拒绝“挑战”,会使新鲜空气的流动减缓。通过与外界的接触,才能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经常吸收外部新鲜空气,从外界获取信息的40年。
“人口压力”是指中国庞大人口基数的压力。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时,往往会忽视“庞大人口”这一点,不负责任地批评中国。笔者因为常年与中国有来往,所以时常会想:作为“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的领导人,其压力和紧张一定是难以想象的吧”。
在讲述中国成长要因之前,先要对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的历代领导人进行正面评价。正因为有巨大的人口压力,所以考虑问题时需要更精准、更深刻,这也成为孕育伟大战略的契机。
在庞大人口的压力下,半途而废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大胆的战略,更不可能让整个国家运转起来。
在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家也有复兴国家的紧迫感,但是现在的日本很少有政治家会想到人口的压力。日本民众有一种天生的“老实认真”的国民性。虽然多次遭受大灾难,但受灾者也能一直忍耐。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加剧时,也不会产生暴乱。虽然有提出安保法违宪,政治沦为政治家以权谋私的手段等抗议的声音,但因为日本国民性比较老实,所以时间一过,风浪也就平息了。
为了吸引到选票,选举口号就像“批发超市为招揽客人大肆散发的传单”一样,即使最终没有兑现,也没人抗议这是“欺诈”。
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而且是多民族共同居住,还有大批等着致富的人口。所以,庞大的人口压力使中国领导人必须成长起来。
领导人的经验会受到个人能力和政治体制的影响。
将中国的政治与日本的政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虽然制度有所不同,但是政治家的经验和经历,会使他们从政的政治手腕天差地别。
日本的政治家是从较小的选区里选出来的,比起国家、国民,更重视地区、居民和选举本身。也有与个人能力无关,凭借世袭成为政治家的人。
但是,中国的政治家需要有从政的经验。想成为干部,需要有基层的工作经验,而且从政的业绩会被考核。一句话,他们都是经历基层工作的种种磨砺,崭露头角而逐步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央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的常务委员们,他们的经历如下:栗战书有在河北省、陕西省、黑龙江省的从政经历;汪洋17岁起就在食品工厂工作,有在安徽省的从政经历;赵乐际是从青海省商务厅的行政人员逐步晋升为省委书记的;韩正在上海市从做仓库管理员起步,逐步上升成常委。
习近平主席也曾经在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一共有22年的从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