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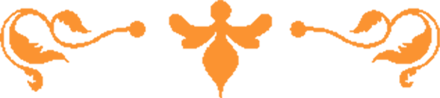

我美国的朋友想要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出来。一开始我不太想这么做,可后来我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只是我不可能凭借这部不太长的传记写出我个人一生中的全部感受,或是详细记下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所有事件。
我们人的感情会随着年岁的增加而发生变化,有些感情会失去它们当日鲜亮的色彩,似乎变得完全陌生起来;有些发生过的事件也会失去它们当时的意义,虽然现在还记着它们,却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不过,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一些强烈的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阐释了他的人生,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使得他的人生朝着一个方向,沿着一条主线前行。
我将把自己这活得并不容易的一生做个概述,并记述下其中的要点,相信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会使读者对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思想状态有个大体的了解。
我的姓名是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祖国是波兰。我的父母都是来自波兰的小地主阶层。在我的国家波兰,有不少家庭都属于这一阶层,他们都持有一份不大的产业,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现在,波兰的知识分子仍然大多是来自这一阶层。
我的爷爷一边务农,一边还管理着一所省立学校,我的父亲生性好学,曾就读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回到波兰,后来成为华沙一所预科大学里的颇有威望的物理学和数学教授。他娶了一位情趣相投的年轻女子,尽管年纪轻轻,她却已受过了严格的教育,是华沙最好的女子学校的校长。
我的父母非常热爱他们的教育事业,一生兢兢业业,他们教出的学生遍及波兰,这些学生直到现在仍然对他们心存感激。每次回到波兰,都能碰到我父母教过的一些学生,在他们的言语间无不充满对我父母的怀念。
尽管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可他们与家中的乡下亲戚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往来。我的假期常常是在他们乡村的亲戚家里度过的,这使我有机会在乡下过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机会了解一下我深深喜爱的农村。我想,我之所以热爱乡野和大自然,与我在那一独具特色的乡村所度过的时光有很大的关系。
我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在华沙,在家里的五个兄妹中,我是最小的,我的大姐14岁就死了,这样家里便剩下了一个哥哥和我们姊妹三个。母亲因为我姐姐的去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再加上身受重病的折磨,在42岁时就离开了我们,留下了悲痛欲绝的丈夫和她的孩子们相依为命。那个时候,我只有9岁,最年长的哥哥也只有13岁。
这一灾难性的事件让我第一次体味到了人生巨大的痛苦,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母亲具有卓越的个性。她头脑聪慧,知识渊博,心胸宽阔,具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她心地善良,怀有无限的慈爱之心。她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她在家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虽说她对自己的信仰非常虔诚(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可她却能包容一切,对不同的宗教信仰持宽容的态度;平等友好地对待一切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在我身上除了小女儿对母亲的那一母女间的爱以外,还有我对母亲热烈的崇拜之情。
母亲的去世对父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对子女的教育当中去。他工作的担子很重,少有闲暇。母亲一直是家中的主心骨,她的过世令我们许多年来都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
我们兄妹都是很早就上了学。我6岁入学,因为在班里数我年龄最小,长得最小,每当有人来学校参观时,我总是被老师叫到前台去朗读课文。这对我不啻是种很大的考验,因为我平日里胆小、内向,在这种时候,我真恨不得跑出去躲起来。我的父亲是位优秀的教师,他很关心我们的功课,知道如何去辅导我们。可我们当时受教育的环境并不好。我们开始时上的是私立学校,初高中时转到了公立学校。
那时候,华沙是在俄国人的统治之下,这一统治的一个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学校和孩子们所实施的管制。连波兰人自己管理的私立学校都有警察严密地监视着,而且官方还强迫连母语还未能说好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习俄语。不过,因为这些学校里的绝大部分教师都是波兰人,他们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去减轻由这种民族压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些私立学校都不能授予正式的文凭,仅有公立学校的学生才可能获得文凭。
完全由俄国人控制的公立学校对波兰人的民族精神实行直接的压制。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由俄国教师用俄语教授,这些俄国人都仇视波兰民族,把学生视为敌人。有节操、有学问的人大多都不愿意到这种学校去教书,因为他们忍受不了俄国人的这一敌视态度。处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学到的东西是否能有价值便值得怀疑了,而且,对学生的身心也造成极大的摧残。时时受到监视,受到怀疑,孩子们知道稍不留神说了一句波兰语,或是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都可能给自己甚至是家人带来危害。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生活中所有的欢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滋生出猜忌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与此同时,这一恶劣的局势也激发出波兰青年的极大爱国热忱。
尽管青少年时期我是生活在异族压迫和丧母之痛的双重阴影下,可至少还有一些快乐的记忆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我们平静而忙碌的生活中,家里亲戚和朋友们的聚会总能带给我们一些欢乐。我父亲非常喜欢文学,读过大量的波兰诗歌和外国诗歌;他甚至还自己写作诗歌,把其他国家的优秀诗篇翻译成朗朗上口的波兰文。我们很喜爱他就家事所写的那些小诗。星期六晚上,他常常为我们朗读波兰著名的诗篇和散文。这些个夜晚不仅带给我们快乐,也重新燃起了我们爱国的热情。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诗歌,能把波兰许多著名诗人的大段诗篇背诵下来,密茨凯维奇、克拉辛斯基和斯沃瓦茨基是我最喜爱的波兰诗人。在我后来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我的这一喜好便越发变得强烈起来。因为我早期学习的外国语言是法语、德语和俄语,于是我很快便熟悉了用这三种语言所写的优秀作品。后来,我意识到学习英语的必要性,就又开始学习英语,不久便能阅读英国文学的原著了。
在音乐方面,我有所欠缺。母亲是个音乐家,嗓音很美,她希望我们都能受到音乐的熏陶。自母亲死后,再也没有了来自她的鼓励,我很快便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回想起来不免有些遗憾。
我学习数学和物理一点儿也不吃力,这两门都是中学里的主课。父亲随时能给予我们辅导,他热爱科学,在学校里他自己也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他喜欢尽自己所能,向我们解释大自然的奥秘和它的规律。只是他没有实验室,不能进行实验。
假期的到来总是令我们感到欣慰,那时我们便可以避开警探的监视,去到乡下的亲戚或是朋友那里。在有着古老乡风的大家庭里,过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树林里欢快地奔跑。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干活。有的时候,我们越过俄国人统治的地方进入加里西亚山中(此地是由奥地利人统治着,政治氛围稍宽松一些)。在那里可以尽情地讲波兰语,唱爱国歌曲,而不必担心被送到监狱。
初次去到加里西亚时,那里的大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平原长大的。所以,我特别怀念住在喀尔巴阡山的小村子里的那段日子,我喜欢眺望峰峦叠嶂的山脉,喜欢在山谷和高山间被称为“海之眼”的湖泊那儿徘徊。不过,在我心中,那一对视野开阔、连绵起伏的平原的依恋从未消逝过。
后来,我有机会跟父亲到更靠南的波多尼亚(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去度假,在敖德萨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随后又北上到了波罗的海。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美好的经历。不过,直至后来去了法国,我才真正见到海洋的巨浪狂波和潮汐涌退的壮观。在我的一生中,每新见到一处大自然的景观,都会令我像个孩子似的那么高兴、激动。
中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兄妹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我的哥哥从医学院毕业后不久,便成为华沙一家大医院的主治医生。我和我的姐姐们原本都打算继承父母的事业去教书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二姐改变了主意,决定学医了。她在巴黎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嫁给了一位内科医生,一个名叫德鲁斯基的波兰人,夫妻二人在波兰的奥属喀尔巴阡山区——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大型的疗养院。我三姐在华沙嫁给了斯查莱先生,三姐常年在学校教书,工作成绩斐然。在波兰独立后,她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校长。
中学时,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15岁便中学毕业了。学习带来的身心上的疲惫让我在乡下几乎休息了一年。一年后我回到了华沙父亲的身边,希望能去一所免费中学任教。可家境的不济迫使我改变了这一决定。我已年迈、身心交瘁的父亲也需要休息了,这样一来,他本来不高的收入又会减少许多。因此,当时还不足17岁的我,便决定离开父亲去做家庭教师,开始独立的生活了。
首次离家去做家庭教师的那一经历至今历历在目。坐在火车上的我心情很是沉重。火车载着我行驶了几个小时,把我热爱的家人留在身后。下火车后,我还得坐五个小时的马车。等在我前面的会是什么呢?当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广阔的平原时,我这样想。
我去任教的那家的男主人是个农场主。他最大的女儿跟我的年龄相仿,尽管是我教她,可我俩的关系却更像是伴侣,而不是师生。我还有两个更小一些的学生,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和我的这些学生都相处得很融洽。下课后,我们常常一起到外面去散步。我热爱乡村,所以并不觉得孤独,尽管我所在的乡下的景色并不那么迷人,可我对那里的一年四季的生活仍能感到满意。我对这个农场的耕种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它的耕作方法被视为这一地区的一个典型。渐渐地我了解了庄稼的种植和生长的全过程,以及各种庄稼在地里的分布情况。在农场的马厩里,我熟悉了各种马匹。
到了冬天,整个田野被冰雪覆盖,我们驾着雪橇在旷野里飞奔。有的时候,甚至难以辨识出雪地中的路来。“当心水沟!”我会朝驾雪橇的人喊,“你就要掉进水沟里了。”“你不必担心!”他话音刚落,我们已坠入水沟!不过,这些侧翻只是更增加了我们远足的乐趣。
我记得有年冬天下了特别厚的雪,我们刨开积雪,造了一间很棒的雪屋。我们坐在里面,眺望外面被雪映成玫瑰色的田野。我们也常常到河面上去一边滑冰,一边担心天气转暖,冰雪融化,会剥夺了我们的这份快乐。
因为我在农场做家庭教师还有不少空余的时间,我便把许多在俄国人统治下无法进入学校的农村孩子组成了一个班,给他们上课。在这一教授的过程中,农场家的大女儿帮衬着我。我们用波兰语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对我很是感激。就是做这样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情也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所有这种自发组织起来教授知识的做法都是被政府禁止的,一旦弄不好就会被送进监狱,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晚上的时间我一般用来自学。我听说有几位女性就是学习了一些课程而后成功地去到圣彼得堡或者是其他地方继续深造的。于是,我决心也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习,效仿她们走过的路。
那时我还没有选定我要走的路。我对文学和社会学,像对科学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在这几年的自学当中,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方向最终还是转到了数学和物理上,并且在这一方面为将来做着扎实的准备。我想好要去巴黎深造,希望自己能攒下足够的钱,以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习。
自学的道路上充满艰辛。我在中学所接受的那点儿理科知识很是零散,跟法国的中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找了一些书籍来读。虽说成效不是那么明显,可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这叫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此外,也学到了一些对我日后有用的知识。
由于二姐决定要去巴黎学医,我不得不修改了我的计划。我们曾许诺要互相帮助,可我们家的财力却不足以让我俩同时赴巴黎求学。这样,我在那个农场主家一直做了三年半的家教,在教完了他们该学的课程后,返回了华沙,在华沙我又接手了一份类似的工作。
我在这个地方只干了一年,便回到父亲的身边。那时父亲刚退休不久,一个人独自生活着。我跟父亲在一起度过了一年非常美好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一些文学作品,我通过做家教挣些钱补贴家用。
与此同时,我继续通过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华沙,连自学都很难;不过,比起乡下来,机会还是多一些。令我高兴的是,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进到一间实验室里去做实验了,这是间市属的小实验室,我的一个表哥是那里的主任。我只有在晚上或是星期天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到那里,那时,实验室里常常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按照课本上讲的方法,做着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各种实验,有时候,所做出的结果令人感到意外。有时我会因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而备受鼓舞,有时又会因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败而感到深深的绝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这些最初的实验告诉我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可它们却也让我更加坚信,我的天性更适合于从事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实验性研究。
另外,我从所参加的一个由华沙热爱学习、立志以教育报国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中,也获益匪浅。
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波兰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团体认为,祖国的未来取决于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的力量,认为这样的一种努力将会改变祖国的面貌,使之焕然一新。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并把知识普及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
为此,大家决定开设夜校,利用晚上的时间给人们授课,各就自己的所长讲授知识。毋庸置疑,这样的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因此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这个团体里的许多无私无畏的青年是会为祖国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的。
我至今对那些由共同的社会理想走到一起的知识青年记忆犹新。诚然,因为活动经费紧张,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可我相信当时激励着我们的那些思想仍然是旨在真正取得社会进步的指南。如果个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提高自身的素质,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不断地完善自己,与此同时,为人类的进步,我们还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尤其是要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都在加强着我想要进一步深造的愿望。尽管父亲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可出于对女儿的爱,他还是帮助我早日实现了我的夙愿。我姐姐刚在巴黎结婚定居,家人商量后就决定我现在就去巴黎,住在姐姐那儿。我和父亲原想着,等我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华沙来,再度跟父亲一起愉快地生活。可命运有的时候往往跟人的愿望相反,后来,我在巴黎结了婚,便留在了法国。做科学研究是我父亲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当他得知我在巴黎所不断取得的科学上的进步时,我们父女的分离也就让他变得容易忍受了。父亲的善良、仁慈和无私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一直住在我哥哥家里,帮着哥哥带孩子,是个慈祥、循循善诱的爷爷。在1902年,我们失去了可爱的父亲,那时,他才刚刚过了70岁。
这样,于1891年11月,在我24岁的时候,我终于实现了几年来一直魂牵梦萦的理想。
到达巴黎时,我受到了姐姐和姐夫热情的接待,可我只在他们家里住了几个月,因为姐夫在巴黎郊外行医,家也安在那边,我需要离市区的学校近一点儿。像许多来自波兰的同学一样,我最终住到了一间又小又简易的屋子里,我自己收集了一些家具,安顿了下来,四年的大学生活我都是在这样的小屋子里度过的。
我不太可能把我这四年所得到的收获一一地讲述出来。我心无旁骛,没有外界的任何干扰,完全沉浸在了学习和学习所带给我的喜悦当中。至于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还是较为艰难的,我的积蓄很有限,家人也都没有能力给我提供帮助。不过,我的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我所认识的不少来巴黎求学的波兰人,他们的境况大体上也是如此。我住的房间在顶层的阁楼里,冬天它抵御不住外面的寒风,因为屋里取暖的炉子很小,又常常烧不上煤。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盆里的水便结成了冰;为了能入睡,我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都搭在被子上。也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用一盏酒精灯和几件简陋的炊具给自己做饭。为了节省开支,常常几片面包、一杯巧克力、一点儿鸡蛋和水果就是一顿饭。我自己整理房间,自己把取暖用的煤搬到六层的阁楼上去。
这种从某些方面看颇为艰难的生活,对我来说,却自有它的魅力所在。它给予我一种弥足珍贵的自由感和独立感。我举目无亲,形单影只地住在巴黎这座巨大的城市里,然而,这一单寒羁旅、无依无靠的生活从未令我感到过沮丧。虽说有时会觉得孤独,可我整体的心理状态却是平和的,是精神上的一种极大的满足。
我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了学习上,因为开始阶段的学习对我来说还是很困难的。我在中学时所学的那点儿物理知识远远跟不上巴黎大学(原索邦大学,1896年改名)所开设的这门课程。尽管在来巴黎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可与法国同年级的学生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必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尤其是数学上的差距。白天我上课,做实验,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学习到深夜。每当了解和学会了新的东西都会令我兴奋不已。就像是有个新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为我打开了它的大门,我终于得以进入其间,去自由地探求。
跟同学们的和睦相处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开始时我腼腆、话少,可不久我便留意到,几乎所有刻苦好学的同学都对我很友好。我们在学习方面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所讨论问题的认识和兴趣。
在我所学的专业里,没有来自波兰的学生。可我和一个波兰侨民的小团体有着亲密的往来。我们经常在自己所住的简陋屋子里聚会,讨论我们民族的各种问题,这样身在国外的我们也就不再感到那么孤单了。有的时候,我们一起散步,或是一块去参加公众集会,因为大家对政治都很感兴趣。但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我不得不中断了与他们的往来,因为我发现为了能尽快地完成学业,我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我甚至不得不把假期的时间也用上,来补我的数学课。
我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补习了自己以前在各门功课上的不足,跟其他同学一起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在1893年物理结业考试时,我取得了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在1894年数学的结业考试中,我也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我姐夫在后来回忆起我的这段学习经历时,曾开玩笑地说,那是“我妻妹生活中最为拼搏的一个时期”。我总是把自己这一段的生活看作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赴巴黎学习是我梦寐以求、等待了那么长时间才得到的机会,我自然备感珍惜,全副身心地投入了其中。
我与皮埃尔·居里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894年。我的同胞,弗里堡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同时还邀请了一位他很熟悉并十分敬重的巴黎年轻的物理学家。在我进到客厅里时,我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正站在一扇朝外面阳台开着的窗户前面,亮光烘托出他高高的身材,他长着赤褐色的头发和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留意到他脸上既深沉又温和的表情,和一副不太留意外部环境的神态,像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梦想家。他对我的态度质朴而又坦诚,似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初次见面之后,他还希望能再次见到我,继续就我们双方都感兴趣的科学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俩似乎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相类似的看法。
此后不久,他到学生公寓来看我,我们逐渐成为好朋友。他向我讲述整日里他进行着怎样的研究,憧憬着去过一种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生活。没过多久,他便向我提出请求,让我跟他一起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可我却不能马上下定决心;我犹豫着,因为做出这个决定将意味着我会远离我的祖国和家人。
假期到来时,我返回了波兰,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再回巴黎。然而,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得到了在巴黎工作和再次深造的机会。我进入了巴黎大学的一个物理实验室,开始进行实验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在那里,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共同的研究方向把我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直到后来我们都认为,除了彼此,我们俩谁也不可能再找到更加合适的伴侣了。于是,我俩决定结婚,在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那个时候,皮埃尔·居里刚刚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被聘为巴黎市物理化学学院物理学教授。他那一年36岁,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了。由于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到了科学研究当中,皮埃尔·居里很少再有时间顾及他的职位和待遇问题,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他住在巴黎郊区的索镇,与他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他很爱他的父母,在第一次跟我提到他们时,他用了“非常出色的”这个表达。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性格刚强、博学和受人尊重的物理学家,母亲是相夫教子的优秀典范。皮埃尔的哥哥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二人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进入这样一个值得尊重和爱戴的家庭,在那里,我受到了这家人热诚的欢迎。
我们的婚事办得十分简朴。我没有穿婚纱,婚礼上也只是邀请了几个朋友,令我高兴的是我父亲和三姐从波兰赶来,参加了我的婚礼。
我俩只求有个安静的地方能工作和生活就可以了,我们很高兴找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小房子,它的窗户外面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公婆送给了我们几件家具。我们用一个亲戚给的礼金,买了两辆自行车,闲暇时骑着它们出去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