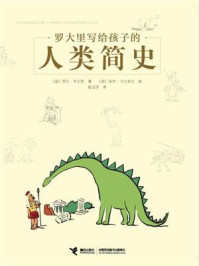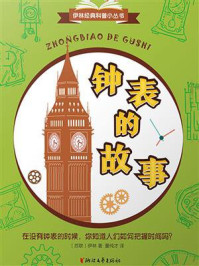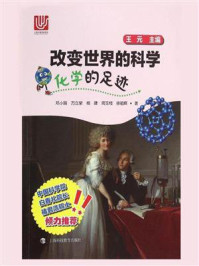观察自然,研究万物,寻找背后的普遍联系和规律,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是追求科学知识的唯一途径。
——拉马克
真正吹响号角向神秘观宣战的科学家,不是哥白尼,也不是伽利略,而是被严重低估的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他是第一个试图用严谨的逻辑把上帝拉下神坛的人。
1744年,拉马克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家中兄弟十一人,他排行垫底。年幼时家里没钱供他读书,大概他也没兴趣读书,却对战争情有独钟,曾骑着一匹老马参加过德法七年战争。根据拉马克自己的说法,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军官全部阵亡,他勇敢地接过了指挥任务,带领大家奋勇冲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段经历可能有吹牛的成分,就像所有老兵都喜爱夸大自己的战争经历一样,不过真假并不重要,反正他挺过枪林弹雨活了下来。
退伍以后,拉马克在巴黎的一家银行当上了小职员。没多久,他开始学医,四年之后辍学,转而学习植物学,并有幸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卢梭。卢梭是自然神学的支持者,经常和拉马克一起散步聊天。和哲学家聊天总是值得吹嘘的事情,他对此从不隐晦。毕竟,那是写下《忏悔录》的卢梭,又不是随便陪人吹牛的流浪汉。所以拉马克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卢梭的名字,不过也仅此而已。
拉马克兴趣广泛、不善谋生,颇有天才气质,学习了一点儿科学知识之后,特别是受到了大哲学家卢梭的开导,从此对人生天地有了新的看法。他立即制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许多计划都因为过于宏大而不可能完成,比如他想搞出一个宏观的总体理论,可以概括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本原则,解决自然科学的所有问题。当然他没有成功,但这些想法至少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这些伟大想法的激励下,拉马克不久就出版了《法国植物志》。非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科学价值的话,那就是引起了著名学者布丰的注意。
当时布丰担任法国巴黎植物园主任,身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兼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德国和俄国的科学院院士的他,具有强大的学术影响力。毫无疑问,他对植物学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布丰同样有着宏大的研究计划,他把牛顿视为偶像,准备像牛顿研究物理那样研究生物学。布丰正在编写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非常需要拉马克这样的助手,所以他为拉马克在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找了一份工作,使拉马克可以专心研究植物。而布丰的许多观点,也对拉马克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丰一度相信“自然发生论”,认为动物和植物并非上帝创造的结果,而是由自然演变而来的。他甚至认为,人也是一种动物。如果只看面孔,猿猴是人类最低级的形式,除了灵魂以外,它们拥有人类的一切器官。但受到时代的限制,布丰并没有完全摆脱神创论的影响。他只是说,如果不是《圣经》的明示,我们可能要为人和猿寻找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尽管略显含糊,仍然足够惊世骇俗,所以《自然史》于1749年刚一出版,就立即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巴黎大学神学院。他们指控布丰离经叛道,威胁要对他进行宗教制裁。布丰很聪明,他知道宗教制裁意味着什么,所以立马给神学院写了一封投降书,声明自己无意对抗《圣经》,对上帝绝对虔诚,并保证《自然史》再版时,他将把这封信刊登在卷首,以此澄清自己的立场。此后布丰就乖多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上帝,表明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在私下里,他却经常对朋友说,只要把上帝换成自然的力量,一切都名正言顺了。
如果说布丰在《自然史》中已经表达了进化论思想,可能有点儿冤枉他了,或者说是抬高了他。其实布丰的思想很奇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但不支持进化思想,反倒是支持退化思想。因为布丰并不认为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而是认为低等生物由高等生物退化而来,比如马退化而为驴,人退化而为猿猴等。这是一种奇特的观点,但如果考虑到布丰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上帝创造了人类,随后这些生物在历经自然的磨难之后,就像用久了的机器,退化是必然的结局。所以退化观是迎合自然神学的怪论。如果布丰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这些问题,或许他会取得某种突破。可惜《自然史》出版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很多知识分子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布丰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进化论的思考也戛然而止。
有人评论说,布丰一生都在进化论的边缘徘徊,可惜他缺少向进化论发起最后冲刺的运气。其实不是运气或勇气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知识积累尚不足以支撑布丰发起最后的冲刺。不过他已经为进化论思想培养了一位优秀的接班人,那就是拉马克。
拉马克要比布丰幸运,他的肉体不但在大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他还被革命者拉去撑门面,做起了新政府的动物学教授,具体工作是研究蠕虫。就这样,植物学家拉马克转而开始研究动物。当时他已年近五十,仍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并且爆发出了惊人的研究能力,让动物学界大吃一惊,并于1783年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拉马克对“蠕虫”这个名称并不满意,于是他首次把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把所有蠕虫都归入无脊椎动物名下,与脊椎动物平起平坐,相关研究自然也提升了一个档次。
拉马克很快发现,无脊椎动物其实很有趣,它们不但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事实上是研究进化论的极佳样本。他从乱七八糟的无脊椎动物种类中看出了物种变化的总体趋势,尽管不甚明朗,但总体方向绝对没错。为此,拉马克在1800年给学生上课时,已经修改了自己的讲义,不再说生物是不变的,而是明确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只不过还缺少有力的证据。
正巧当时博物馆有一位研究人员去世了,把自己收集的各种软体动物化石都留给了拉马克。拉马克在研究这些遗物的时候,对软体动物化石进行了认真归类,意外发现了一条变化规律,那些化石与现存的软体动物极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其中可以排出一条线性的进化关系。这让拉马克认识到,动物可能处于变化之中,而不是如神创论宣传的那样永久不变。当时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完全是替上帝着想的结果——上帝不可能不厌其烦地创造出如此名目繁杂的小动物来。
1809年,拉马克出版了《动物学哲学》,开始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想法。他在书中详细讨论了动物的分类与进化过程,完整地提出了进化理论,那就是著名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在拉马克的理论体系中,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相辅相成,没有用进废退,就没有所谓的获得性,当然也就无从遗传。用进废退的思想明确指出物种可变,可以“进”,也可以“退”,这和神创论坚持的物种不变观点产生了直接的矛盾。拉马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宗教势力烧死,所以采取了聪明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他没有集中提出明确的观点,而是分散零碎地表述了某种思想,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抓不住重点,自然也就可以让自己免遭不必要的攻击。
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总结拉马克的观点。简而言之,拉马克认为,生物会对环境做出反应,这就是用进废退。随着环境的持续影响,生物习性也会随之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会遗传下去,这就是获得性遗传。
支持拉马克理论最好的证据是长颈鹿。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如果戴围巾,需要好几米的布料才行。如此特别的性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拉马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答了另一个问题:长颈鹿的脖子是怎么长那么长的。
在拉马克看来,长颈鹿原本是矮个子,因为低处的树叶不够吃,或者抢不过别的动物,矮颈鹿的祖先不得不拼命伸长脖子去吃更高的树叶,结果脖子越伸越长,终于变成现在这么长。这就是“用进”。
此外还有“废退”的例子,比如裸鼹鼠的眼睛。
裸鼹鼠长年生活在地下洞穴中,各种器官从头到脚,基本都适应了地下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眼睛,成年以后就深深陷在皮肤下面,视力完全退化。如果裸鼹鼠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就会因为光线刺激而造成神经紊乱,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因为没有光线,所以视力退化,这就是典型的“废退”。
从表面上看来,“用进废退”的例子到处皆是,比如深海鱼类因为长年不见阳光,所以眼睛都退化了。鸵鸟的腿因为经常跪在滚烫的沙漠上,膝盖上长出了厚厚的胼胝质,也就是老茧。而令人惊奇的是,还在卵中没有出壳的小鸵鸟腿上也有胼胝质,所以这被看作是支持拉马克理论的重要证据,证明后天获得的性状似乎真的可以遗传下去。
正因为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与人们的直观印象一致,显得特别容易理解,因而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直到现在,生物老师还在非常费力地解释拉马克的理论为什么错了,而学生依然表示无法接受。下文中我们会深度分析麻烦出在哪里。
拉马克根据自己的理论,强烈反对物种概念。他认为物种只是人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物种。根据用进废退理论,所有的生物都处于连续的变化之中。物种之所以看上去独自成形,与其他物种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因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标本来填补物种与物种之间的链条。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必定存在着介于两个物种之间的模棱两可的动物。当所有物种收集齐备以后,就可以看出生物界是由一连串过渡形态的生物组成的进化链条。
反对物种概念的不只是拉马克,布丰也持同样的看法。但布丰和拉马克的逻辑不同,他只是简单地认为物种就是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体。无论哪种动物,每个个体都和其他个体不一样,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狗,也没有两只完全相同的猫。所有生物都会因环境、气候、营养的改变而改变。为此布丰猛烈抨击了林奈的分类学,因为分类学完全建立在物种概念之上。布丰认为,林奈除了给动植物起名字,其他什么都不懂。拉马克无疑受到了布丰的强烈影响,然后又影响了其他人。直到现在,仍有生物学家认为物种确实不存在,那只是人为研究的需要,而不是自然的本质。
拉马克认为,既然所有物种都处于连续变化之中,那就无所谓灭绝。根据他的推理,所有物种都没有灭绝,它们只不过是从一个物种转变成了另一个物种而已。而物种不灭的观点事实上为神创论解决了一个难题——如果许多动物都灭绝了,那为什么现在仍然存在大量动物种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灭绝的动物越来越多,现存的动物应该非常少才对啊。为了解释这一难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上帝并没有休息,而是一直在创造新的物种;二是上帝确实休息了,那些新的物种其实是由旧的物种进化而来的。拉马克的方案,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动物消失了,而有的动物在不断涌现,因为物种之间可以自行替换。如此一来,上帝就可以安然享受闲暇的时光了。
尽管拉马克花费了较大精力推广自己的理论,但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布丰已经不在人世,拉马克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还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反对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动物学家居维叶。特别是在拉马克死后,他遭到了居维叶的无情攻击和打压,并直接导致拉马克的理论被彻底埋没。
居维叶是与布丰齐名的科学天才,自小家庭富裕,受到过良好的科学教育,四岁就能读书,过目不忘,世称神童。他十四岁进大学,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加上天生的学习热情,十八岁就已名声在外,年纪轻轻就已出任诺曼底大学助教,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开创了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动物分类学等研究领域。同时,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拿破仑关系密切,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
与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居维叶同样信奉自然神学,他研究生物不是为了推翻《圣经》,而是相反。他的基本思想与《圣经》高度一致,比如居维叶坚信,所有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成不变,就算大量出土的动物化石,也没能改变他的看法。
当时巴黎因为市政建设的需要开辟了许多采石场,意外挖出了大量化石。居维叶受政府委派,对采石场化石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发现采石场的地层可以分为五层,每一层的化石都不相同,其中最上层是淡水动植物化石,第二层以海洋贝壳类生物为主,第三层又是淡水生物,第四层又是海洋生物,最下面一层,也就是第五层,则包含淡水贝壳类化石。通过如此复杂的化石分层现象,居维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巴黎地区曾经数次被海水淹没,当地所有陆生生物都灭绝了。海水退去后,淡水生物才得以重新归来。数度反复,才出现了如此奇特的地层化石结构。根据这个判断,居维叶提出了著名的“灾变论”,也就是说,在地球历史上曾经周期性地出现大灾难,因而造成了生物种类的大更迭。
居维叶通过对化石的分析,判断乳齿象和猛犸象等大型动物都已灭绝,低等动物的灭绝数量更是惊人,这是科学界第一次承认动物灭绝。为了捍卫《圣经》的权威,居维叶必须给生物灭绝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于天才的居维叶来说,此事并不困难,因为他还发现,不同地质层面的化石明显呈现不断复杂化的趋势,最底层只有原始的腔肠动物化石,上层则出现了鱼类等脊椎动物,直到最上层,才出现了哺乳动物。如果居维叶根据这些化石线索进一步思考,就可能得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可惜的是,受到自然神学的影响,居维叶就此止步。他仍然坚信物种不变论,并对那些化石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生物确实在灭绝,而低等生物的灭绝,恰恰是为了给高等生物腾出空间来。直到五千年前的那次大洪水,也就是最后一次大洪水,是上帝在清空舞台,为人类上场做准备。
居维叶还发现,埃及木乃伊的骨架和现代人完全相同,这让他深信,物种在四千年内确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既然如此,进化当然无从谈起。
居维叶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满意,因为在“灾变论”与“物种不变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自洽——既然物种不会变,当然不会从低等生物变成高等生物,那么低等生物只能灭绝,而大灾难正好能造成大灭绝。两者相互需要,一拍即合。所以在今天看来,居维叶的结论虽然不可思议,但在自然神学的范畴内其实非常合理。他所倡导的灾变论也成为神创论的重要理论工具,后来与进化论开展了漫长的论战,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而与巴黎科学院另一位重要学者圣提雷尔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坚定了居维叶的信念,导致他在背离进化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圣提雷尔是布丰的学生,同时也是拉马克的好友,早年受过教会教育,不久转攻博物学,成为法国著名的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二十一岁时已成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而当时的居维叶还籍籍无名。为了能到巴黎工作,居维叶曾特意将自己的论文整理后寄给了圣提雷尔,请他指导。圣提雷尔对居维叶的研究非常欣赏,于是向博物馆大力推荐,并将自己的很多标本送给居维叶研究,其中包括圣提雷尔亲自跟随拿破仑从埃及带回的木乃伊。从这种意义上说,圣提雷尔甚至可以说是居维叶的科学引路人。此后,居维叶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拉马克和圣提雷尔成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三巨头。
与拉马克一样,圣提雷尔受到布丰思想的强烈影响,也主张物种可变,因而在此问题上与居维叶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生物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由于坚信物种不变,居维叶推断:生物的所有结构都对应特定的功能,即所谓一物一用。什么样的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比如心脏用于输送血液、肺腑用于呼吸等。所有这些结构都绝对精确,没有无用的器官,也没有退化的器官,因为所有器官都出自上帝之手。上帝不可能造无用的器官,更不可能让器官半途退化。正因为所有器官都执行某种特定的功能,所以整个生物体才会适应环境。就像钟表要想正常运行,其中的每个零件都需要有自己的功能一样,没有哪个零件可以随手扔掉。
圣提雷尔根据物种可变的原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大自然原本给所有动物都配置了相同功能的器官,并且数量相等。只是由于不同的环境会对生物造成不同的影响,这样才有了动物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生物结构的功能也是可变的,否则无法应对变化的环境。圣提雷尔甚至认为节肢动物的分节附肢和脊椎动物的分节脊椎源自同一种结构,它们原本都有相同的功能。他据此提出了“同功器官”的概念,和现在通行的“同源器官”概念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指结构不同但功能相同的器官。由此可见,圣提雷尔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由于圣提雷尔与居维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终于发展为公开的论战,那就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论战,论战的焦点正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1830年2月15日,在法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圣提雷尔当众宣读了自己学生的论文,对比了头足动物与脊椎动物的解剖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乌贼和狗的解剖结构,并认为两者有相同的基本设计。圣提雷尔以论文为切入点,向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论文中谈到的脊椎动物具有同一结构的观点,与自己一贯的见解相符:有的结构可以有多种功能,比如鲸鱼的前肢与人类的前肢,虽然结构相同,但功能完全不同;而有些不同的结构,可以完成相同的功能,比如蝙蝠的翼手和鸟类的翅膀,都具有飞行的功能。而且圣提雷尔认为有些器官的功能已经退化,似乎并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既然如此,在结构与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但圣提雷尔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他居然认为所有动物都来自一个统一的结构,甚至认为节肢动物的外骨骼与脊椎动物的骨骼和肋骨相当。在此基础上,圣提雷尔做出了一个重大假设: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有相同的起源。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甚至是进化论的基础,但当时圣提雷尔没有占得先机,因为他的观点超出了当时的理解能力。普通听众很难理解,一只猫怎么可能和蜈蚣有着相同的起源呢?圣提雷尔有苦说不出,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细胞与基因理论的支持,具体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同的生物会有相同的起源。他只能强调思想的作用,也就是从内在的逻辑出发,推导出这个结果,但推导过程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遭到了居维叶的强力反击。
居维叶早就把动物界分为四大类。一切动物都可归属于四大门类,彼此没有先后之分,都是上帝创造的结果。既然如此,各大门类各安其位,并不存在谁进化成谁的问题。基于这个逻辑,居维叶对圣提雷尔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反击。那是一场漫长的论战。法国科学院大厅内常常座无虚席,大家都在聆听两位科学家的口水仗,就像观看话剧一样津津有味。
直到1832年5月13日,巴黎科学院论战才告一段落,因为那天居维叶去世了,科学院也因此而宣布居维叶胜出,毕竟他的观点更符合《圣经》的主张。居维叶的胜利虽然压制了圣提雷尔,更大的影响却落在了拉马克头上。因为物种不变论和物种可变论是一对不可调和的死敌。
居维叶原本曾一度支持拉马克的想法,但在宗教势力的高压下,他聪明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与拉马克彻底决裂。
当初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出版时,立即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巴黎大主教从中读出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亲自去找拿破仑,要求对拉马克予以严厉制裁。拿破仑把此事交给居维叶处理,希望拉马克能像布丰那样,公开声明自己无意亵渎上帝和《圣经》,并收回一切与《圣经》相违背的言论。
居维叶按照拿破仑的指示去找拉马克,他暗示拉马克,如果不做让步,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拉马克一口回绝了居维叶,他拒绝因为宗教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科学原则。居维叶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到拿破仑面前添油加醋地评论了一番。拿破仑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法国大学管理部门将拉马克除名,同时停止其所享受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的一切待遇。居维叶为了迎合拿破仑,对拉马克的进化理论竭尽嘲笑之能事,指责拉马克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受居维叶的影响,当时一大批学者都对拉马克展开了无情的攻击。在他们眼里,拉马克无疑是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小丑。拉马克因此身败名裂。
1809年冬天,拉马克心情落寞地离开了科学院,和小女儿搬到巴黎东郊的平民区居住,依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甚至双目失明,百病缠身。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而是借助女儿的笔录坚持写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他对自己的遭遇并没有感到后悔,曾说:“科学让人受益匪浅,还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纯洁,以弥补生命中不能避免的苦难。”
1829年12月8日,拉马克在巴黎与世长辞,享年85岁,遗骸被埋葬在蒙巴纳斯的公墓。他生前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的动物学或植物学研究,而是关注他的进化论。可惜这个心愿被他带进了坟墓。
尽管如此,拉马克并没有被后人彻底遗忘,现在已经被看作是进化论的先驱之一。虽然生前寂寥,死后却拥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法国人,正像研究达尔文那样研究拉马克,并期待他的进化理论能够重放光芒。在拉马克身上,寄托着法国智慧战胜英国智慧的希望。
1909年,英国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50周年的时候,法国人也举办了纪念拉马克165周年诞辰的活动,同时纪念《动物学哲学》出版100周年。人们在拉马克工作过的巴黎植物园竖起一座半身塑像,底座上写着一行字:进化论的创始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拉马克的理论比达尔文的理论还要流行,因为“用进废退”的观点很容易理解,因而很容易被接受。拉马克强调目的就是动力,甚至“欲望”和“意志”也能推动生物的进化,比如长颈鹿特别想把脖子长长一点儿,于是真的就长长了,这就是“意志”的力量。至于意志最终来自何方,拉马克只好归功于上帝。他同样没有彻底摆脱自然神学的影响。不过人文学者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希望拉马克是正确的,如此一来,坚定的意志就能引导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甚至是天堂。意志靠什么起作用,却是人文学者无法回答的难题。
至此拉马克已经完成了铺路者的任务,他扣动了科学对战宗教的扳机,但并没有打响。枪是好枪,却打出了哑弹。
真正扣动扳机并射中要害的,是达尔文。
当拉马克在法国凄然离世时,达尔文已经准备乘船出海了。
一次伟大的航程即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