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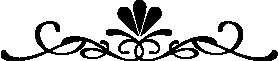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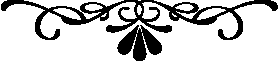
有些人会认为变异是偶然发生的——家养状态下的生物变异是普遍且多样的,而在自然状态下相对较少。显然,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但却说明我们对引发各类特殊变异的原因毫无所知。一些学者认为,生殖系统的机能使个体产生差异或使结构上产生非常细微的变化,正如父母与孩子之间一样。与自然条件下相比,在家养条件下出现的变异和畸形的状况更加频繁,而且分布广的物种要比分布狭窄的物种的变异性更大。由此可知,变异性通常与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关。我已经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环境变化以两种方式产生作用,一种是对生物体的部分或整体直接地发生作用,一种是通过生殖系统间接地发生作用。在生物界中,有两种引起变异的因素,一种是生物本身,另一种是外界环境,前者的作用更为显著。外部条件的改变会直接产生定向或者不定向变异。在不定变异中,生物体处于可塑状态,其变异性往往很不稳定。而在定向变异中,生物可以适应一定的环境,并且使所有个体或大多数个体通过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异。
气候、食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对生物变异产生多少直接影响,是很难确定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时间的推移中,我们会发现,环境的作用产生的实际效果,比事实能证明的效果要更大。另外,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自然界中各类生物间看到的无数构造复杂的相互适应,绝不能单纯地归纳为外界环境的作用。以下几种情况中,外部条件似乎产生了一些细微的效果:福布斯自信地说,比起更北部或更深处的同一物种的贝壳,位于南端的以及生活在浅水中的贝壳的颜色更鲜艳,但也不是全都如此;古尔德认为,与在岛上或海岸附近生活的鸟相比,生长在陆地空旷大气中的同一种鸟的颜色更鲜艳;同样,对于昆虫来说,沃拉斯顿深信海滨环境会影响它们的颜色;穆根-唐顿曾列出一大串植物,证明生长在近海岸的植物,其叶片肉质比生长在别处的更肥厚。这些奇特的现象体现了生物的定向性,即同样环境条件下生活的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常常具有相似的特征。
当变异对生物作用不大时,我们很难确定其中多少归因于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多少归因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同物种的动物生活的地区越靠北,它们的毛皮就越厚实。但是,谁又能说清楚,这种皮毛上的差异,有多少是基于毛皮最温暖的个体对有利变异的累积,又有多少是基于寒冷气候的影响呢?因为气候似乎直接影响了家畜的皮毛。
许多实例都能表明,同一物种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产生相似的变种;也有一些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生活的物种,却不会产生相似的变种。另外,每个博物学家都知道,有些物种生活在极端相反的气候条件下仍能保持纯种或根本不发生变异。这些事实让我意识到,相较于周围环境对变异的直接影响,某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原因引发的生物本身的变异倾向反而更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环境可以决定哪个变种可以生存下去,生活环境不仅能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变异,同样也能对生物进行自然选择。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人类进行选择时,上述两种变异的差别很明显;人工选择通常是选择已经发生的变异,再按照人类的意志使其朝着一定方向累积;后一作用就与自然状况下适者生存的作用一致。
从第一章提到的事实来看,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家畜经常使用的器官会更强大,而不使用则会退化;并且这类变化是可以遗传的。在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比较标准来判断长期连续使用或不使用的效果,因为我们不知道祖先的类型;但是许多动物的结构都可以通过不常使用而退化来解释。正如欧文教授所说,自然界中没有比不能飞的鸟更奇怪的现象了;但有几种鸟确实是处于这种状态的。南美洲大头鸭只能在水面上拍打它的翅膀,这几乎与家养的艾尔斯伯里鸭一样。坎宁安先生说,这种鸭在年幼时是会飞的,长大后就失去了这种能力。因为在地上觅食的体型较大的鸟,除了逃避危险之外,很少用到翅膀。因此我相信,现在或者不久之前在海岛上生活的几种鸟类,翅膀都不发达,可能是因为海岛上没有天敌,所以它们很少使用翅膀而退化了。鸵鸟确实栖息在大陆上,并处于危险之中,无法通过飞行逃避危险,但是可以通过爪子来防御敌人,就像那些四足兽类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鸵鸟祖先和鸨类有相似的习性,但是在连续世代中,鸵鸟的体积和体重不断增大,爪子使用得比较多,而翅膀使用得比较少,最后就无法飞翔了。
柯比曾指出(我也观察到了相同的事实),许多雄性食粪蜣螂的前足跗节经常折断。他检查了自己收藏的17个标本,发现没有一个留有前足跗节的痕迹。有一种蜣螂,由于其前足跗节常常断掉,以至于被描述为不具有跗节了。其他属的一些个体虽然有跗节,但也发育得不完全。被埃及人奉为神圣的甲虫蜣螂,其跗节也是发育不良的。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偶然的损伤是否会遗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布朗西卡观察到的事实:豚鼠手术后的特征可以遗传。因此,蜣螂前足跗节的缺失或发育不良,并不是肢体残缺的遗传,最恰当的解释是由于长期不使用造成的退化。因为许多食粪类的蜣螂,失去跗节都发生在生命的早期,所以这类昆虫的跗节应是一种不太重要或不经常使用的器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全部或者主要由自然选择引起的构造变异,当作不使用的缘故。沃拉斯顿先生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居住在马德拉岛的550种甲虫中,有200种甲虫的翅膀是残缺的,因而无法飞行。在当地29个特有属中,至少有23个属的物种与之类似!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甲虫经常被吹到海上而死亡;沃拉斯顿先生观察到,马德拉岛的甲虫隐藏得很好,只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才出来;在没有遮蔽的德塞塔什岛,无翅甲虫的比例比马德拉群岛上的大;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实,沃拉斯顿先生对此非常重视,即在其他地区非常多的必须使用翅膀飞翔的甲虫,在马德拉群岛几乎没有看见。以上几个事实使我相信,如此多的马德拉甲虫出现无翅的状况,主要是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以及长期不使用造成的退化。翅膀退化了的甲虫,由于丧失了飞行能力,可以避免被风吹向大海;另一方面,那些会飞行的甲虫通常会被吹到海里,因此被灭绝了。
马德拉群岛有些昆虫不在地面觅食,比如以花朵为食的鞘翅目昆虫和鳞翅目昆虫,它们必须使用翅膀来维持生存。正如沃拉斯顿先生猜测的那样,它们的翅膀根本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大,这与自然选择的作用是相符合的。因为当新昆虫来到岛上时,自然选择增大或减小翅膀的趋势,取决于大多数个体是通过战胜海风来生存,还是通过少飞或者不会来生存。
鼹鼠和若干穴居啮齿类动物的眼睛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被皮毛遮盖住。眼睛的这种状态可能是由于不使用而逐渐退化,但也许自然选择也发挥了作用。在南美,有一种啮齿类动物栉鼠,它的穴居习性比鼹鼠更强。经常抓到它们的西班牙人告诉我,它们的眼睛通常都是瞎的。我曾经保存过一个活的此类动物,它的眼睛确实是这样,通过解剖显示,它眼睛会瞎的原因是瞬膜发炎。对于任何动物来说,频繁地发炎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然而,眼睛肯定不是生活在地下的动物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眼睛变小、上下眼睑粘连,而且有毛长在上面,对这类动物来说可能是有利的。这样的话,自然选择就会对不使用的器官产生作用了。
众所周知,生活在卡尼俄拉和肯塔基的几种穴居动物,虽然分属几个截然不同的纲,但是它们的眼睛都是瞎的。有一些螃蟹,尽管眼睛消失了,眼柄却仍然存在,就像望远镜失去了玻璃片而镜架却依然存在的情形。很难想象,尽管眼睛没有用,也不会对生活在黑暗中的动物造成任何伤害,所以我将眼睛退化的原因归结于不使用。有一种失明的动物洞鼠,西利曼教授在距洞口约800米(半英里)的地方(并非洞穴最深处)捕捉到两只洞鼠,它们的眼睛大而有光。西利曼教授告诉我,当这两只洞鼠在逐渐加强光线的环境中生活大约一个月以后,就可以蒙眬地看见周围环境了。
很难想象,还有与石灰岩深洞相似的生活环境。从普遍的观点来看,瞎眼动物来自美洲和欧洲的山洞,可以预料这些动物在构造和亲缘关系上应该非常接近。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两处洞穴内的动物,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仅就昆虫而言,喜华德说,“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地方性眼光来观察这些现象,马摩斯洞和卡尼俄拉各洞虽有少数相似的动物,但仅仅能表明欧洲与北美动物群之间存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已。”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假设,具有正常视力的美洲动物,数代从外部世界慢慢迁移到肯塔基州洞穴越来越深的地方,正如欧洲动物也迁入了欧洲的洞穴一样。这种习性的慢慢改变,我们也有一些证据。正如喜华德所说:“那些在地下生活的动物,我们将其看作受邻近地方地理限制的动物群的小分支。一旦它们迁入地下,在黑暗中生活,就逐渐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但是刚转入地下生活的动物,与原动物群差异很小。它们首先要适应光明到黑暗的过渡,然后再慢慢适应微弱的光线,到最后完全适应黑暗环境,它们的构造也会变化。” 我们应该认识到,喜华德的这些话是针对不同物种,并非同一物种。当一种动物经过若干代迁移到地下最深处生活时,眼睛由于不使用,会或多或少地退化,而自然选择通常会影响其他构造的变化,例如增长的触角或者触须,用以补偿失去的视觉。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们仍能看到,美洲大陆动物和穴居动物、欧洲大陆动物和穴居动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正如我从达纳教授那里听到的那样,某些美洲洞穴动物就是这种情况。一些欧洲洞穴昆虫与周围地区的昆虫息息相关。如果用上帝独力创造的观点看待两大洲上瞎眼的穴居动物与大洲上其他生物的亲缘关系,就无法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了。两大洲几种穴居动物的关系应当是相当密切的,我们可以从欧美两大陆上一般生物间的关系推测出这一点。有一种叫盲目埋葬虫的生物,它们大多数生活在离洞穴很远的阴暗岩石上。因此,该属内穴居动物视觉器官的消失,似乎与黑暗环境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的视觉器官早已退化,更容易适应穴居生活。墨雷先生曾观察到,盲步行属也具有这种显著的特征,该属昆虫除穴居之外,尚未在其他地方被发现过。但是生活在欧洲和美洲某些洞穴里的物种却与此不同,可能是这些动物的祖先在丧失视觉之前,在两个大陆上分布较广泛。不过那些在大陆上生活的都已经灭绝了,只留下了隐居在洞穴里的。某些穴居动物应该非常独特,但是这丝毫没有让人感到惊讶,如阿加西斯提到过的盲鱼以及欧洲的爬行动物盲螈(现在已将其划分为两栖类)。唯一令我惊讶的,也许是由于这些在黑暗中生活的生物个体不多,彼此间生存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因此没有保留太多的古代生物残骸。
植物的习性能够遗传,例如开花期、休眠期、种子发芽所需的雨水量等,这使我不得不说一些气候驯化的问题。同一属的物种居住在非常炎热和非常寒冷的地区的情况都非常普遍,如果同一属的所有物种都来自同一个亲种,那么在长期繁衍的过程中,气候驯化必定会发生作用。众所周知,每个物种都可以适应本土的气候,但是寒带或温带地区的物种却不能适应热带气候,相反也是如此。同样,许多肉质植物不能忍受潮湿的气候。但是,人们常常高估了某些物种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可以从以下事实推测出来:我们往往无法预测新引进植物是否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我们也无法预知,从不同地区引进的动植物,能否在这里健康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自然环境下,物种之间的生存斗争限制了它们的地理范围。这种生存斗争类似于物种对特殊气候的适应性,前者的作用或许更大些。尽管生物只能适应一定的生存环境,但对于少数几种植物,有证据表明它们能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即气候驯化。胡克博士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不同高度采集到同种松树和杜鹃花的种子,在英国种植后,发现它们的抗寒能力不同。思韦兹先生告诉我,他在锡兰岛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沃森先生对从亚速尔群岛带到英国的欧洲植物进行了观察,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列举一些别的例子。关于动物,也可以给出几个真实的案例:在某些历史时期内,一些物种的生存范围曾经从较暖的低纬度地区迁移到了较冷的高纬度地区,反之亦然。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动物是否严格适应了本土的气候,我们也不了解这些动物在迁移之后是否能适应新环境。
我相信家畜最初是由未开化人驯养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而是因为它们非常有用,并且在家养的条件下易于繁殖。家养动物不仅能够适应不同的气候,还可以在这样的气候下繁育。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现在生活在自然环境下的动物,很多类型都可以适应各种气候环境。但是,由于某些家畜可能来自几种野生种群,我们决不能将上述观点推得太远。例如,热带狼和寒带狼的血统可能混入了家养犬中。老鼠和鼹鼠不能被视为家畜,但它们是由人带到世界各地的。而现在,与其他啮齿类动物相比,它们的分布范围要广得多。它们既能生活在北方法罗群岛寒冷的地区,也能在南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热带的许多岛屿上生活。因此我认为,适应任何特殊的气候是大多数动物共有的能力。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和家养动物都具有能够忍耐不同气候的能力。例如已经灭绝的大象和犀牛能够忍受冰川气候,而现存的种类都属于热带或亚热带生物。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异常,这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表现出适应性的例子。
一个物种对任何特殊气候的适应程度,有多少是由习性造成的,又有多少取决于对具有不同构造的变种的选择作用,抑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我们很难弄清楚。无论是通过类推,还是通过许多农业著作和中国古代书籍中提出的建议,我们都可以知道,在将动物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时要非常谨慎。因此,我必须相信习性会对生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人类不太可能成功地挑选出如此多的特别适应其所在地区环境的品种和亚品种;我认为这一定是由于习性的原因。另一方面,我没有理由怀疑,自然选择将继续保存那些天生最能适应居住环境的个体。在关于多种栽培植物的论文中记载,某些变种比其他变种更能适应某些气候。这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果树的著作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某些变种建议种植在北方,而南方则建议种植其他变种。并且由于这些变种中的大多数是近代培育出来的,因此不会因为习性上的不同而影响它们体质上的差异。菊芋曾经被举例为气候驯化对物种无用的证据,在英国,菊芋从来没有通过种子繁殖过,因此不能产生新的变种,至今它们的植株都很柔弱。也有人以菜豆为例,而且更具有说服力。但是除非按照下面的方法做过,否则不能说他曾做过这个实验:首先要提早播种菜豆,让霜冻破坏大部分植株,然后从少数幸存的菜豆中收集种子;然后再以相同的方式种植;要一直留意不能出现杂交的情况,如此循环往复;经过二十代后,连续的种植才算完成了。我们无法确定菜豆的幼苗本身是否有差异,因为已经有报道说,有些幼苗看上去比其他幼苗更耐寒,我也曾亲眼见过这类明显的事例。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生物的习性和器官的用进废退,在生物体构成和各种器官结构的变异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用进废退通常与自然选择结合在一起,有时甚至被自然选择控制。
相关变异是指生物的各部分在成长和发育过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任何一个部分发生细微变异并通过自然选择而积累时,其他部分也会发生变异。相关变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充分,并且常常和其他事实混淆。下面,我将谈到遗传常常表现出的相关变异的假象。最明显的情况是,仅仅为动物幼体或幼虫的利益而积累的变异将影响成体的结构。在动物胚胎早期,由于身体上一些构造相同,所处环境又大致雷同,似乎最容易发生相同的变异。例如,在身体的左右两侧发生同样的变异;前腿和后腿,甚至下颚和四肢,都同时发生了变异,因为某些解剖学家认为,下颚与四肢是属于同源构造。我毫不怀疑,这些趋势或多或少地受自然选择的控制。曾经有一群鹿,鹿角仅长在一侧;如果这对鹿有很大的用处,那么它可能会由于自然选择而永久保留下来。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同源部分趋向于结合。这一点在畸形植物中经常见到。在正常构造中,花瓣的管状结合是一种极常见的同源器官结合。生物中坚硬的部分似乎能影响相邻的柔软部分的形态。一些作者认为,鸟类骨盆形状的多样性会导致其肾脏形状的显著差异。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压力的原因,人类母亲的骨盆形状会影响婴儿的头部形状。据施莱格尔说,蛇类身体的形状和吞咽方式决定了最重要器官的位置和形状。
这种相关变异的性质通常非常模糊。小圣提雷尔曾强调指出,我们还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畸形构造常常共存,而有些却很少共存。例如,白猫的蓝眼睛和耳聋之间的关系;猫的玳瑁色和雌性之间的关系;鸽子足上的羽毛外趾间蹼皮的关系;幼鸽绒毛的多少与将来羽毛的颜色之间的关系;还有,土耳其裸犬的毛与其齿之间的关系。在上述这些奇特的关系中,同源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最后那种情况,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因为哺乳动物中皮肤特别的鲸目与贫齿目都长有最异常的牙齿。可是,正如米瓦特先生所说,这一规律存在许多例外,因此它的适用范围很小。
据我所知,菊科和伞形科植物在花序上内外花的差异更适合阐明相关变异规则的重要性,而与用进废退及自然选择作用无关。我们都知道,雏菊的中央花与边花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往往伴随着生殖器官的部分或完全退化。但是,在这类植物中,有些种子的形态和纹路也有差别,一些学者将这些差异归因于总苞对边花的压力,或者它们彼此之间的压力,而一些菊科植物边花种子的形状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胡克博士告诉我的那样,就伞形科的花冠而言,花序最密的物种中,内花和外花出现的差异最大。也许有人认为,边花的发育需要生殖器官输送养料,这样就会造成生殖器官发育不良。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某些菊科植物中,外部和内部小花的种子有所不同,但花冠却没有任何差异。可能这些差异与养料流向中心花和边花的多少有关。至少我们知道,在不规则的花簇中,最靠近轴的花朵通常最整齐。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相关变异的实例:在许多天竺葵属的植物中,当花序的中央花上方两片花瓣失去浓色的斑点时,所附着的蜜腺就会完全退化;如果只有其中一瓣失去斑点,那么所附着的蜜腺就会缩短,但不会退化。
斯普兰格尔先生对于花冠发育的观点是可信的。他认为,边花的主要作用是引诱昆虫,这对植物的受精是有利且必需的。假如是这样的话,自然选择可能已经发挥作用了。但是,就种子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上的差异而言,这些差异并不总是与花冠的差异相关联,似乎它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植物有利。然而,在伞形科中,这些差异非常重要。根据老德康多尔先生的说法,该科植物的种子中有在外花直生而在内花弯曲的,他以这些特征作为该科植物的主要分类标准。因此,有些构造变化分类学家认为很有价值,这些变化可能完全受变异和相关法则的支配。而据我们判断,这对物种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可能经常错误地将一群物种共有的、遗传下来的构造,当成相关变异所致。因为它们的祖先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了某种结构上的变异,并且经过几千代的发展,又有了一些不相关的变异。如果这两种变异已经遗传给具有不同习性的全部后代,自然会被认为它们在某些方面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我毫不怀疑,其他相关变异的例子完全是由于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例如,德康多尔指出,不开裂的果实里面从未发现过具翼的种子。我这样解释这个现象:除非果实是裂开的,否则种子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渐长翼。只有果实开裂需要风来传播种子时,能够被风吹起的种子才相对具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老圣提雷尔和歌德在同时期提出了生长补偿法则或生长平衡法则;如歌德所言,“为了某一方面的花费,自然不得不在另一方面节约”。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家养物种:如果营养过多地流向某个部位或器官,那么流向另一部位或器官的营养就至少不会过量。因此,很难让一头奶牛既产很多牛奶,同时身体又很肥胖。同一颗甘蓝变种,不能既长出茂盛而有营养的叶子,又结出大量的含油种子。当果实中的种子萎缩时,果实本身的大小和品质就会大大提高。而在家鸡中,头上有大丛毛冠的往往都长有瘦小的肉冠,而那些颚须多的家鸡,通常肉垂会很小。如果物种处于自然状态,生长补偿法则很难普遍适用。但是许多优秀的观察者,尤其是植物学家,都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不会在这里给出任何实例,因为我没有方法区分:哪一构造只是由于自然选择作用而发达的,而另一相关构造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或者不使用而退化的;也难弄清楚某一构造的过度生长是因为它剥夺了相邻部分的营养。
我认为已经提出的补偿实例以及其他一些事实,都可以归纳在一个更普遍的原则中,即自然选择一直在努力节约生物体的每个部分。如果生存条件发生改变,一些之前有用的构造可能变得不那么有用了,这个构造就会缩小,这对生物个体是有利的,不会浪费其营养来建设无用的构造。因此,我才能理解当初观察蔓足类时曾令我震惊的事实:当一种蔓足类寄生在另一蔓足类体内,并因此得到保护时,它的外壳或背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雄性四甲石砌属个体就是这样,寄生石砌属更是如此。其他蔓足类都具有极其发达的背甲,它是由头部前端三个重要的体节组成的,并且具有巨大的神经和肌肉。而那些因寄生而被保护的石砌属,头的前部明显退化了,仅在触角基部留有痕迹。如果节省了不用的大型复杂构造,对于每个物种的后代来说,绝对是有利的。因为在每个动物面临的生存斗争中,它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必须减少营养的浪费。
因此,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当身体的任何构造变得多余时,自然选择作用都会使它缩小,但不会引起其他构造的相应增大。反之,自然选择可以促使任何器官增大,而无须缩小某些毗邻部分作为必要的补偿。
正如小圣提雷尔所说,在物种和变种中,如果将同一个体的任何构造或器官(如蛇的脊椎骨、多雄蕊花中的雄蕊等)重复多次,它重复的次数就容易变异;相反的,同样的构造或器官,如果重复器官较少,就更具有稳定性,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了。小圣提雷尔和一些植物学家进一步指出,重复的器官,在构造上也非常容易发生变异。这正是欧文教授所说的“生长的重复”,并且他认为这是低等生物的标志。上述观点似乎与博物学家的普遍看法是一致的,即在自然界中,低等生物比高等生物更容易发生变异。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低级是指生物的一些构造很少专门用于某种特殊功能。只要同一构造必须实现多种功能,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为什么它容易发生变异,因为自然选择对这种器官比对专营一特殊功能的器官宽松。就好比一把有各种用途的刀,可以是各种形状;但是有特殊用途的刀,通常形状都是特定的。永远不要忘记,自然选择只在对生物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
一般学者认为,退化的构造容易产生高度变异,以后我们会对这个论题进行讨论。我在这里仅做一点补充,它们的变异似乎是由于其无用性引起的,因此自然选择无法对这些变异发挥作用。
几年前,沃特豪斯关于发育异常的构造容易发生变异的说法曾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欧文教授也观察并推断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了使人们相信上述结论的真实性,我必须列举出我搜集到的一系列事实,但无法在这里列出一长串实例。我只能说,这个观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可能有种种原因导致错误的发生,但是我希望我已经避免了所有能想到的错误。应该了解的是,该规律绝不适用于任何生物构造,只有在比较近缘物种的同一构造时,发育异常的构造才适用于这一规律。例如,蝙蝠的翅膀在哺乳动物中是最异常的构造,但是该规律不适用于这里,因为所有蝙蝠都有翅膀;仅当蝙蝠中的某一物种的翅膀比同属其他物种的翅膀发育得更显著时,这一规律才适用。此外,副性征以任何一种方式出现,这一规律都是非常适用的。亨特所说的副性征是指仅属于雌性或雄性的性状,这些性状与生殖作用没有直接关系。这一规律适用于雌雄两性,但是由于雌性的副性征通常不是很明显,因此该规律对雌性很少适用。毫无疑问,无论副性征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容易发生变异。但是,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副性征,在雌雄同体的蔓足类中也得到了证实。我在研究该类动物时,特别研究了华特豪斯的言论,并发现这一规律基本上完全适用。在另外一部作品中,我会列举出更好的例子。在这里,我仅简要举出一个例子,用来说明此规律可以广泛应用。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无柄蔓足类的厣甲都是非常重要的构造,通常在不同的属中,它们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在四甲藤壶属的几个物种中,同源的厣甲却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形状完全不同,即使是在同种的不同个体之间,差异也很大。因此,这些重要的器官在同种的各变种间呈现的差异,比不同属之间物种呈现出的差异要大得多。
某一地区同种鸟类之间的差异非常小,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它们。在我看来,上述规律也可以适用于鸟类。但是我无法确认这一规律是否适用于植物,由于植物的变异性,使得比较它们的变异的相对程度特别困难,那将严重动摇我对其真实性的信念。
当我们看到某一物种的任何构造或器官显著发育时,就会推论该构造或者器官对那个物种具有高度重要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构造或者器官很容易发生变异。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每个物种都是独立创造的,其各个构造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那么对此我们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但是,如果各群物种是从其他物种衍生而来的,并且已经通过自然选择发生了变异,那么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如果我们忽略了家养动物的构造或个体,并且不进行选择,那么这部分构造(例如金鸡的冠)或整个品种将不再具有一致的性状,可以说这个品种已经退化。在退化的器官、几乎没有特殊目的的特殊器官或者多型性生物群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选择要么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要么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生物体还处于波动状态。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家养动物的构造,由于连续选择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且这些构造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异的。通过观察同一品种不同个体的鸽子,我们可以发现,翻飞鸽的喙、信鸽的喙与肉垂、扇尾鸽的姿态与尾羽等,具有巨大的差异,而这些正是英国养鸽家目前主要关注的几个点。甚至在同一亚品种中,例如短面翻飞鸽,也很难繁殖出近乎完美的个体,因为它们的大多数个体都与纯种鸽的标准相去甚远。确实可以说,有两种力量一直在不断斗争:一方面是通过不断的选择来保持品种的纯粹,另一方面是返祖以及发生新变异的内在倾向。从长远来看,前者会获得成功,但从优良短面翻飞鸽品种中,仍有可能会培育出普通粗劣的翻飞鸽。总之,只要迅速不断地进行选择,那些正在变异的部分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异。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自然界的情况。与同属的其他物种相比,当某个构造在任何一个物种中显著发育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从本属从各物种的共同祖先分出来以后,该构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并且这个时期不会很漫长,因为几乎没有物种能延续生存到一个地质纪以上。异常变异量是指非常巨大且长期持续的可变性,为了物种的利益,这种变异会一直通过自然选择不断积累。但是,由于异常发达的构造或器官的变异性很大,并且在一个不太久远的时期内可以持续很久,因此,作为一般规律,我们期望这些构造比长期保持不变的构造具有更大的变异性。我坚信情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是自然选择,另一方面是返祖和变异的趋势,两者之间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停止;而且发育最异常的器官也会稳定下来。因此,不管一个器官有多异常,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遗传给变异后代。例如蝙蝠的翅膀,按照我们的理论,必然在几乎相同的状态下存在了很长时间,因此比其他器官更不容易发生变异。只有在这种变异是相对较近发生并且异常巨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发现所谓“发生着的变异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继续选择以所需方式和程度变异的个体,以及通过继续拒绝倾向于恢复到以前的、放弃有返祖倾向的个体,变异性就可以稳定下来。
本题也适用上一节讨论的规律。众所周知,物种性状比属的性状更易变异。现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一个大属内,某些物种开蓝色花朵,而另一些物种开红色花朵,则颜色只是物种的性状,没有人会对蓝色花种变成红色或红色花种变蓝色感到惊讶;但是如果属内所有物种都开蓝色花朵,则颜色将成为属的性状,并且其发生变异将是不同寻常的情况。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示例,是因为大多数博物学家提出的解释在这里都不适用。他们认为物种性状比属的性状更易变异,是因为在生理上,物种性状没有属的性状重要。我相信他们的解释是不全面的,或者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我在分类一章里还要提及这一点。关于物种性状比属的性状更易变异,援引证据来支持几乎是多余的。我在博物学著作里屡次注意到,有人惊讶地谈到关于重要性状的事实:某些重要器官或构造,在物种的大群中通常非常稳定,然而在亲缘密切的物种中却有极大的差异,并且在同一个物种的个体中,也往往会发生变异。这个事实表明,当属级特征降为种级特征时,虽然其生理重要性没有改变,但通常已经容易发生变异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畸形:至少小圣提雷尔深信,同一属中不同物种的器官差异越大,则个体发生畸形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每个物种被独立创造的观点来看,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属的各物种之间,构造相异部分比相似部分更容易发生变异。如果按照物种是特征明显及固定的变种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可以预期在最近发生了变异、彼此有差异的那部分构造,仍然会经常发生变异。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陈述:属的性状是指同属内所有物种在构造上彼此相似,而与近缘属在构造上不相同的性状。我之所以将这些特性归因于共同祖先的遗传,是因为很少有自然选择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改变不同的物种,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所谓属的特性,是指各物种在从共同祖先分离出来之前已经遗传到的特性,经历了数代后没有变异或仅有少许变异,现在可能不会再变异了。另外,同属不同物种之间的相异特性为物种的特性。由于这些特性在从共同祖先分出来以后发生了变异,因而不同的物种之间有了差异;它们很可能仍然在发生变异,至少比那些长期保持不变的构造更具可变性。
副性征是非常容易变异的,这一点无须我详细说明,已为博物学者公认。同时,人们也认为,在生物群中,各物种的副性征差异比其他构造的差异要大,例如我们可以比较副性征明显的雄鸡与雌鸡之间的差异量,并以此来说明。副性征容易发生变异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我们能够了解到副性征不能像其他特性那样稳定,这是因为性选择积累造成了副性征,而性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严格,它不会引起死亡,只是减少占劣势的雄性的后代。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副性征变异,由于性选择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因此其作用范围很广,并可促使同群内各物种副性征的差异量比其他方面更大。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同一物种两个性别之间的副性征差异,通常为同一属的不同物种之间相同构造上的差异。基于这个事实,我将列举两个此前提到过的例子加以说明,并且由于这些案例之间的差异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甲虫足部跗节的数目,通常是非常大的甲虫群体共有的特征;但是,正如韦斯特伍德所说,在木吸虫科中,这个变异非常大,即使在同种的两性之间也有差异;对于土栖蜂类来说,翅脉是最重要的特征,大部分土栖蜂类都有这些特征,但某些属的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相同物种的两性之间却出现了差异。卢伯克爵士也指出,一些小形甲壳类动物例子能够极好地解释这一规律。他说:“角镖水蚤属主要通过前触角和第五对附肢表现性征,而物种间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这些器官上。” 这种关系可以明确解释我的观点:我认为同一属的所有物种,即任何一个物种的雌雄两性,都肯定来自同一祖先。因此,如果共同祖先或其早期后代的某些构造发生了变异,这部分变异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利用,使得这些物种适应自然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也促使同一物种的两个性别彼此适应,或者使雄性通过与其他雄性斗争来获得雌性。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物种的特征即区别各物种的特征,比属的特征即属内所有物种共有的特征更容易发生变异;一个物种与同属别的种相比较,任何发育异常的构造,往往变异性更大;一个构造无论如何发育异常,如果是全部物种共有的,那么变异程度就不会很大;副性征的变异性很大,并且在近缘物种中的差异也很大;通过生物的相同构造,通常能表现出副性征的差异和普通物种间的差异;以上所有规则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主要是由于同一群体的物种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并且从它那里遗传到了很多共同点;与遗传已久且没有变异的构造相比,最近变异较大的构造仍可能继续变异;对于自然选择而言,通过时间的流逝,或多或少地抑制了返祖和进一步变异的趋势;性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严格;通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都可以积累相同构造的变异,因此它可以被当作副性征,也可以被当作是一般特征。
不同的物种会表现出相似的变异;并且一个物种中的许多变种通常都具有近缘变种的某些特征,或者重现其早期祖先的某些特征。通过关注我们的家养品种,这些主张最容易被理解。在相距最远的地区中,最独特的鸽子品种分化出的亚变种中,有的头上有倒羽,有的足上长羽毛,这些特征都是原始岩鸽没有的。因此,这些特征就是两个以上品种呈现的类似变异。球胸鸽经常出现14根或16根尾羽,可以被视为变异,对于另一品种孔雀鸽来说却是正常构造。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所有这些类似变异都是由几个品种的鸽子受到类似未知因素的影响时,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相同构造和变异倾向。植物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瑞典芜菁和芜菁甘蓝的膨大茎部,通常我们称之为根,有些植物学家将这两类植物列为通过对相同祖先的栽培而得来的两个变种。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两个所谓的不同物种呈现出的相似变异;此外,还有普通芜菁也可以作为类似变异的例子假如根据每个物种是被独立创造的观点,我们应该将这三种植物的茎的相似性,归因于三个独立但密切相关的创造行为,而不是一个共同祖先以同样方式变异的结果。诺丹先生曾在葫芦科中观察到很多类似变异的例子,其他学者在谷类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最近,沃尔先生曾详细讨论过自然状态下昆虫的类似变异现象,并将其归于他的“均等变异法则”之中。
但是,对于鸽子,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在各个品种中不时会有石板蓝色的品种出现,它们的翅膀上有两条黑带,尾端也有一条黑带,腰部及外尾近基部是白色。所有这些都具有岩鸽远祖的特征,因此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一种返祖现象,而不是近期出现的相似变异。我们可能会相信这个结论:这些岩鸽远祖的特征颜色,很容易出现在两个颜色不同的品种的杂交后代中,说明它们并不是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只是受到了遗传法则杂交作用的影响。
毫无疑问,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某些特征在消失了许多世代之后,也许是几百代之后还会重新出现。但是,如果一个品种只与其他某个品种杂交过一次,其后代(有人说是12代或者20代)偶尔都会表现出外来品种的特征。经过12代之后,从同个祖先承继的血液的比例仅为2048∶1;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一般人认为这种极小比例的外来血液的保留带来了返祖的倾向。在没有杂交过的品种中,虽然它的双亲已经失去了祖代的某些特征,正如先前所说的那样,重现失去性状的倾向,无论是强是弱,仍然可以遗传给无数的后代,尽管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已在一个品种中失去的特征,在许多世代后重新出现,最可能的假设是,失去了几百世代的特征,并不是某一个个体突然获得的,而是这种特征潜伏在每一世代中,直到遇到了有利的条件才会再次出现。例如,在勾喙帕布鸽中很少会有蓝色的品种,但是产生蓝色品种的潜在因素在每一世代中都存在,而且可以通过无数世代遗传下去,与无用或退化器官的遗传相比,这种遗传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更大。但是,退化器官的再现,有时确实是因为遗传造成的。
假设由于同一属的所有物种都应该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所以可以预料它们偶尔会以类似的方式发生变异,并导致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产生彼此相似的变种,或某一物种的变种与另一物种在某些特征上有些相似。在我看来,这另一物种只是一个特征显著且永久的变种。但是由此获得的特征可能不重要,因为根据物种的不同习性,所有重要特征的出现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控制。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同一属的物种偶尔也会重现远祖的特征。但是,由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某个群体共同祖先的确切特征,因此也无法区分返祖特征和类似变异的特征。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亲种岩鸽是不具毛腿和倒冠毛的,就无法判断家养品种中这些特征的出现到底是返祖还是类似变异。但是,我们可以从色带的数目来推论,蓝色羽毛是一种返祖现象。因为鸽子的色带与蓝色是有关联的,而一次简单的变异无法出现大量的色带。尤其是不同颜色的品种杂交时,常出现蓝色与其他不同颜色的品种,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上述结论。因此,在自然界中,虽然我们无法判断哪些是祖代特征的重现,哪些又是新的类似变异,但是,根据我的理论,会发现一物种的变异后代与同群其他物种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之所以识别变异物种困难,是因为变种与同属其他物种的特征相似。此外,在两个可疑物种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类型,这表明,除非所有这些类型都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物种,否则它们在变异时已经获得了其他类型的某些特征。但是类似变异最好的证据是,特征稳定的构造或器官偶尔也会发生变异,导致其在某种程度上与近缘种的同一构造或器官类似。我已经收集了很多这样的案例,但是像先前一样,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我只能不断重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且非常值得注意。
在这里,我将提出一个奇怪而复杂的案例,它发生于同属的某些物种中,一部分是在家养状况下,一部分是在自然环境下,这是一个生物的重要特征不受影响及返祖现象的实例。驴腿上有时有明显的横纹,就像斑马腿的一样。有人断言幼驴腿上的条纹是最明显的,从我的观察来看,这是事实。有时驴肩上的条纹是双数的,条纹的长度和形状都容易发生变异。据记载,有一头白色的驴子(并非患了白化病),其脊背上和肩上都没有条纹;而在深色的驴子中,这些条纹有时会非常模糊,甚至完全消失。据说,由帕拉斯命名的野驴,肩上有双重条纹。布莱思先生曾在一头野驴的标本上看到一条明显的肩条纹,它本来不应该有这种肩条纹;普尔上校告诉我,这个物种的幼驴通常在腿部有条纹,肩膀上的条纹却十分模糊。斑驴虽然像斑马一样,上体常具明显的条纹,但是腿上却没有。在阿萨·格雷博士绘制的标本图上,却有清晰的斑马状条纹出现在斑驴后足踝关节处。
我在英国收集了不同品种、各种颜色的马,还有肩上有条纹的例子。在暗褐色和鼠褐色的马中,腿上生有条纹的也不少见,栗色马就是一个例子。暗褐色的马,肩上有时会呈现出微弱的条纹,而我在一匹赤褐色马上也见过带有肩条纹的。我儿子仔细观察了褐色比利时拉车马,并且对我描述了该马,其双肩上都有两条并列的条纹,腿部也有条纹。我曾亲眼见过一匹灰褐色德文郡小马,其双肩上各有三条平行的条纹。有人告诉过我,在威尔士小马的肩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在印度西北部的凯替华马,普遍长有条纹。为印度政府检查过该品种的普尔上校告诉我,没有条纹的马通常被认为不是纯种马。此马的脊背、腿上和肩上,通常都是有条纹的,肩上的条纹有时候是两条或者三条,脸的侧面有时也是有条纹的。条纹在小马驹上最明显,而有时在老马身上会消失。普尔上校也见过初生的灰色和赤褐色的凯替华马都有条纹。从爱德华兹先生给我的信息中,我也有理由怀疑,在英国赛马中,小马驹中的脊背条纹比在成年动物中更为常见。最近,我养了一匹小马,它是由赤褐色雌马(土耳其雌马和法来密斯雄马的后代)和赤褐色英国赛马杂交所生的。它产下一周时,它的臀部和前额都生出了很多极窄的暗色斑马状条纹,而腿部的条纹则不明显。不久之后,所有这些条纹就完全消失了。在此,我不再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我要说的是,我在一些国家搜集了各种马生有腿纹和肩纹的例子,西自英国,东至中国,北起挪威,南至马来群岛,都有这些情况存在。在世界各地,这种条纹在暗褐色和鼠褐色的马中最多,暗褐色包括的范围很广,从黑色到褐色,直至接近乳黄色,应有尽有。
我知道史密斯上校曾就此主题撰写过文章,他认为马的一些品种来自于若干原种,其中的一个原种就是暗褐色且有条纹的,并且上述外观都是由于在古代曾和这暗褐色马种杂交而产生的。我们可以对这个论点加以反驳,因为那些壮硕的比利时拉车马,威尔士矮种马,挪威矮脚马和瘦长的凯替华马,都生活在世界上相距很远的地方,如果说它们都曾和某个假设的原种杂交,这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马属中几个物种的杂交情况。罗林断言,驴和马杂交所生的骡子,一般腿部都具有明显的条纹。根据戈斯先生的说法,美国有些地区的骡子,十之八九腿部都有条纹。我曾经见过一条骡子,它的腿有如此多的条纹,以至于任何人起初都以为它是斑马的杂交后代。在马丁先生一篇关于马的优秀论文中,绘有一幅类似的骡子图。我在四幅彩色的图画中看到了驴和斑马产下的杂种,它们腿上的条纹比身体其他部分的更明显,并且其中一幅图上画有两条并列的肩条纹。莫尔顿勋爵蓄养了一匹有名的杂种,为栗色雌马与雄斑驴所生,它与后来该栗色雌马与黑色阿拉伯雄马所生纯种的后代,腿部的条纹都比纯种斑驴明显得多。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格雷博士曾绘制过驴子与野驴所育杂交种的图(他告诉我,他还知道另一个相同例子)。这个杂种的四条腿上都有条纹,像德文郡褐色马及威尔士小马那样,其肩部还有三条短条纹,甚至在面部两侧也生有斑马状的条纹。我们知道,驴腿上只是偶然有条纹,而野驴腿上和肩上没有条纹。关于这最后一个事实,我坚信杂种面部的每一条斑纹的出现都不是偶然。我曾向普尔上校询问过凯替华马的面部是否有条纹,并且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要如何解释这几个事实呢?我们看到马属的几个非常独特的品种,通过简单的变异,可以像斑马一样在腿上长有条纹,或者像驴一样在肩上出现条纹。在马匹中,这种条纹在暗褐色品种中出现的可能性最大,而这种颜色接近该属其他物种普遍具有的颜色。条纹的外观并不伴随任何形式的变异或任何其他新特征的出现。我们还看到,这种趋势在几种最独特的物种之间的杂种中变得最明显。现在看看几种鸽子的情况:这几个品种均来自一种蓝色的鸽子(包含两三个亚种或地理种),这种鸽子具一定的条纹或其他标志。如果任何品种的鸽子变异之后身体呈现蓝色,上述条纹及其他标志就会重现,但其他形态和特征都不会发生变化。假如不同颜色的最原始、最纯粹的品种进行杂交,其后代重现蓝色和条纹及其他标志特征的倾向最大。我曾说过,关于返祖想象,最合理的解释是:每一世代的幼体都有产生长期消失的特征的趋势,这种趋势有时由于未知原因会占优势。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几种马属动物中,条纹在幼体中比在较老的个体中更常见。如果我们把那些保持纯种达数百年之久的家鸽称为物种,那么马属内的物种具有相似的特征。我可以大胆地猜测,千万代以前存在着一种动物,其条纹与斑马一样,但是其他方面的构造却不相同,它就是现在的家养马(无论是源自一个还是多个野生原种)、驴、野驴、斑驴和斑马的共同祖先。
如果有人相信每个马属内的各个物种都是独立创造的,那么任何物种被创造出来时就有一种趋势,即在自然界或家养条件下,都会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变异,使得它像马属中其他物种一样具有条纹;而且,任何物种被创造出来时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即这些物种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物种杂交后,生出的带有条纹的后代与其父母并不相似,而是与同属中的其他物种相似。在我看来,一旦接受了这种观点,就等于否认了真正的原因,而去接受不真实的或未知的事实,这种观点夸大了上帝的作用;而我只能像老朽无知的神创论者们一样,相信贝类化石从未存活过,它们只是从石头里被创造出来的,以模仿今日在海边生活的贝类而已。
我们深感对变异法则的无知。各构造变异的原因,我们能解释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但只要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同种中不同变种间的较小差异,还是同属中不同物种间的较大差异,同样都受到法则的支配。外部环境的改变通常会造成不稳定变异性,有时也会产生直接的和定向的变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显著,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习性可以产生特殊的构造,无论是经常使用的器官会强化,还是较少使用的器官会减弱和缩小,这些结论可以用于许多场合。同源构造趋于以相同的方式变异,并且趋向于结合。硬体构造及外部构造的改变,有时会影响相邻软体构造或内部构造。当某个构造特别发达时,可能会从相邻构造汲取营养;而在不损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多余的构造可能被废退。生命早期的构造通常会影响随后发育的构造;虽然我们还不太了解许多相关变异事实的性质,但毫无疑问,它们是会发生的。重复构造在重复次数和构造特征方面容易产生变异,可能是这部分构造并没有因为特定功能而专用的缘故,因此,它们的变异不受自然选择的支配。可能是同样的原因,低级生物比高级生物更容易发生变异。无用的退化构造不受自然选择的控制,因此更容易变异。物种特性比属的特性更容易发生变异,所谓物种特性是指区别同一属内各物种的性状特征,这些特性从各物种的共同祖先分出以后,常常会发生变异;属的特性是指遗传已久而没有发生变异的性状特征。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推测,在近期发生了变异,彼此有差别的构造,还会继续变异。我在第二章中说过,这个推论也适用于整个群体。在某些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同属的物种,这表明这里曾发生过很多的变异和分化,或者产生了很多新的物种。因此,平均而言,现在这些区域内的物种会出现很多的变种。副性征特别容易发生变异,同属内各物种呈现出的副性征差异常比其他构造的差异要大。同一物种雌雄两性间副性征的差异,通常表现为同属的各物种之间相同构造上的差异。异常发达的器官构造比近缘种的相同构造更容易发生变异,因为从该属形成以后,它们就经历了极多的异常变异,由于这种变异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因此自然选择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抑制变异的趋势和阻止变异的进程。假如一个物种具有特别发达的器官,并且已经产生了许多变异的后代(这是一个缓慢且长久的过程),不论这个器官发育得如何异常,自然选择都会使这个器官的特征保持不变。如果源自同一个祖先的许多物种继承了大致相同的构造,并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下生存,就容易发生类似变异,有时还可能发生返祖现象。虽然返祖现象与类似变异并没有引起重要的新变异,但是这些变异在增进自然界的美丽和协调的多样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后代与亲代之间的差异,每一个微小的差异都必定有它的起因。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构造中,与物种习性有关的变异都是由有利变异慢慢积累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