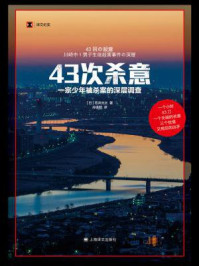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文艺批评文集》初版于1964年(不过,某些进入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可上溯到1954年)。我现在是在1971年。因而,时间的问题在这里是必然要提出来的(“时间”,在我们不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它是历史之腼腆的、被窒息的形式)。
我们知道,近年来,一种研究运动,也是一种战斗运动,围绕着符号的概念、对它的描写(description)和它的过程(procès)在法国发展了起来;把这
一运动称为
符号学
(sémiologie)
 ,或是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e),或是
语义分析
(sémanalyse)或是
文本分析
(analyse textuelle),都不重要:不管怎样,没有人满意这些词语,因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时髦,另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过分宽泛和走样的应用。对于我来说,我将保留“符号学”这个词语,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考虑,而是为了方便地指明一整套丰富的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如果我需要对法国符号学做一番简短评介的话,我却不会尽力为其找出一种最初的界限;我忠实于吕西安·费弗尔
,或是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e),或是
语义分析
(sémanalyse)或是
文本分析
(analyse textuelle),都不重要:不管怎样,没有人满意这些词语,因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时髦,另一些人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种过分宽泛和走样的应用。对于我来说,我将保留“符号学”这个词语,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考虑,而是为了方便地指明一整套丰富的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如果我需要对法国符号学做一番简短评介的话,我却不会尽力为其找出一种最初的界限;我忠实于吕西安·费弗尔
 的劝告(见其关于历史分期的一篇文章),更愿意为其寻找一种中心标记,而从这一中心标记出发,该运动便似乎可以辐射到
其前
和
其后
。对于符号学来说,这一时间是1966年;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巴黎方面,这种研究的最为敏锐的那些课题在那一年出现了重大的、大概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混合:这种变化表现在新创杂志《分析手册》(
Les Cahiers pour l’analyse
)
的出版方面(1966),在这份杂志中,我们看到了符号学的主题、拉康
的劝告(见其关于历史分期的一篇文章),更愿意为其寻找一种中心标记,而从这一中心标记出发,该运动便似乎可以辐射到
其前
和
其后
。对于符号学来说,这一时间是1966年;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巴黎方面,这种研究的最为敏锐的那些课题在那一年出现了重大的、大概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混合:这种变化表现在新创杂志《分析手册》(
Les Cahiers pour l’analyse
)
的出版方面(1966),在这份杂志中,我们看到了符号学的主题、拉康
 的主题和阿尔都塞
的主题和阿尔都塞
 的主题;于是,我们仍在争论的那些严肃问题便被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说话主体与故事之间的新型关系、从文本到作品在理论上和论战上的替换。正是在那个时刻,实现了符号学设想的第一次衍射,即符号观念的一种过程——这一设想最初曾将这种过程有点过于天真地看作自己的功劳:这种过程从1967年开始便被德里达
的主题;于是,我们仍在争论的那些严肃问题便被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说话主体与故事之间的新型关系、从文本到作品在理论上和论战上的替换。正是在那个时刻,实现了符号学设想的第一次衍射,即符号观念的一种过程——这一设想最初曾将这种过程有点过于天真地看作自己的功劳:这种过程从1967年开始便被德里达
 的著述、《原样》杂志(
Tel Quel
)
[1]
的作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的著述、《原样》杂志(
Tel Quel
)
[1]
的作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的研究工作所标志。
的研究工作所标志。
《文艺批评文集》一书虽然先于这一转折,但属于符号学的上升阶段。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应该以纯粹历时性的(diachronique)方式即(在赋予其一种意义、一种历史可理解性的同时)以
合乎情理
的方式供人参考。首先,在这本书本身,多元性总是存在着:书中所有文本都是多义的(正像其作者在1954年至1964年那个时期一样,他同时介入了文学分析、符号学的初创和对布莱希特
 艺术理论的捍卫),并且,这些文本的汇编是拼凑的:从
一开始,就没有总体意义上的考虑,就没有承担一种智力“命运”的妄想:它们仅仅是一项渐进的、对于他自己来讲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研究工作的痕迹。其次,如果它正好是“结构主义”教给我们的一种东西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或将来的)阅读属于这本过时书籍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这些文本会因其他人对其投注的新目光而
发生变化
;更明确地讲,可以希望它们适合于被叫作
诸多言语活动之合谋
(collusion de langages)的东西;可以希望最近的先锋派的言语活动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借助于通常的多元使命)
无论如何
已经是它们自己的意义了,一句话,希望它们可以在一种
翻译
活动中(符号仅仅是可翻译的)被考虑。最后,至于将来,必须想到,文化时间的运动并不是直线的:当然,一些主题最终可能陷入过时境地;但是,其他主题,虽然表面上气势大减,但却有可能重返言语活动的舞台。例如布莱希特,他出现在这部汇编中,但似乎已从先锋派领域消失了,我确信,他没有说出他最后的主张:他还会回来的,当然不是像我们在《文艺批评文集》之初看到的那样,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螺旋形地
回来。这是维科
艺术理论的捍卫),并且,这些文本的汇编是拼凑的:从
一开始,就没有总体意义上的考虑,就没有承担一种智力“命运”的妄想:它们仅仅是一项渐进的、对于他自己来讲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研究工作的痕迹。其次,如果它正好是“结构主义”教给我们的一种东西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或将来的)阅读属于这本过时书籍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这些文本会因其他人对其投注的新目光而
发生变化
;更明确地讲,可以希望它们适合于被叫作
诸多言语活动之合谋
(collusion de langages)的东西;可以希望最近的先锋派的言语活动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借助于通常的多元使命)
无论如何
已经是它们自己的意义了,一句话,希望它们可以在一种
翻译
活动中(符号仅仅是可翻译的)被考虑。最后,至于将来,必须想到,文化时间的运动并不是直线的:当然,一些主题最终可能陷入过时境地;但是,其他主题,虽然表面上气势大减,但却有可能重返言语活动的舞台。例如布莱希特,他出现在这部汇编中,但似乎已从先锋派领域消失了,我确信,他没有说出他最后的主张:他还会回来的,当然不是像我们在《文艺批评文集》之初看到的那样,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螺旋形地
回来。这是维科
 提出的历史之美妙的意象(在不重复和不反复的情况下重述历史),而我正想将这部书的新版本置于这种意象的保护之下。
提出的历史之美妙的意象(在不重复和不反复的情况下重述历史),而我正想将这部书的新版本置于这种意象的保护之下。
1971年9月,R. B.
注释
[1] 《原样》(Tel Quel):又译《泰凯尔》、《如是》。因本书对“Tel Quel”本义有所使用,故取《原样》译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