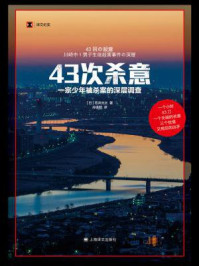在欧洲,24个世纪以来,戏剧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今天,即1955年,还是那个样子。每当我们去剧院,不论是看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蒙泰朗
;今天,即1955年,还是那个样子。每当我们去剧院,不论是看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蒙泰朗
 的戏剧,不论是拉辛
的戏剧,不论是拉辛
 的戏剧还是鲁森
的戏剧还是鲁森
 的戏剧,不
论是玛丽亚·卡萨雷
的戏剧,不
论是玛丽亚·卡萨雷
 演出的戏剧还是皮埃尔·弗雷奈
演出的戏剧还是皮埃尔·弗雷奈
 的戏剧,不论我们的爱好是什么,也不论我们属于什么党派,我们都要根据若干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观说出快乐与烦恼、好与坏,这种道德观的信条是:观众越是激动,他就越是与主人公同一;舞台越是模仿动作,演员就越是体现其角色;戏剧越是神奇的,演出就越是绝好的。
的戏剧,不论我们的爱好是什么,也不论我们属于什么党派,我们都要根据若干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观说出快乐与烦恼、好与坏,这种道德观的信条是:观众越是激动,他就越是与主人公同一;舞台越是模仿动作,演员就越是体现其角色;戏剧越是神奇的,演出就越是绝好的。
然而,有一个人来了,他的作品和思想在我们最有充分理由认为是“自然的”这一传统观点上彻底地反对这种艺术;他不顾任何传统,对我们说,观众只应该介入演出中的一半,为的是“了解”演示的东西,而不去承受这种东西;演员应该帮助产生这种意识,同时揭示其作用,而不是去体现这种意识;观众从来都不应该完全地与主人公同一,以便于他总可以自由地评判其痛苦的原因,继而评判其治疗方案;动作不应该是被模仿的,而应该是被讲述的;戏剧应该不再是神奇的,而应该变成批判的,在他看来,这还是最好的表达热情的方式。
于是,正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重新质疑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反应、我们一直信守的戏剧“法则”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沉默或讥讽,并面对布莱希特。我们的杂志在面对现时戏剧的粗俗或低下、墨守成规和技巧僵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愤怒,以至于不能再长久拖延迟迟不去询问我们时代的这位大剧作家了,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作品,而且提供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灵验、严密、稳定,也许难以应用,但它至少具有一种无可争辩 的和拯救性的“轰动”和惊异效果。
不论人们最后对于布莱希特的论断是什么,至少都应该注意到,他的思想与我们时代的重大进步主题是协调一致的:要知道,人类的弊端就由人类自己的手掌控着,也就是说,世界是易于操作的;艺术可以、也应该介入历史之中;艺术应该与和它相关联的科学一起致力于相同的任务;我们今后应该有一种有关阐释的艺术,而不仅仅有一种有关表达(expression)的艺术;戏剧应该坚定地帮助历史,同时揭示其过程;舞台技巧本身也是被引入的;最后,不存在永恒艺术的一种“本质”,但是,每个社会都应该发明有助于它更好地获得自我解放的艺术。
当然,布莱希特的思想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并招惹来一些阻力,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因为法国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东德
 的历史复杂性。《大众戏剧》为布莱希特安排这一专号,并不因此打算解决这些问题或克服这些阻力。我们现在唯一的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布莱希特。
的历史复杂性。《大众戏剧》为布莱希特安排这一专号,并不因此打算解决这些问题或克服这些阻力。我们现在唯一的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布莱希特。
我们将微微开启一本卷宗,我们远不能将其看作是已经封卷的。如果《大众戏剧》的读者们想为此提供他们的证明的话,我们将非常乐于接受。在我们看来,对于这样一位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看作“当代关键人物”的人,这将弥补一个数目极大的知识分子群或戏剧界人士对他的无知或漠视。
1955,《大众戏剧》
注释
[1] 为《大众戏剧》第11期(1955年1—2月)布莱希特专号所写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