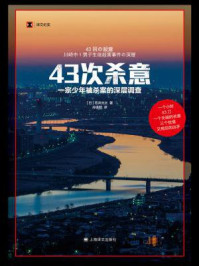我在写——这便是言语活动的第一等级。随后,我写我在写——这便是第二等级。(帕斯卡尔已经说过:“遁逝的思想,我想把它写出来;我宁愿写出来,而不想让它从我这里遁逝。”)
今天,我们对于这第二等级消费量很大。我们知识分子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对无论什么样的语句都提出猜疑,同时揭示其所有等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没有穷尽的。而向每一个词开放的这种深渊、言语活动的这种疯狂,我们科学地称之 为:陈述活动(énonciation)(首先,我们是因为一种策略上的原因才打开这个深渊的,即打掉我们的陈述之自负和我们的科学之傲气)。
第二等级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只需将一种意图、一个场面、一个躯体的级别撤后一点,就可以完全推翻我们对此可能有的兴趣和我们有可能给它的意义。第二等级有着一些色情和美(例如拙劣的文艺作品)。我们甚至可以变成第二等级的狂热爱好者。不接受外延、不接受自发性、不接受喋喋不休、不接受平淡无奇和天真的重复,只容忍一些表现出——哪怕是轻微地表现出——一种偏离能力的言语活动:滑稽模仿、意义含混、改头换面的引用。言语活动一旦思考,就变成破坏性的。然而,有一个条件:它要永远不停地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停留在第二等级上,我就会受到智力至上论的指责(例如佛教向任何简单的自省性发出的指责);但是如果我去掉(理智、科学、道德的)级别,如果我使陈述活动自由进行,我就打开了无休止的贬低之路,我就消除了对于言语活动的心安理得。
任何话语都处于等级游戏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游戏称之为:阈学(bathmologie)
 。一个新词不属于多余,如果我们由此可以想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言语活动划分的科学——的话。这种科学
将是前所未闻的,因为它将动摇表达、阅读和听的习惯要求(“真实”,“现实”,“忠实”),它的原理将是一种震撼。就像我们跳过一个台阶一样,它将跨越任何表达方式。
。一个新词不属于多余,如果我们由此可以想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言语活动划分的科学——的话。这种科学
将是前所未闻的,因为它将动摇表达、阅读和听的习惯要求(“真实”,“现实”,“忠实”),它的原理将是一种震撼。就像我们跳过一个台阶一样,它将跨越任何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