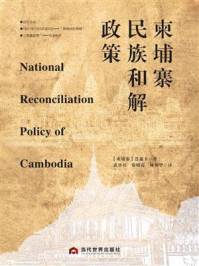赫哲族是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目前主要生活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下游,自松花江至乌苏里江的右岸及西岸。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赫哲族人口为5354人。中国的史籍和俄罗斯的一些史料都表明:明清以来,黑龙江流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口是那乃人(赫哲人)生息、活动之摇篮(赫庆云、纪悦生,2016:42~51)。完备的父系氏族制度,为抢夺妇女、财产或血亲复仇而进行的部落战争,为了生计而进行的频繁的氏族迁徙,以萨满为中介的多神宗教活动等,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内容,直到20世纪70年代,渔猎经济还是赫哲族的主要生产方式。赫哲族一直有语言而无文字,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口头传统、生活技艺和歌舞艺术形式。按照史诗发展阶段和基本规律判断,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神话、传说、故事、萨满神歌等文艺传统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篇幅规模较为宏大、故事情节更为复杂的英雄史诗“伊玛堪”。
伊玛堪是以民族语言讲唱部落联盟征战历史,以歌颂民族英雄莫日根不朽功业为主的民族史诗,代表着赫哲族传统文学的艺术成就,也承载与彰显着赫哲族的生产生活、精神文化与民族心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种曾经作为赫哲族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的史诗讲唱活动已经濒临消失。与此同时,生活方式日益呈现现代化面孔的赫哲族人开始在心理上寻求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时在现代性冲击下被边缘化的传统文化重新担负起民族认同的功能。尤其是伊玛堪在被列入世界和国家级非遗名录后迎来了新的转机。如何完成这一传统文化事项在当下现代社会中的再植和再生,是我们需要研究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史诗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之中的古老文学样式,在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因此“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是一座民族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郎樱,1999a),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黑格尔,1981:108)。随着史诗文本的大量发掘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术界开始以大量的事实对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进行驳斥。同时在全球化和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世界性的、区域和地方性的传统话语,正在不同层面和维度重构关于史诗的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随着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我国的史诗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逐步构建起更富于阐释力的史诗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概念的界定和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但是直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系统的理论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以荷马史诗为范例的古典诗学研究体系下,在欧洲的古典学和语文学的涵濡下,西方古典诗学在史诗结构和形式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掀起了民间史诗搜集与研究的热潮,口头诗歌得到发掘和重视,推动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方面的探索,为后来学者提出史诗研究范式向口头传统和实证研究范式转变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伴随欧洲民俗学的兴起,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典型样式再次受到现代学者的关注,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受到历史研究的启发,以及史诗分析程序的日益精密、严谨,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首创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的比较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其文化意义,开启了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的新篇章。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与其学生洛德(Albert Bates Lord)以“荷马问题”为试金石,在南斯拉夫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和口传史诗采录,在此基础上,共同开拓了口头传统比较研究的新领域。他们在研究中揭示出口传史诗传统鲜明的程式化特征与讲述中歌手创作的动力机制,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学界将之命名为“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这一理论使史诗研究超越了欧洲古典学科而成为跨文化、跨地域和跨学科的口头传统比较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史诗研究领域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史诗研究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极大地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同时提高了口头传统的分析理论的阐释力(尹虎彬,2008)。
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界把史诗确认为民间文艺样式。相对于歌谣、神话和故事各门分支学科,我国史诗学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陆续被发掘和采录。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专家和学者开始大规模地搜集、采录、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史诗,在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回答了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提出的“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的疑问,也提请人们重新思考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除却蜚声于世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史诗更有力地证实我国是一个民族史诗蕴藏丰富的史诗大国。
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相对薄弱。尽管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但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处于起步时期的中国史诗研究多受西方古典诗学的影响,将史诗纳入文学和历史学的范畴,一方面偏重体裁、文本等形式的研究,以书面文学的判断标准、分析方法和评价体系进行文本解读,另一方面侧重于关注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而把史诗作为民族文学的经典纳入文学史的表述体系之中,而忽略了对史诗自身“口头性”(orality)的微观分析。
20世纪末期,随着口头传统、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等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引入,学术界开始以民俗学和整体研究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的史诗与史诗传统,从文化多样性视角出发,立足中国史诗活形态的特性,逐渐突破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进入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史诗研究学者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自此,中国的口头诗学研究进入新的领域,逐渐转向对口头诗歌内部运作机制的探讨,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由对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史诗样式的内部结构研究,从而使我国的史诗研究逐渐走向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新层面,也逐渐取得了与国际史诗研究对话和交流的话语权。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任何外来理论的借鉴和使用都必然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借鉴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和学术观念的“口头传统”理论,使之为我国史诗研究提供参照的基础上,我们更要立足本土史诗与文化传统,擘肌析理,将其批判地应用于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最终构建真正符合我国史诗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模式。我国形态多样的民族史诗传统,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进行史诗理论的拓展研究,无疑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也为借鉴西方“口头传统”诗学理论和本土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坚实的材料基础,这是本书选取活形态史诗文本进行个案研究的首要动因之一。
本书选择濒临灭绝的赫哲族口传英雄史诗伊玛堪作为研究对象,还源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伊玛堪本身具备的多重研究价值。赫哲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古老民族之一,居住在三江平原一带,没有文字,以渔猎为生,却创造和保留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渔猎文化和民间艺术形式,其中篇幅巨大、情节曲折的英雄史诗伊玛堪堪称民族文化之集大成者,是记录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活书”,与其他民族史诗一样,具有叙事学、语言学、民族学、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重研究价值。在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人口较少甚至曾经濒临灭绝的民族中,创造并传唱着一曲曲古远苍凉的英雄赞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史上的奇迹,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
在笔者生长的东北地区,在许多少数民族中都发现了活形态的史诗文本。与举世闻名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相对应,东北地区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达斡尔族的“乌钦”和赫哲族的“伊玛堪”被称为“三小民族英雄史诗”,而学术界对于它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文化自觉背景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对于民族的文化自觉具有重要意义。本书试图在民族史诗的研究及其文化传承上能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目的,为无文字的北方民族史诗研究略尽绵力。
真正的研究往往是从学术史的结构中启程,又是在具体的学科传统中开展的。这就需要我们要善于把以往及随后的理论和整套术语放在特定的学术发展脉络中加以检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做新的界定和阐述,从材料和事实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伊玛堪的采录研究进行梳理。
关于伊玛堪的调查、记录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了民族学家凌纯声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这是我国来自实地考察的第一部关于赫哲族的民族志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伊玛堪文字记录。这次考察始于1930年,历时三月“在松花江下游,自依兰以至抚远一带实地考察民族生活状况与社会情形”(凌纯声,2012:1)。该书50余万字,分上下两卷,有插图333幅。其中“赫哲故事”共19篇,约30万字,绝大多数是伊玛堪作品。作者将这19篇“赫哲故事”分成四类:英雄故事、宗教故事、狐仙故事和普通故事。其中14篇当属于伊玛堪创作。唯一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搜求故事的目的是为研究文化作参证,因此虽一一地真实记录,却没顾及伊玛堪的讲唱形式,而是采取了唱讲并用散文形式记录的做法,因而没有保存伊玛堪卓有特色的韵文诗体。一些伊玛堪曲调,分记在赫哲族音乐部分。虽然伊玛堪的艺术形式没有得到恰当的保留,但由于作者严肃的科学态度,较完整地记录下了伊玛堪的情节脉络,而没有过多地添加政治和文学性的内容,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看到伊玛堪的原貌,在目前研究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具有足资凭信的多学科研究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国民族研究工作者参与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伊玛堪受到重视。30余篇伊玛堪名目被查明,6个伊玛堪片断被采录。同江县八岔乡的吴进才讲唱的完整的《安徒莫日根》,饶河四排村葛德胜说唱的长篇伊玛堪《满格木莫日根》被刘忠波等人记录整理,分别发表在此次考察的成果《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刘忠波编写的《赫哲人》中,伊玛堪第一次被称为“赫哲族以口头相传的说唱文学”。紧随其后的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开展的黑龙江省各民族民间文学普查,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期间的调查包括对与伊玛堪相关的伊玛堪篇目、讲唱者及个别唱篇和片断的发掘。
伊玛堪采录的丰收季节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以及地方有关组织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组成赫哲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开展了赫哲族民间文学遗产抢救工作。从1980年9月到1981年5月,他们先后两次分别走访了四排、八岔、街津口等赫哲乡里的伊玛堪著名歌手葛德胜、吴连贵、尤树林等。按说唱的艺术形式采录了葛德胜说唱的《满斗莫日根》、《香叟莫日根》、《阿格弟莫日根》、《希尔达鲁莫日根》、《木都里莫日根》和《吴胡萨莫日根》6部伊玛堪作品,经过整理、翻译分别发表在黑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内部研究资料《黑龙江民间文学》的第2、12、20、21集中。这些汉译译文作品较为准确地表现了伊玛堪的故事内容,韵散结合的记录形式较之前更充分地反映出伊玛堪讲唱结合的叙事特点和体裁特征。
由于伊玛堪及其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大规模正式公开出版,所以国内外的学术界虽然知道我国黑龙江流域有史诗性的长篇说唱文学形式,但是因为公开资料甚少而对之缺乏广泛深入的了解、认识和研究。因此,1998年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将以往发表的伊玛堪作品重新整理,出版了《伊玛堪》作品集上下两卷,包括长期以来采录的十几篇伊玛堪作品及片段,对不同的整理稿做了字词的统一,以便于读者阅读,同时尽量注意保留了口语讲述的风格。在每篇作品后面附记有伊玛堪的作者、采录地点和采录时的相关背景资料,使读者增加了感性认识。此外,在书后附有《葛德胜自传》、《赫哲族伊玛堪调查报告》、《赫哲族的萨满》和《伊玛堪歌手情况简表》,为伊玛堪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和依据,也进一步提升了伊玛堪在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影响力。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1992年,黑龙江民族研究所出版了赫哲族学者尤志贤编译的《赫哲族伊玛堪选》,共收录了《满都莫日根》和《沙伦莫日根》两部完整的伊玛堪作品及《木竹林莫日根》和《吴胡萨莫日根》片段,不仅有准确优美、散韵结合的汉译译文,还用国际音标标注了赫哲语原文,弥补了以往整理出版伊玛堪作品中的不足。这不仅在保存伊玛堪作品方面做出了贡献,也在保存赫哲语原始资料方面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