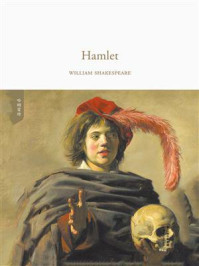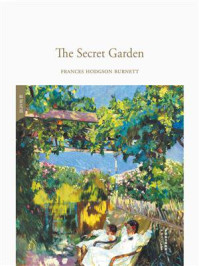城内的军营与周围的驻地传来第一阵号角声前,大多数市民就早早地醒了。他们不必从草垫和铺了一层薄毡的床上起身,因为除了孩子,蜂巢般密布的屋宅里几乎没几个人躺下过,相反,他们却围着火苗微弱的火盆或壁炉,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地熬了一夜,一直熬到夜色褪尽,又开始提心吊胆与惶惶不安的一天。
该团当年就是在这个区起的家,其实,当年一手拉起这支队伍的是一个十足的无赖,他率领该团投到了拿破仑的麾下,后来升任皇帝阶前的一名元帅,是一个煞气遮住半边天、威震半个地球、红极一时的人物。该团后来招募的新兵多半出自这个区,当地的小伙子们年纪一到就早早地从了军,因此,这里的老人不仅多半是当年的老兵,而且个个已为人父、沾亲带故,不单是阵亡士兵年迈的双亲或亲人,若非纯粹机遇和运气,兴许还是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和爱人也在阵亡士兵之列的父亲、母亲、姐妹、妻子和恋人。
号角的余音尚未散尽,人们就拥出了杂乱无章的贫民区。一名法国,或英国,抑或美国飞行员(或者一名莽撞的德国飞行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茅棚和公寓汇成一条条小巷、小街和叫不出名儿的死胡同,小巷、小街和死胡同又汇成大街,一如涓涓细流汇成小溪,小溪汇成江河,直至全市的民众似乎都拥上了市中心广场四通八达、宽阔的林荫大道,挤满了广场,继而随着汇聚一处的人流,如同一波一往无前的浪头拥向市政厅的假门,三国联军的三队哨兵在门前守着三根光溜溜的旗杆F,静候三面相似的旗帜。
他们在这里遇到了第一支军队。这是一支屯骑,骑兵们勒马迎着古时候的东城老城门方向,在广场宽阔的大道口摆好阵势,仿佛等着先洪水一步直奔驻军司令星期三卧室的淙淙声。但人群连看都没看一眼这支骑兵,一个劲儿地拥向广场,由于人多拥挤,人流放缓了速度,最终停下了脚步,骚动的人群顶着渐高的日头,惴惴不安、耐着性子盯着市政厅大门。
扼守这座城市的要塞传来了黎明的炮声;市政厅门口凭空同时打出了三面旗帜,升上三根旗杆。它们在晨曦中打出、升上、高耸旗杆的顶端,静静地挂在那儿。第一缕晨风吹来,它们迎风招展,飘进了阳光,洒进三种交相辉映的颜色——红色代表勇气和自豪,白色代表纯洁与坚贞,蓝色代表正直与真理。骑兵身后空荡荡的大道突然洒满了阳光,阳光将人和马高大的身影投向人群,就好像这队骑兵正要冲将过去。
谁知冲向骑兵的却是民众。人群不声不响,这帮暂时走到一起的人秩序井然,像陡落的潮水,浪势不可挡。骑兵暂时没采取任何行动,在场负责的是一位军官,虽说看样子不过是一位上士。接着,上士吼了一声。这不是一道命令,因为骑兵们没动。这声吼听着毫无意义,说实在的,莫名其妙,是一声凄凉、绝望的呼喊,仿佛这时候城市上空遮天蔽日的云雀中的一只,翱翔空中,却又看不见,不知从何处发出一声悦耳、轻轻的鸣叫,悬浮在空中,渐渐淡去。不过接下来的一声吼却是一道命令。可惜为时已晚;人群仿佛走进斗狮场的殉道者,以血肉之躯几近漠然、不屑一顾地迈进铁蹄与马刀的铁阵,慢慢地走向这支本着难以想象的忍让但又势不可当的军队。
骑兵立刻勒住了马。即便这时候,队伍仍秩序井然。队伍仿佛被一只大手捉住似的,开始后退——被勒得翻着白眼的马,高举马刀、高高在上、张大嘴巴却又并不出声的小脸——好似一尊尊武士雕像,瞬间被深藏石窖、舍不得示人的瑰宝化作的泥石流冲出空空如也的宫殿、大厦或博物馆,统统向后退去。不久,骑在马上的军官挣脱了束缚。一时间,似乎唯独他在前进,因为在分立两旁的人群中,唯独他高高在上、一动不动。接着,他确实动了起来,他催着勒得紧紧、铁铸一般的马挺进,穿过流动的人群;马下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声音,兴许是他策马硬闯的路上,一个孩子,或者女人,抑或是又痛又怕顾不得体面的男人的恸哭,他虚张声势、骑着马闪躲腾挪地穿过了人河,人群好像水承载着劈波斩浪的船头,并不躲着他和他的马。不一会儿,他就不见了踪影。人群这下一拥上了大道,将骑兵冲散在道路两旁,浩浩荡荡地从他们身边经过,仿佛一条洪水泛滥、吸干了支流的大河,带走了纵横交错、大街小巷的人流,大道最后汇成了一片人头攒动、波涛汹涌、无声无息的湖泊。
但步兵早就已经赶到了,不等那位骑兵军官汇报当天的值日官,值日官派传令兵,传令兵叫来勤务兵,勤务兵放下伺候副官洗漱、修面的活儿,副官叫醒尚在梦中的驻军司令,驻军司令打电话或差通信员去要塞通知步兵指挥官,步兵就跟着人群冲出了中心广场。步兵这次出动了整整一个营,除了骡马,一个个全副武装、排着整齐的队列出了中心广场,由一辆收起挡板、随时准备上阵的轻型坦克开道,前进的途中,坦克如同一台扫雪车,分开了人群,又舞起扫帚将分立两旁的人逼退到路牙,步兵分成两列纵队、并排跟着一路猛进的坦克,到了最后,从广场到老城门之间的整条大道,除了两排上了刺刀、互相交错的步枪外,又空无一人。星期三这天的某个时候,刺刀林后出现了一阵骚动,但范围不到十英尺,没有扩散,只有附近的人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交错的刺刀下,一名排副低头侧着身子挤了进去,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一名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年轻妇女,也兴许是一位姑娘家晕了过去。她穿着一身单薄、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躺在她晕倒的地方,看样子,是一路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而且多半是靠两条腿或坐牛车,如果说她存心倒毙在此的话,躺在她倒下时人家为她让开的一块墓穴一样狭窄的空地,那些显然腾不出地儿给她的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等着谁第一个出手相救。排副出了手。
“总得把她扶起来吧,”他怒斥道,“把她抬走,免得在大街上被踩着了。”一名男子走上前,但他和排副刚弯下腰,那女人却睁开了眼睛;排副去拉她的时候,她甚至挣扎着自己站起来;排副的态度算不上粗暴,不过是见不得、想不明白老百姓始终那么糊涂愚笨,尤其是这种时候,害得他丢下岗位不得脱身。“她是谁家的?”他问。没有人应,只有一张张默默关切的脸。他分明也不指望有人应。他四下打量了一眼,他心里也明白,就算有人站出来照看她,恐怕也没办法把她带出人群;他又开了口,这次是对她,但很快又忍着怒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男人身材魁梧,四十上下,蓄着一部胡子,透着西西里的土匪的匪气,他一身军装、胸戴世界三大洲的军功绶带,他的身材让一百年前的拿破仑矮了两三英寸,就好似恺撒让意大利人矮了三分,汉尼拔功高无名豪杰三分。要是换在巴黎的会所,他和巴黎的会所要是换在别处,他本应是一位看管酒桶的人夫人父。排副又瞥了一眼一张张耐着性子的面孔。“有谁——”
“她是饿的。”不知谁说了一声。
“那好,”排副说,“有谁——”话音未落,一只手递过来一块面包。或者说没吃完的面包,还沾着泥巴,甚至还带着口袋里的余温。排副接过了面包,谁知他递给她的时候,她却不肯接,脸和眼睛略显惊恐、飞快地瞥了一眼四周,像是在找一条逃路。排副将面包塞在她的手上。“拿着,”他粗声粗气地说,话不中听,但并不冷漠,不过是性子急了些,“吃吧。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还得待在这里,还得瞧着他。”
谁知她又不肯接受,推开了面包,她针对的不是这份馈赠,而是面包,也不是针对给她的人,她针对的是她自己。她强忍着不去看那块面包,但她也清楚自己欲罢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不再赌气。她嘴上推辞,眼睛、全身却跟她作着对,不等她伸手去接,眼睛就恨不得将面包吞了下去。她一把从排副手中抓过面包,双手捧到脸前,生怕人家抢去似的,又好像不想人家看见她狼吞虎咽。她像老鼠一样啃着面包,眼睛不时地从指缝里飞快地瞥一眼,说不上偷偷摸摸,也说不上遮遮掩掩,不过是不安、警惕和惊恐,好似吹着一块时旺时灭的炭火。她这会儿再无大碍,排副转身要走,同一个声音现在又开了腔。说话的分明是拿出面包的男人,不过,就算是排副说的,也丝毫看不出来。但他刚才分明说过,这张脸不该出现在这儿,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不仅仅在法国,而且在五月末不论哪一个星期三的四十公里内的西线。相比身边星期三这天赶到这里的其他人,这男人其实并不年轻,但却不显老(他身材高大,清清爽爽),他穿着一件泛白的罩衫、一条粗布裤子和一双污渍斑斑的鞋,俨然一副养路工人,或是泥水匠的打扮,往那儿一站,显得高大挺拔、落落大方。他想必是一位因伤安然退役的军人,自从将近四年前的八月五日后再也不用服役,就算如此,却也看不出,如果排副说过这话,有此想法,那不过是从他一闪而逝的眼神中露出的端倪。那男人第一次开口,是对排副说的;这一次,排副不再怀疑。
“她吃了面包,”那男人说,“垫巴了肚子,想是不那么难过了,不是吗?”
排副其实已转过了身,正要离开,是那个声音、嘟哝让他停下了脚步。这声嘟哝,与其说轻柔,倒不如干脆说沉着;与其说迟疑,倒不如说和蔼、矜持,最关键的是天真。他转身前的一刹那,瞬间的犹豫,他能明白、感觉身后的一张张安静、关切的脸都在看,看的不是他,也不是说话的人,就如同望着那人的声音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营造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接着,排副也看到了。是他身上穿的衣服。他扭头望着说话的人和他身边的一张张面孔,那神情如同出于尝够艰辛、不知何时是头的磨难和不幸,见怪不怪,这时候恰好浮上心头,甚至都不无懊悔地望着二十年前他不单投身也放弃了的天职和生计,不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血肉之躯这道不可逾越的藩篱对面的全人类;在他看来,那一圈平静、关切的脸泛着一层抹之不去、淡淡的铁青色。一向如此;变的不过是色调,沙漠和热带地区的淡黄和白,旧军装鲜艳饱满的红和蓝,三年来变色龙一样的铁青色。他早就料到,不单是料到,而是认命,断了想头、忘了饥饿、丧失了决心,到了一天领几个苏
 这点实惠和权利,只需服从命令、抛头露面、不惜脆弱的血肉之躯,一辈子放弃一己之好的地步。二十年来,他如同一个无名无分的外来人,高高在上,有几分瞧不起这说不上名儿来的蛮夷的世态,单说不幸吧,他和生死与共的兄弟凭着勇气和忍耐跟着无坚不摧的星条旗、勋章和绶带迎难而上,挺过了难关,就仿佛一艘巡洋舰(或者说,一年前的坦克)冲进鱼群。但现在却今非昔比。望着一张张焦急的面孔(除了那名年轻的女子;唯独她没看他,一双纤细、脏兮兮的手捧着一截面包啃着,所以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与这个非亲非故、叫不出名字的姑娘似乎站在一口狭窄、叫人喘不过气的井里),他不无惊恐地发现,自己才是个另类,不只是另类,还脱离了时代;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正义和机会渐渐荡然无存,换回来的是上衣胸口象征英勇、坚忍和忠诚的勋章,付出的是身体上的痛苦,出卖的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他没动声色。花花绿绿的绶带本身就说明他不能,戴在胸口的绶带证明他也不会。
这点实惠和权利,只需服从命令、抛头露面、不惜脆弱的血肉之躯,一辈子放弃一己之好的地步。二十年来,他如同一个无名无分的外来人,高高在上,有几分瞧不起这说不上名儿来的蛮夷的世态,单说不幸吧,他和生死与共的兄弟凭着勇气和忍耐跟着无坚不摧的星条旗、勋章和绶带迎难而上,挺过了难关,就仿佛一艘巡洋舰(或者说,一年前的坦克)冲进鱼群。但现在却今非昔比。望着一张张焦急的面孔(除了那名年轻的女子;唯独她没看他,一双纤细、脏兮兮的手捧着一截面包啃着,所以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与这个非亲非故、叫不出名字的姑娘似乎站在一口狭窄、叫人喘不过气的井里),他不无惊恐地发现,自己才是个另类,不只是另类,还脱离了时代;二十年前的这一天,正义和机会渐渐荡然无存,换回来的是上衣胸口象征英勇、坚忍和忠诚的勋章,付出的是身体上的痛苦,出卖的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他没动声色。花花绿绿的绶带本身就说明他不能,戴在胸口的绶带证明他也不会。
“怎么说?”排副说。
“是全团。”高个子男人用阳刚、豪爽、悦耳的男中音若有所思地小声说,“全团。零点时分,除了军官和少数几个士官,谁也没出战壕。有这回事吗?”
“怎么说?”排副又问道。
“Bosche
 干吗不动手?”高个子男人问,“难道他们看出我们不打算打过去?进攻出了什么情况?炮轰进展顺利,还有隆隆的掩护炮火,不料解除了炮火,只有排长爬出战壕,兵却一个没动?他们想必都看到了,不是吗?你们周三面临着另一个相距仅一千米、相持了四年的前线的时候,可以看出进攻失利,兴许也明白了个中的因由。你不能说是因为阻击火网;那是你首先跳出战壕冲向敌阵的理由,冒着不知哪一方的炮火,往往还是自己人的,不是吗?”
干吗不动手?”高个子男人问,“难道他们看出我们不打算打过去?进攻出了什么情况?炮轰进展顺利,还有隆隆的掩护炮火,不料解除了炮火,只有排长爬出战壕,兵却一个没动?他们想必都看到了,不是吗?你们周三面临着另一个相距仅一千米、相持了四年的前线的时候,可以看出进攻失利,兴许也明白了个中的因由。你不能说是因为阻击火网;那是你首先跳出战壕冲向敌阵的理由,冒着不知哪一方的炮火,往往还是自己人的,不是吗?”
排副独独瞧着那个大个子男人;不用看,他就能感觉到其他人屏住呼吸竖着耳朵一声不吭,生怕漏了一个字。“一位元帅,”排副不屑地说,“兴许该叫人家瞧瞧你制服里面了。”说着,他伸出了手。“叫大伙儿瞧瞧。”
大个子沉着、坦然地打量了他一阵。接着伸手从罩衫里摸出几张纸,递了过去。纸叠过,折缝磨出了毛、发黑,还卷了角。排副接过纸展开,但即使这个时候,他的眼睛似乎也没瞧着纸;而是飞快地又瞥了一眼一张张屏息敛容的面孔,大个子仍坦然地低头望着他,接着又含糊、坦然、近乎心不在焉地打了个哈哈:“昨天中午,除了做做样子,全线停火,隔一万米对一个炮阵放一炮,到了十五点,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停了火,等静了下来,你不难听到德国佬也是如此,所以到昨天日落时分,除了做做样子,法国全境难觅炮火的踪迹,他们尽量将时间间隔得长一些,生怕打破了时隔四年突然降临人间的寂静……”排副匆匆地合上文件,递还给那人,或者说显然如此,因为不等那人抬手去接,排副伸手抓住了他罩衫的前襟,攥住皱巴巴的纸和粗布衣服,猛地一拽,但险些摔了个跟头的是排副,不是大个子,排副凶神恶煞似的面孔与他相遇,张着露出一口发黑的烂牙的嘴,却又发不出声,因为那人坦然、不疾不徐地小声说着:“加尼翁少将率领全师人马赶过来向总司令请命,因为和平与寂静冷不丁地降临人间,人一时……”
“连一个元帅都不赞成。”排副义愤难平,愤愤地嘟哝了一句,声音并不高过对方,周围屏气凝神的人似乎没听见,或者说没听进去多少,抑或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听的是对方,年轻女人听没听见多少,不得而知,只见她泪流满面还在捧着面包啃着,仿佛一个聋子,目不转睛、好奇地望着他们。“你叫那帮孙子过来看看,是不是有人开了小差?”
“这事我也清楚,”对方说,“我不过说说罢了。你看过我的证件。”
“宪兵司令手下的副官也会这么说。”排副说着,愤然转身,攥着皱巴巴的证件,手肘并用地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返回了大街;接着,他猛然停住了脚步,伸头对着老城门方向,像是恨不得托起全身,高出挤挤挨挨的人头和面孔一截。接着,他们都听到了,不仅在交错的枪林下猫着腰归队的排副,连捧着面包的女人也停止了咀嚼,侧过了耳朵,人头和挤得密不透风的身体全都撇下她,转向大道,倒不是他们对她的苦楚无动于衷,不想安慰她一下,而是老城门方向现在沿街传来的一阵喧嚣,仿佛起了一阵风。且不说沿两边路牙一字排开的步兵班长、排长的嚷嚷,那喧嚣不如说是一声叹息、一声怨愤的宣泄,在星期三这天沿街从一个胸膛传到另一个胸膛。那声叹息仿佛揪了一夜的心,到现在才暂搁下来,新的一天即将揭晓夜间叫人心慌的事实,这恐惧渐渐加深,仿佛这新的一天、仿佛一波遮天蔽日的巨浪随第一辆进城的小轿车向人群席卷而来。
车上坐着三位将军。车开得飞快,快得连连响起各位排长此起彼伏的口令和各排咔嚓一声举枪敬礼又咔嚓一声收枪稍息,小汽车和着如同生着钢铁羽毛、无形的翅膀发出的一声拖长了的咔嚓声疾驰而过。这是一辆跟驱逐舰一样颜色的长敞篷车,车上飘着一面联军最高统帅的将旗,三位将军在一本正经、神气十足的副官的簇拥下并肩坐在车后座。这三位老人家分别指挥三支独立的军队,经各方协商一致和同意,其中一人统帅这三支军队(照理统帅半个欧洲的海陆空三军)——坐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中间的最高统帅:他头发微白,生着一副精明、睿智、多疑的面孔,除了自己的觉悟、才智和通天的权力,其他一概不信。三人掠过惊恐和诧异的人群,在班排长口令、马靴和步枪咔嚓的敬礼声中扬长而去。
卡车接踵而至,开得飞快,一辆紧接着一辆,似乎一眼望不到尾,因为出动了一个团。可惜仍听不到协调、明白无误的人声,这次连咔嚓的敬礼都没了,唯独人群的骚动和不断地挪移,人群仍诧异、将信将疑、默默、痛苦、恐惧地走向第一辆卡车,似乎要冲向每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将它包围,又紧追飞驰而过的车而去,偶尔因为一个人,兴许是一名妇女冲一张一闪而过的面孔呼唤一声才肯作罢。由于卡车开得飞快,还没来得及认清,这张面孔就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不等认出后发出一声呼唤,隆隆的下一辆车就已将它淹没,所以说,小轿车快,卡车开得更快,鉴于车头前方是半个懒散的大陆,这辆小车天生优哉游哉,而现在立刻就能猜出目的地的卡车只能让人羞愧难当。
车是敞篷,好像运牛车,架着高高的栏板,车厢内挤满了一个个光着脑袋、被缴了械、浑身带着前线硝烟的兵,他们胡子拉碴、满面倦容的脸上露出一副义无反顾和目空一切的神色,从没见过人,或者看不懂这些人,至少认不出他们是人似的愣愣地望着眼前的民众。他们如同回想梦魇的梦游者,认不出人和熟悉的事物,瞧着眼前飞逝、留不住的瞬间,仿佛赶去赴死,一个接一个匆匆地一闪而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分别,并非无视他们各有各的身份和姓名,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姓名;看不出分别并不在于相同的命运,而在于他们都以一个名字和身份归于同一种命运,归于最清净之地:忍得了人之将死的孤独——他们一闪而过,好像不关心,或者不在乎,甚至看不懂他们身处的乱哄哄的场面,以及隆隆挺进的速度,仿佛一个个幽灵鬼怪,也兴许是铁皮或纸板上刻得模糊的人物,在上演一幕悲情哑剧的舞台上一再被生生地绑走。这时候传来了一阵整齐划一的声音:中心广场方向隐约传来一阵嚷嚷,想是第一辆卡车现在到了那里。闹声很大,由于太远显得若有若无;拖着调儿,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挑衅,令人费解的是,同时还有着非人的特质,好像嚷嚷的不是那些兵,仿佛一阵突如其来、哗哗但和顺的春雨,仅仅借了他们之口。这阵嚷嚷其实发自驶过中心广场的第一批卡车,市政厅门前的三面旗帜下笔直地立着三名哨兵,晨风过后,三面旗帜静静地悬在旗杆上,年纪稍长一些的总司令上了门前的石台阶,止步转过身,跟他下车的两位年纪稍轻的将军,也跟着他转过了身,他们两人与他一样头发花白,站在高他一级的台阶上,所以高他一头,他们稍稍后他一步,但并非依次排开,第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车内光着头、衣衫不整、梦游似的士兵兴许是见到了三面旗帜,也兴许见到了人头攒动的大街后孤零零的三位老人,他们回过了神,总算回过了神,同时猜到、认出了三位衣冠楚楚的老人,不仅凭他们与对应的三面旗帜,而是凭他们远离人群,如同在人走一空的市中心的三名骇人的瘟疫携带者,或者在肆虐这座城市的瘟疫中安然逃过一劫的三个幸存者,又仿佛一张经历了这五六十年来的浩劫、渐褪了色的照片,最终安然无恙,不过,卡车中总算回过神来的士兵冲三个无动于衷的人影挥着拳头,异口同声,异口同声地喊着,随着鱼贯进入广场,继而疾驰而过的卡车加入了呐喊,喊声接力似的从一辆卡车传给下一辆卡车,直到最后一辆车仿佛拖着一团在劫难逃、有去无回的迷雾,迷雾中一副副张大嘴巴的面孔和气势汹汹的拳头一如卡车卷起的尘土渐渐散去。
这喧嚣仿佛灰尘,在开动、产生摩擦、结成队伍、产生冲力和速度的人或物一去不返后仍在空中久久不肯散去。整条街现在喊声雷动,并非出于反抗,不过是惊奇和疑惑,大街两旁现在挤满了挺着胸膛、张大嘴巴、振臂高呼的苍白面孔。又开过来一辆卡车。车开得飞快;虽说与前一辆相距二百码,但看那速度,似乎比其他车快了一倍,就好像其他车看起来比坐着三位将军、插了小旗的轿车快一倍一样。但这辆车却近乎悄无声息。好像见不得人似的。其他车公然抛下了羞耻和绝望,隆隆、几乎震天动地驶过,这一辆却来无声、去无踪,倒不是开车的司机讨厌要去的地方,而是憎恶车上载的人。
与其他卡车一样,车也是敞篷车,除了车上的人,看不出什么分别。别的车满载士兵,但独独这一辆只带了十三个。他们一样光着脑袋、蓬头垢面、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只不过戴着镣铐,野兽似的一个连着一个铐在车身上。乍一看,他们不单像一群外国人,而且形同别的种族、另一种人类;尽管他们的领章上写着同一个团的番号,但在该团始终先他们一步,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士兵眼中,他们是另类、怪物、异族。且不说他们戴着镣铐、无人愿意与之为伍,就凭他们的神色和态度,那些逃也似的卡车里的面孔茫然、神情疲惫,仿佛昏睡初醒,这十三个人却板着面孔、聚精会神。仔细再看,这十三个人中,的确有四个是外国人,说他们是外国人,不单单看他们戴的镣铐,全团人不屑与他们为伍,还看他们与卡车飞驰而过的这个城池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是四张山民的面孔,出自一个没有山的国度,这是四张农民的面孔,出自一个无人务农的国家;即便与另外九个戴着镣铐的兵相比,也属于异类,因为那九个人板着脸、小心翼翼,显得心事重重,那四个外国人中,有三个稍显迷茫,虽也赔着小心,但却显得彬彬有礼,好像在看稀奇,姑且这么说吧,他们好像第一次走进一座新奇的城市;这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嚷嚷,说的是他们不指望听懂,说句真格的,也不十分在乎的语言,因而也不在乎人家嚷了些什么;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不是法国人,这么说吧,就凭他不服人家的辱骂、流露的恐惧和愤怒,人群早看出第四个反正与另外三个不是一类。人群攥紧拳头嚷嚷,或辱骂的是这个人,而他却仅仅瞥了一眼另外十二个同伴。他靠近前排,手轻轻地扶着车厢板的顶端,连着两只手腕的链环和袖口缀的下士条纹一览无余,他生着一张与另外十二个人迥异、与上述三个人一样的山民面孔,年纪在十三个人中略显年轻,他与另外十二个人一样盯着茫茫一片、从眼前飞逝的眼睛、如洞的嘴和拳头。但他既不失魂落魄,也不害怕,露出的不过是一副急切、聚精会神和坦然的态度,外带含蓄、心领神会、超然这种另外几个人没有的神色,仿佛他早料到紧追着卡车不放的喧嚣,无须怪罪谁,也不必遗憾。
这辆车驶过中心广场的时候,三位将军依然跟摆好姿势,等着记者拍照似的伫立在市政厅门前的台阶上。看样子,不说三个外国人,除了迎着白天的回头风飘摆的一溜儿三面旗帜,十二个人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三面不一样的旗帜的意义,以及旗帜下立着三位扛着将星、戴着军帽的老人。看来唯独第十三个人注意、看到、发觉到了这一幕;由于车速太快,下士与这位老将军匆匆一个照面的一刹那,唯独下士的目光不经意地一瞥,其他卡车中的官兵恐怕谁也不敢说一定瞧过他,或者这位将军,飞驰的卡车中下士山形袖章和戴着镣铐的手腕上方那张农民的脸与市政厅门前的台阶上最高统帅将星和鲜艳的功勋绶带上方那张苍白、高深莫测的脸刹那间打了个照面。卡车很快绝尘而去。总司令他老人家转过身,两位同僚跟着他转身,一边一个分立左右;年轻、机灵能干的副官在三名哨兵立正敬礼的当儿腾地跳起身,打开了车门。
这一次的骚动几乎无人在意,不仅是因为嚷嚷和鼎沸的人声,还因为人群这时候也在挪动。又是晕过去的那个小女人。最后一辆卡车开过来的时候,她还啃着面包。见到卡车,她住了口,紧挨她的人事后记得她站起身、喊着叫着,拼命地分开人群,想要拦住或追上那辆卡车似的跑上大街。只是大家这时候都涌向了大街,连被她挠着、扒着后背,以及含着一嘴面包冲人家嚷嚷、被她喷了一脸面包渣的人都跟了上去。除了给她那块面包的男子站在原地,谁也顾不上她,而她却用攥着面包的手不停地捶着他的胸口,含着一口黏糊糊的面包冲他吼着什么。
接着,她一口将面包渣吐在他的身上,说是故意,那是冤枉了她,她顾不得扭头吐掉面包,口沫、面包渣飞溅地冲他吼了一通。那男子抬手用衣袖揩了一把脸,去追人群,在好不容易冲破交织的枪林、涌上大街的人群中一闪,不见了踪影。她捏着剩下来的一截面包,也追了过去。有一刻,她甚至追上了他们,分明有比他们更要紧的事似的,在跟着疾驰而过的卡车涌上大街的人群中飞奔。可惜她超过的人很快又一个接一个地赶上了她、超了过去。不一会儿工夫,她就落在了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队尾,她跌跌撞撞、气喘吁吁、没了力气,好像与全市、全世界民众的方向背道而驰,等她好不容易赶到中心广场,停下脚步,好像全人类都一走而空、不见了踪影,又留给她一条宽阔、空荡荡的大街和广场,那一刻,甚至可以说这座城市和地球,只剩下一个娇弱的女人,绞着手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或者说还是个姑娘家,一位原本俊俏的姑娘,只缺一个觉、一顿饭,一盆热水、一块肥皂和一把梳子,否则她又能焕发当初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