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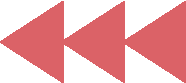
“日安!”德法日先生往下瞧着那低俯着做鞋的苍白的头,说道。
那头抬起一会,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回应了这一问候,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
“日安!”
“原来你还在忙着干活啊?”
沉默很久之后,那头又抬起一会,那声音答道,“是的——我在干活。”这次一双深陷的眼睛瞧了瞧问话的人,才再次低下头。
那有气无力的声音既可怜又可怕。不是由于身体虚弱那种有气无力,虽然监禁和粗劣的饮食无疑有一定关系。那声音的可悲的独特之处是,那是由于与世隔绝,长期不说话而形成的。它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发出的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声。它完全丧失了人声的活力和共鸣,使人觉得它像一块原来很美的色彩,后来黯淡失色,成了一抹污迹。它是那么深沉,压抑,就像从地下发出来的声音。它那么真切地表现了绝望的迷途的人的声音,一个孤独地在荒野上彷徨,走得精疲力竭,饿得半死的旅客,在倒毙前,就会用这种声音怀念家和朋友。
在默默地工作了几分钟之后,那双深陷的眼睛又往上瞧:并非出于兴趣或好奇,而是先出于迟钝的,机械的感觉,意识到那位唯一的来客所站的地方,还没有空。
“我想,”德法日说道,他一直注视着这个鞋匠,“把窗开大一点亮一些。亮一些你受得了吗?”
鞋匠停下工作;茫然地听着,一会瞧瞧他一边的地板,一会又瞧瞧另一边的地板,然后仰望着说话人。
“你说什么?”
“亮一些你受得了吗?”
“要是你开亮些,我就得忍受。”(“就得”这个词,略微说得重一些。)
他把那半扇打开的窗门再开大一点,暂时固定在那个角度上。大量光线照进这间阁楼,照见了这个鞋匠,暂时放下工作,膝上放着一只未做好的鞋。脚下和凳子上散放着几件普通工具和各种各样的碎皮块。一部白胡子,剪得参差不齐,但不很长,双颊下陷,眼睛特别明亮。在那仍是黑色的眉毛和蓬乱的白发下面,他那瘦骨嶙峋的脸可能使眼睛显得很大,虽然它们本来的确不是那样;不过,它们天生就大,现在显得不自然的大罢了。他那件破烂的黄衬衣,衣领敞着,显出他的身子枯瘦不堪。他,他那件旧帆布工作服,他那双松松垮垮的长袜,以及他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由于长期不直接接触阳光和空气,都已褪成羊皮纸黄色,浑然一体,很难对它们加以区别。
他把一只手举在眼前,遮住光,那手的骨头似乎透明。他放下工作,这样坐着,两眼发呆。他总要先看看这一边的地板,又看看另一边,才看他面前的那个人影,好像他失去了凭声音定位的习惯;他总要先这样看来看去,才说话,于是忘了说话。
“今天你要做完这双鞋吗?”德法日问道,一边打手势要洛里先生过去。
“你说什么?”
“今天你打算做完这双鞋吗?”
“说不好。我想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一问倒使他想起他的工作,于是又埋头干起来。
洛里先生把那个女儿留在门边,悄悄走过去。他在德法日身边站了一两分钟之后,鞋匠才抬头往上看。他看到另一个人影并不显得吃惊,不过这时他一只手的手指晃晃悠悠晃到唇边(他的嘴唇和指甲都是铅灰色),随即落到他的活计上,又埋头做鞋。这一看一动之间不过顷刻工夫。
“有位客人来看你,你瞧。”德法日先生说道。
“你说什么?”
“来了客人。”
鞋匠像刚才那样抬起头,但他的手并没有离开他的活计。
“嗨!”德法日说道,“就是这位先生,他懂行,鞋做得好不好,他一看就知道。把你做的那只鞋给他看看。拿着,先生。”
洛里先生接过鞋拿着。
“告诉先生,这是什么鞋,制鞋人的名字。”
停顿了比往常更长的时间之后,鞋匠才答道:
“我忘了你问我什么事。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你能不能给先生说一说这是什么鞋?”
“这是女士鞋。是年轻小姐穿的便鞋。现在流行的式样。过去我还没见过。我这里有一个鞋样。”他瞧了那只鞋一眼,闪过一点得意的神色。
“制鞋人的名字?”德法日说道。
既然他手里没拿着活计,就拳着右手放在左手心里,又拳着左手放在右手心里,然后摸摸长胡子的下巴,这样不停地有规律地倒来倒去。要使他从说话时常常陷入的走神状态中清醒过来,有如使一个很虚弱的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或由于希望获得什么秘密,竭力留住一个快死的人的灵魂一样困难。
“你问过我的名字吗?”
“的确问过。”
“北塔楼,一百零五号。”
“就这个名字?”
“北塔楼,一百零五号。”
他发出一声既非叹气,又非呻吟的疲倦的声音,又埋头干活,直到又打破沉默。
“你的职业不是做鞋的吧?”洛里先生直瞧着他,说道。
他那双深陷的眼睛转向德法日,好像这该由他来回答,既然他不帮忙,那双眼睛往地板上看来看去之后,又转向发问人。
“我的职业不是做鞋。不,我过去的职业不是做鞋。我——我在这儿学的,自学的。我要求允许我——”
他走神了,甚至长达几分钟,这时他一直重复那一套有规律的两手倒来倒去的动作,他的眼睛离开那张脸看来看去之后,终于又慢慢转向那张脸,一停到那儿,他吃惊了,仿佛睡觉的人刚醒,又回到昨夜的话题似的。
“我要求准许我自学,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得到准许,从此我就做鞋了。”
当他伸出手要那只从他那里拿去的鞋子时,洛里先生仍直瞧他的脸,说道:
“马内特先生,你一点也记不得我了吗?”
那只鞋掉到地上,他坐着定定地瞧着发问的人。
“马内特先生,”——洛里先生把手放到德法日的胳膊上——“你一点也记不得这个人了吗?看看他。看看我。难道你心里就想不起过去的老银行职员,过去的业务关系,过去的仆人,过去的年月,马内特先生?”
这个被关了多年的囚徒目不转睛地一会看着洛里先生,一会看着德法日,这时,那前额当中早已消失的,活跃而专注的智力的标志,渐渐强行透过罩住他的黑雾。那些标志又被雾罩住,暗淡了,消失了;但它们出现过。那位小姐年轻美丽的脸上也丝毫不差地重复出现那样的表情,因为她已经顺着墙悄悄走到能看见他的地方,这时正站在那儿瞧着他,她举起手来,最初只是出于惊惶的怜悯,即使不是为了避开他,挡住不敢看他,这时,向他伸过去,由于急于要把那幽灵似的脸搂在她温暖年轻的怀里,急于用爱使他恢复生机,恢复希望而发抖——她美丽年轻的脸上那样丝毫不差地重复出现(只不过那些特征更鲜明)那样的表情,看来它就好像一道移动的光,从他那儿移到了她身上。
阴暗又罩住他的前额。他瞧着他们俩时,越来越走神了,他的眼睛又像先前那样,蒙眬,茫然地往地板上,往他的周围,看来看去。最后,长叹一声,拿起鞋,又干起来。
“你认出他了吗,先生?”德法日悄声问道。
“是的;有一会。最初我以为毫无希望,但是,就一会,我的确看见了过去我很熟悉的脸。别做声!咱们往后退一退,别做声!”
她已经离开了墙边,走到他坐的板凳前。他埋头工作时不知道这个人影会伸出手摸他,这有些可怕。
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弄出响声。她像幽灵似的站在他旁边,他埋头干他的活。
他终于需要换手上的工具,要用鞋匠刀。刀在他身边,但不在她站的那一边,他拿起刀又埋头工作时,他的眼睛看见了她的裙子。又抬起眼睛,看到她的脸。那两个旁观者正要上前,但她打了个手势止住他们。她并不怕他拿刀砍她,但他们怕。
他露出可怕的神色凝视着她,过了一会他的嘴唇动了动,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声来。在他急促、吃力的呼吸的间歇中,渐渐听到他的声音:
“怎么回事?”
她的眼泪滚滚直流,一边把两手举到唇上吻一下飞给他;随即把两手抱在胸上,仿佛搂着他那被毁的头似的。
“你不是看守的女儿吧?”
她叹息着说,“不。”
“你是谁?”
她仍信不过她的嗓子,怕泣不成声,便挨着他在板凳上坐下。他躲了躲,但她扶住他的胳膊。这引起他一阵异样的战栗,又明显地传遍全身;他一边凝视着她,一边轻轻地放下刀。
她匆匆撩开她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披到脖子上。他的手一点,一点挪过去,拿起她的头发看。正看着就走神了,接着长叹一声,又开始做鞋。
不久,她放开他的胳膊,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怀疑地对那手看了两三次,仿佛要看准它确实在那里,才放下他的工作,把手伸到脖子上,取下一根弄黑的细绳,绳上系着一块叠好的破布。他把它放在膝上,小心地打开,破布里包着一点头发:不过一两根金黄色长发,这是他在多年前的一天从他指头上解下来的。
他又把她的头发拿在手里,仔细看着。“一样的头发。怎么可能呢?那是什么时候?那是怎么回事?”
他的前额又出现专注的神情,他似乎意识到她的前额也有这种神情。他把她转过去全身对着光亮,看着她。
“我应召出去那天晚上,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去的时候,她很担心,但我不担心——后来,把我带到北塔楼,他们发现我袖子上有这两根头发。‘你们把这两根头发留给我吧?这决不能帮我的身体逃出去,虽然会帮我的灵魂逃出去。’这是我当时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
他的嘴唇,动了多次,才说出这番话来。不过,他一说出口,就连贯地想起那些词,虽然很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你?”
当他可怕地突然转向她时,那两个旁观者再次吃了一惊。她任他抓住,坐着一动不动,只低声说,“恳求你们,好心的先生,别走近我们,别说话,别动!”
“听啊!”他叫道,“这是谁的声音?”
他边叫边松开抓住她的手,又抓住他的白发一阵乱扯。如同除了做鞋而外,一切都从他心里消失一样,这阵狂乱平息了,他把那小包叠起,打算放到怀里保存好;他仍瞧着她,阴郁地摇摇头。
“不是,不是,不是;你太年轻,像盛开的花朵。不可能。瞧瞧我这囚徒是什么样子。这不是她熟悉的手,这不是她熟悉的脸,这不是她听过的声音。不,不。她原来——他原来——在北塔楼过那些难熬的日子之前——多年以前。你叫什么名字,我温柔的天使?”
由于他的口气和态度变得温和了,她跪倒在他面前,两手乞求似的放在他的胸口上。
“啊,先生,以后你会知道我的名字,我母亲是谁,我父亲是谁,还有我从来不知道他们那苦难的经历的原因。不过,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在这里我不能告诉你。现在,在这里,我只能告诉你,我求你挨着我为我祝福。吻我,吻我!啊,亲爱的,亲爱的!”
他那冷冰冰的白头和她那金光闪闪的头发混在一起,她的头发温暖并点亮了那白头,仿佛那是在他身上闪耀的自由之光。
“要是你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愿是这样——要是你听我的声音,跟你曾经听来像甜美的音乐一般的声音,有些像,为此哭吧,为此哭吧!要是你摸着我的头发,有所感触,使你想起你年轻,自由的时候,躺在你怀里的可爱的头,为此哭吧,为此哭吧!当我向你暗示,不久我们就有一个家,我会尽心尽力孝敬你,侍候你,要是引起你对一个早已破败的家的回忆,而你那可怜的心已衰弱不堪,那么,为此哭吧,为此哭吧!”
她更紧地搂着他的脖子,把他像小孩子似的搂在怀里摇着。
“当我告诉你,最最亲爱的,你的痛苦已经过去,我到这儿就是为了带你脱离苦海,我们到英国去过和平、安宁的生活,要是我使你想到你被毁了的本来有作为的一生,想到我们的祖国法国对你这样恶毒,那么为此哭吧,为此哭吧!当我以后告诉你我的名字,我还活着的父亲,已去世的母亲,要是你知道,由于我那可怜的母亲的爱,对我隐瞒了他遭受的痛苦,因而我从来没有为他终日奔走,彻夜不眠,哭泣,为此我必须向我尊敬的父亲下跪,乞求他宽恕,为此哭吧,为此哭吧!为她哭,再为我哭吧!好心的先生们,感谢上帝!我感到他那神圣的眼泪流到我脸上,他的抽泣撞击着我的心。啊,瞧!为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他已倒在她的胳膊里,脸落在她胸上;这一情景是如此感人,然而在此之前所蒙受的奇冤和巨大痛苦又那样可怕,那两位旁观者都蒙住了脸。
阁楼里的安静很久未被打搅,他的起伏的胸部和抖动的身子也早已屈从于一切暴风雨——人性的象征——之后必然出现的平静,就像那称为“生命”的暴风雨最终必然要静下来那样安息,寂然无声;这时他们走过去,准备从地上扶起父女俩。原来,他已慢慢滑到地板上,昏昏迷迷躺在那儿,已经精疲力竭。她也跟着他一起躺下,他的头才能靠在她的胳膊上;她的头发搭在他身上,像窗帘似的给他挡住光。
“要是不惊动他,”她一边说,一边向洛里先生举起手,他在反复擤过鼻子后向他们俯下身子,“能马上安排好离开巴黎就好了,我们可以从这个门把他送走——”
“不过,要考虑考虑。他适于旅行吗?”洛里先生问道。
“对他来说,这个城市太可怕了,我认为,旅行比留在这里更合适。”
“对,”德法日说道,他正跪在那儿旁观,旁听,“岂只合适;无论凭什么理由,马内特先生最好离开法国。我说,我去雇一辆马车和几匹驿马,好吗?”
“这是正事,”洛里先生说道,他一听这话马上恢复了有条理的态度,“既然有事要办,我还是办事吧。”
“那么,”马内特小姐恳求道,“请让我们留在这儿,你们瞧,他现在多镇静,现在让他跟我在一起,你们不会担心了。你们干吗要担心呢?如果你们把门锁上,保证别人不会打搅,等你们回来时,你们准会发现他跟你们离开时一样安静。无论如何,我要照顾他,直到你们回来,然后我们马上把他送走。”
洛里先生和德法日都不愿意这样办,主张他们当中留下一个。但是,不仅要雇马车,还要办旅行证件,而且天快黑了,时间紧迫,他们终于急忙把必须办的事作了分派,匆匆离开,分头去办事。
天渐渐黑了,女儿挨着父亲躺在坚硬的地面上,守护着他。天越来越黑,他们俩这样静静地躺着,直到墙上的裂缝透进一点亮光。
洛里先生和德法日先生已作好旅行的一切准备,还准备了旅行斗篷,披的围的东西,夹肉面包,葡萄酒和热咖啡。德法日先生把这些食物和他带来的灯,放在板凳上(阁楼里除了一张干草铺的床,什么也没有),接着,他和洛里先生唤醒这个囚徒,把他扶起来。
无论多高的智力,都无法从他脸上那恐慌的茫然的惊奇中,看出他心里的隐秘。他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否记得他们跟他说过的话,他是否知道他已获得自由,这些都是最精明的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他们试着跟他说话;但他是那么慌乱,回答得那么慢,看到他那样困惑,他们吃了一惊,都认为,暂时不宜再打搅他。有时,他两手抱着头那副狂乱,迷惘的样子,过去还从未见过,不过,他还爱听他女儿说话,哪怕仅仅听声音,而且她一说话,就总是转过身去听。
由于长期在淫威下服从惯了,他还是那样驯服地吃喝他们给他吃喝的东西,穿上他们给他穿的斗篷和其他披的围的东西。他女儿伸手挽住他的胳膊时,他马上作出反应,用两手抓住那只手——抓住不放。
他们开始下楼;德法日先生拿着灯走在前面,洛里先生殿后。他们由那长长的主楼道下去,没有走几步,他就站住,凝视着屋顶和四周的墙壁。
“你记得这地方,父亲?你记得在这儿上楼?”
“你说什么?”
可是,还没有等她再问,他就喃喃地做了回答,仿佛她又问过了。
“记得吗?不,我不记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在他们看来,显然他一点也记不得把他从监狱带到这座楼房的事。他们听见他喃喃地说,“北塔楼,一百零五号”;当他看四周的墙壁时,显然是把它当作那曾经长期关过他的坚固的城堡墙。他们走到院子之后,他本能地放慢了脚步,仿佛在等待放吊桥;既然那儿没有吊桥,他却看见一辆马车在街上等着,便放下他女儿的手,又抱住头。
门口附近没有人群,那许许多多窗户,看不见一个人影;街上连偶然过路的人也没有。一片反常的寂静和荒凉。只看见一个人,那就是德法日太太——她靠在门柱上编织着,什么也没有看见。
这个囚徒上了车,他的女儿也跟着上了车,洛里先生刚上踏板就给止住了,因为囚徒可怜巴巴地要他做鞋的工具和那双未做完的鞋。德法日太太马上叫他的丈夫,说她去拿,便一边织着,一边离开车灯照着的地方,穿过院子。她很快就把那些东西拿下来,递进车里,然后马上又靠在门柱上编织,什么也没有看见。
德法日上了驾驶座,便吩咐“到关卡!”马车夫一甩鞭子,他们在微弱的过于摇晃的灯光下,咔哒咔哒地驶去。
在那过于摇晃的灯光下——在路面较好的街上晃得更亮,在较坏的街上,则晃得更暗——经过点着灯的店铺,快乐的人群,灯火通明的咖啡店和剧院大门,来到一个城门。士兵们提着灯站在那儿的警卫室旁边。“证件,旅客们!”“这儿,长官先生,”德法日说着,下了车,严肃地把他带到一边,“这就是里边那位白头先生的证件。这是由——连他一起交给我的。”他放低了声音,这时那些军用提灯当中出现了飘动,其中一盏由一只穿制服的胳膊提进了马车,与那只胳膊相关联的一双眼睛,用不同于日日夜夜例行检查的目光,瞧着那位白头的先生。“行啦,走吧!”那位穿制服的说。“再见!”德法日说。于是,从一小片灯光越来越微弱的过于摇晃的路灯下,来到一大片星斗之下。
到了这满天一动不动的永恒的星光之下:有些星星离这小小的地球太远,据学者说,它们的光至今还不一定照到它,虽说它只是宇宙中一个小点,那里却受尽苦难,也无所不为:夜的阴影既大又暗。从这段寒冷、不安的历程,直到黎明,这些阴影再次在洛里先生耳边悄悄地说个不停——他坐在这个被埋葬后又挖出来的人对面,捉摸着,不知道他永远丧失了哪些不可思议的能力,又有哪些可以恢复——还是问那些事:
“我希望你愿意起死回生吧?”
还是那样的回答:
“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