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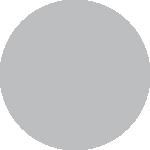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
无论上面这句话是王维说的,还是借着王维的名说的,其广为流传本身就说明了水墨一道在中国画中的地位。
水墨最为上,这一“上”字,指的当是品级的高下,是一种至高的境界。简要地来说,这一“上”大约包含了二层意思。其一是指“不易”,其二是指“耐看”。
说水墨不易,有时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因为中国画绘制程序上,水墨是前提——除了没骨一道外,无论最终的完成品是浅绛,还是青绿,或者水墨,其前道工序都是水墨;因此,仅从程序上来说水墨应该并不难,不仅不难,而且是每一位从事中国画的人都能画的。但是,同样几乎所有的画家又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水墨要比着色难画。这个“难”,一方面是因为手段单一。画面上只有墨色,也就意味着只有用这单一的色彩来表现斑斓的现实世界。尽管很早我们就有了“墨分五色”的论述,依然改变不了仍然是墨色这一事实。因此,如何用墨色来应对色彩,依然是每一位画家都要自己来解决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突显线条的地位。画者,形与色也。既然缩减了色彩,那么,造型的线条也就首当其冲了。以不同的线质表现事物不同的形质,这就要求画家笔下的线条既要有丰富的变化,又要保持线条的独立审美。
说水墨耐看,其实是指水墨更经得起品味。水墨放弃了色彩,只保留单一的墨色,这既是手段的缩减,也是手段的纯粹。自然造化固然有其自成其样的色彩节奏,但并非都能照搬到画面上,亦即绘画作为一件独立的作品自有其作为绘画的色彩节奏——通常这被称为绘画性。画面中的自然性和绘画性,是一个需要用心性来协调的问题。对水墨山水来说,协调造化的斑斓与水墨的单一的要求显然更高了,亦即要求画家有更丰赡的心性修养,而这或许也正是水墨被称道的缘由之一。换言之,这是排除了由色彩还原带来的直接的官能的愉悦之后的直诉心性。心绪性情是真切的、微妙的,也是复杂而难以道述的,水墨正是凭依着柔软的毛笔、敏感的宣纸、在不定流变的水媒介作用下,成为心性传达的有效途径。所谓“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说的便是以线为本的书画可以“如其人”,而“如其人”的“人”同样不是其外表,而是心性。水墨因其缩减色彩的辅助而更加注重线条表现力的提炼和运用:线条的徐疾、轻重、浓淡、干湿,和由此构成的律动、节奏、旋律是与心绪性情最为契合的。在《诗·大序》中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线条,正是这“舞之蹈之”的迹痕,当线条糅合了心绪性情后,便有了一咏三叹的隽永意蕴,而艺术中所说的品味,所指于此。
山水,是造化,更是精神。
山水,不仅是自然景致,更是精神家园。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山水田园诗,在中国文化的演化历程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敬鬼神而远之”的春秋时期开始,中国文化的焦点就不再是人与神灵的关系,而是人与天的关系。在“天人合一”的先行观念引导下,对造化自然的感悟,便成为究天人之际的有效途径——我们深信“道法自然”。因此,登山临水可以悟道,图画山水同样可以悟道。宗炳的“畅神”说,早在山水画尚未抵达其成熟之时,就标划了其终极的理想。魏晋以来,山水画的历史就不是在探索其理想目标,而是在不断寻找抵达理想境地的技术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山水画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技法演化史,以至于在整个山水画历史中积淀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技之至者可以达乎道。技法,成为了一种绘画力须解决的问题。
注重技法,其实就是注重“舞之蹈之”——心绪性情的表达。从这一意义上说,技法虽是技法,却又不仅仅是技法。
说技法是技法,是因为山水画是借助自然景观来表达内心的,因此,不能脱离自然造化(如果脱离了自然造化,绘画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因为,我们还有一门抽去具体形象的表现艺术:书法。亦即脱离具体形象,绘画不可避免地会被书法收编)。因此,技法不仅是可以传承的,而且也是共时并存的。
说技法不仅仅是技法,是因为作为“舞之蹈之”的一种表现或呈现,乃是由每个人的心性所决定的。因此,在共同的技法规范——程式中,注入了个人的心绪性情,此时的技法就不能为造化的形貌所拘囿了;而形貌之外的神韵,也就成了技法的引导。以“神韵”为要求指向的技法,有一个更具体的代名词:笔墨。换言之,作为“笔墨”乃是以神韵为指向的技法,或者说是能承载体现心绪性情的技法。从这一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绘画史大体就是一部绘画技法史;而一部绘画技法史大体也就是一部绘画神韵史、一部绘画心性史。
缘此之故,绘画技法既是最基础的,又是最深邃的。因而,斗胆承应这部书稿,并不是有多少值得分享的经验,而是希望借此向同道同好讨教,期待大方之家的不吝教正。
邵琦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