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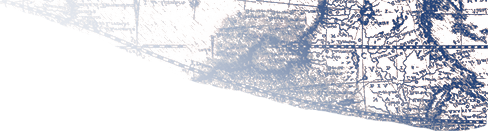
偷渡客雅各布决定在离境前找个姑娘度过最后一夜。
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境附近,许多准备去肯尼亚讨生活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最后一项支出是,跑到小酒馆里再亲近一次本国的姑娘。
他们之所以这样,源于两国社会触目惊心的差距。
在肯尼亚,卖淫在法律上是禁止的,虽然在地下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子并不少,但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在东非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殊服务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异乡的打工仔舍不得把钱投入到这昂贵的欢愉之中。
而在埃塞俄比亚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国家地处内陆高原,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加上历经数十年的战乱,如今是非洲东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灾荒年里,女孩子被迫卖淫补贴家用,据说最便宜的时候每次的费用只有1美元。也正因为贫穷,卖淫目前在埃塞俄比亚也是合法的,政府曾经数次讨论要废除卖淫的合法化,但都由于社会反弹而作罢。
2014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由于那几年经济发展不错,一夜风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00比尔(人民币65元左右)。对于即将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这个价格仍然是值得的。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侧的小旅馆里,整整一夜紧紧搂抱着姑娘,恨不能将她们的每一寸肌肤都探索清楚,将每一丝感觉都纳入长久的回味之中。他们第二天就要到达异国的土地,也许几年内都无法亲近女人。
雅各布也遵循着这个规律,找了一个女人。
雅各布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在埃塞俄比亚的小城和乡下,大部分的旅馆都兼做妓院生意。这种小型的旅馆一般都有一个院子,院子周围是几间客房,在临街的一侧有一个小餐馆,餐馆白天卖饭,晚上做酒吧。穿着廉价鲜艳衣服的姑娘们就在酒吧里和客人谈生意,然后入住后面的房间。
我和雅各布是在离境前的那一天,在从迪拉到亚贝洛的车上认识的。那一天,我从沙舍默内出发,换了三趟车才到达亚贝洛。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我邻座的青年建议我和他一同寻找住处。他就是雅各布。
跟随着他,我找了一家便宜但是典型的小旅馆住下。为了表达感激,我请雅各布吃了顿晚餐。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偷渡客,准备去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讨生活。
他的英语很不流利,但加上手势可以交流。
吃完饭,雅各布决定去找姑娘度过出国前的最后一夜。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前后(北京时间凌晨2点),旅馆的餐馆已经改成了酒吧,雅各布点了两瓶啤酒,坐下望着角落里几位绚丽的姑娘。
从长相上看,姑娘们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下。埃塞俄比亚人种介于白色和黑色中间,是一种美丽的咖啡色,带着一种安于天命的善良表情。埃塞俄比亚的男人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显得英俊挺拔。比如雅各布,他高高瘦瘦,戴着墨镜,一副摇滚明星的模样。
在我离开酒吧回去睡觉时,雅各布看上了一个身材微丰的年轻女孩。与其他姑娘不同的是,这个女孩还在酒吧兼职做服务生,一眼看不出她是妓女。她美丽的面容甚至让我也感到心动。
但不管她长得怎样,价格都是固定的——每夜200比尔。
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洗漱时,看到姑娘从雅各布房间里出来。她看见我,莞尔一笑,又显得有些羞涩,转身回屋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雅各布出来了:“哦,纯正的埃塞俄比亚姑娘!来自贡德尔的小甜心!我一夜都没有睡!”他张着手臂动情地对我说,满怀着对夜间的留恋和对白天的憎恨。
我们在他的絮絮叨叨中上路。但慢慢地,雅各布对姑娘的感觉变了,最初他不断地用回味的语气表达着对姑娘的爱慕之情,可后来又忍不住开始贬低她。
“她只是个妓女,跟很多人上过床,她太熟练了,太没有羞耻感。”他总结说。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我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我是个男人,不能离开女人。”
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抱怨,却不忍心戳穿他的真实感受:这个马上就要去往陌生国度的青年在怀念即将离开的祖国。他多想留下,找个女人过日子,可是祖国却养活不了他,逼着他去别人的国家,还必须偷渡过去。他试图贬低祖国的一切,为自己的离去提供正当性,但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