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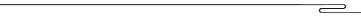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放弃了对主观性的深入辨析而走上了寻找客观性的普遍规则之路,这应当是康德的一大失误。在他为了说明定言令式而设计的四个例子里,除了说谎的例子之外,另外三个也同样是有马脚可寻的。第一个例子讨论的是主动求死的问题:
一个人,由于经历了一系列无可逃脱的恶邪事件而感到心灰意冷、倦厌生活,如果他还没有丧失理性,能问一问自己,自己夺去生命是否和自己的责任不相容,那么就请他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的行为准则是否可以变成一条普遍的自然规律。他的行为准则是:在生命期限的延长只会带来更多痛苦而不是更多满足的时候,我就把缩短生命当作对我最有利的原则。那么可以再问:这条自利原则,是否可能成为普遍的自然规律呢?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以通过情感促使生命的提高为职志的自然竟然把毁灭生命作为自己的规律,这是自相矛盾的,从而也就不能作为自然而存在。这样看来,那样的准则不可以成为普遍的自然规律,并且和责任的最高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

康德在这里为大自然预设了一条并不与之相符的特质,即“以通过情感促使生命的提高为职志”,他认为这样的大自然不可能“把毁灭生命作为自己的规律”,然而今天我们知道,生物体为了基因的复制或传递而牺牲生命的确就是大自然颠扑不破的规律。并不悲观厌世的雄螳螂在交尾之后被刚刚还在一起缠绵缱绻的伴侣吃掉,化作了后者身体内用以抚育后代的养分,甚至连微生物在种群面临危机的时候也会出现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的行为。
我们还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来质疑康德的这个例证,也就是把厌世者的那条行为准则—“在生命期限的延长只会带来更多痛苦而不是更多满足的时候,我就把缩短生命当作对我最有利的原则”——请每一个人回答,或者我们把它表述成“当生活变成无可避免且连续不断的酷刑折磨的时候,我就把结束生命当作对我最有利的原则”,我想除了一些极其坚韧的宗教人士之外,这的确会成为一条广为接受的普遍原则。即便表述为“在犯了违背道德和人情的严重罪行以后,自己悔恨,而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自杀寻死,借以忏悔罪过,像这样的自杀,就不一定是坏事”,若放到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文化里,想来会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事实上,引号里的这段话正是19世纪的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讲的。

古罗马有着极其相似的风俗,自杀在那里甚至是一种普遍的“习惯”。个中缘由,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多有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当就是对自尊的维护了。孟德斯鸠以富于诗意的笔调写道:“我们竟然这样尊重自己,那就是我们由于一种自然的和朦胧的本能而同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本能使我们爱自己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中国西汉时代的官僚阶层也是以同样的流行方式来维护自尊的,因为他们以接受司法调查为耻,后世的一些儒家学者对这种独特的历史风气颇为缅怀,认为这是士大夫高贵精神的体现。
中国西汉时代的官僚阶层也是以同样的流行方式来维护自尊的,因为他们以接受司法调查为耻,后世的一些儒家学者对这种独特的历史风气颇为缅怀,认为这是士大夫高贵精神的体现。
是的,若在生与义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孟子这样的人,不义而偷生正是“在生命期限的延长只会带来更多痛苦而不是更多满足的时候”,所以甘愿“缩短生命”;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吟咏的“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同样表达了求死的心志。他们当会认为,所有人在同样的情形下都应该做出相同的选择,否则才不符合正义的标准,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一个相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在行将就木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自我了断,以此为国家节约资源,这在许多人看来或许是相当高尚的。传说中斯巴达宪法的创始人,伟大的莱喀古士,在决定自我牺牲之前讲过如下的话:“一个有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一切能力都能够用于行善的目的,而在他毕生为他的国家服务之后,如果可能的话,他是应该使自己的死为国家谋求更多的利益的。”威廉·葛德文,这位信奉唯理主义的政治哲学家,认为自杀是我们的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所以应该受到道德的规范,自杀之前要审慎地权衡利弊才行——莱喀古士就是葛德文所列举的一位在自杀问题上的道德楷模。

“权衡利弊”,看上去这才是合乎理性的做法。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即便像洛克这样主张人既无权剥夺自己的生命,也无权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的伟大哲人,也认为当一个人因为做了坏事而理应处死的时候,他的生命权丧失给谁,谁就可以暂时饶过他的性命,让他为自己服役,“当他权衡奴役的痛苦超过了生命的价值时,他便有权以情愿一死来反抗他的主人的意志”。
 洛克的隐含道理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人因为犯罪该死,所以在理论上已经是个死人了,他因为不堪奴役而自杀,只不过是在事实上完成了自己的死亡。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所以在他活着为奴的时候,其实是作为死人而存在的。
洛克的隐含道理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人因为犯罪该死,所以在理论上已经是个死人了,他因为不堪奴役而自杀,只不过是在事实上完成了自己的死亡。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所以在他活着为奴的时候,其实是作为死人而存在的。
但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是自杀了,这是不是意志薄弱的体现呢?王国维曾撰文表达意志薄弱的结果,除了废学之外另生有三种疾病,即运动狂、嗜欲狂、自杀狂:
前二者之为意志薄弱之结果,人皆知之。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而意志薄弱之社会反以美名加之。吾人虽不欲科以杀人之罪,其可得乎?

撰写此文的20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遗书于三子贞明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只欠一死”之语出自吴梅村的名句“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那是明清易代之际,深负明朝皇恩的吴梅村当死而未死,这是否也是“意志薄弱之结果”呢?这样看来,人的“缩短生命”的企图,真的通不过康德的定言令式的考核吗?
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名被俘的士兵即将接受讯问,要他供出同伴的藏身之所,而他知道敌军掌握了一种人脑读取技术,可以获知任何人的秘密,所以,即便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御一切严刑拷打,但在这项高科技面前,再强大的意志力也无济于事。这时候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自杀的机会,那么,他该不该就此自我了断呢?
这是1955年一份基督教学刊提出的问题,“人脑读取技术”则是我的加工,为的是把问题简化,免得有人坚持说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原文作者怀有唯实论的态度,认为价值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问题里,“自杀”这件事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内在的恶”——无论任何人、任何情境,只要自杀,就是不对的。
同样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伦理学家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的发明人,则站在唯名论的一边指斥上述见解之僵化与荒谬。
 而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来解决这个问题:不错,自杀是恶,出卖同伴也是恶,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在这两件恶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若他选择了罪恶程度较低的那个,这个行为应该算善吧?—但是,如果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那么,即便在康德那里,道德上对“自杀”的禁令也就不再是不可动摇的了,而任何原本在定言令式的准绳之下被孤立权衡的事情如今都可以在“关系”当中被如此这般地重新考虑了。康德也许不会喜欢这样的事。
而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视角来解决这个问题:不错,自杀是恶,出卖同伴也是恶,但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在这两件恶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若他选择了罪恶程度较低的那个,这个行为应该算善吧?—但是,如果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那么,即便在康德那里,道德上对“自杀”的禁令也就不再是不可动摇的了,而任何原本在定言令式的准绳之下被孤立权衡的事情如今都可以在“关系”当中被如此这般地重新考虑了。康德也许不会喜欢这样的事。
我们继续看那个被俘士兵的例子,假设他深知敌军的人脑读取技术的厉害,于是为了不泄露军事机密,为使祖国免受致命的核打击,他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之后,他灵魂遇到了一位天使,天使赞叹说:“你真是太伟大了!”他淡然地说:“这不算什么,换作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恰恰是一个应用定言令式决定自杀的例子,看来定言令式不仅与“人是目的”这两条原则终于会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其本身也是很难自洽的。譬如,若墨子和杨朱分别学习了康德哲学,一起面对“要不要拔一毛以利天下”的道德抉择,墨子当然愿意“拔一毛以利天下”成为普遍原则,杨朱也当然愿意“不拔一毛以利天下”成为普遍原则,并各自坚信在自己的主张成为普遍原则之后并不会导致自我毁灭。或以罗素的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一个患忧郁病的人完全可能想要人人都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