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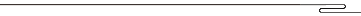
在康德设计的几个例子里,说谎的例子是最有名的一个。说谎是否道德呢?如果说谎变成了一条普遍准则,人人都说谎,那么谎话也就没人相信了。也就是说,在康德的规则下,说谎变成了一件自我毁灭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该说谎。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准则,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理解并便捷地采用。用康德的原话来说就是:
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来回答不兑现的诺言是否合乎责任的问题,我只须问自己,我是否也愿意把这个通过假诺言而解脱自己困境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规律;也愿意它不但适用于我自己,同样也适用于他人?我是否愿意这样说,在处境困难而找不到其他解脱办法时,每个人都可以做假诺言?这样,我很快就会觉察到,虽然我愿意说谎,但我却不愿意让说谎变成一条普遍的规律。因为按照这样的规律,也就不可能做任何诺言。既然人们不相信保证,我对自己将来的行为,不论做什么保证都是无用的。即或他们轻信了这种保证,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于我。这样看来,如果我一旦把我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那么它也就毁灭自身。因此,用不着多大的聪明,我就会知道做什么事情,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

康德的规则看上去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同一类型,然而康德是不赞成这一条古老格言的,因为“它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它既不包括对自己责任的根据,也不包含对他人所负责任的根据。好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除非他有借口不对别人做好事,别人也就不会对他做好事。最后因为,它不是人们相互间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那些触犯刑律的人,还会以此为根据不服法官的判决,逃避惩罚”。

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它太有功利性,甚至罪犯可以对法官说: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被人判刑,就请你也不要判我的刑。这样的逻辑自然无法被人接受,所以康德要找的是一个纯粹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著名的定言令式(又译作定言命令、绝对命令)。
但是,这一纯粹的道德规则也引来过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就近来说,桑德尔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朋友躲避追杀而逃到你家,杀手追到门口,向你打听你朋友的下落,那么你该不该说谎呢?——答案是:你依然不可以说谎,亦即不可以违背康德的定言令式,但你可以讲些“有误导作用的事实”。
邓晓芒举过一个贪污的例子以说明康德的过于形式主义的缺陷:譬如你受托保管别人的财产,你该不该中饱私囊呢?应用定言令式,如果所有受托保管别人财产的人都去贪污,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委托他人保管财产了,贪污这个规则也就自我毁灭掉了;但是,这个论证是以私有产权为前提的,如果换到公有制下,委托的财产就算被贪污了,但委托人还是有可能继续找人托管财产,因为财产反正不是自己的。
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我想症结主要出在表述方式上。在康德的说谎者的例子里,说谎者有其特定的处境,即“处境困难而找不到其他解脱办法”,所以他要用定言令式裁决的并不是简单的“是否应该说谎”,而是“在处境困难而找不到其他解脱办法时,我是否也愿意把这个通过假诺言而解脱自己困境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规律”。桑德尔则把问题过度简化为“是否应该说谎”,所以才会蹊跷地得出“在朋友被杀手追杀时,自己也不该对杀手说谎”的结论。
而所谓“有误导作用的事实”,既是“误导”,就已经怀了欺骗的动机,已经属于欺骗之一类;“以真话骗人”从来都是狡黠的人们相当擅长的事情,那么,难道说谎是不可以的,欺骗却是可以的吗?
对于桑德尔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前提下换一种表达方式,即“我该不该以说谎的方式做出有利于一个陷于急难中的朋友的事情?”或者索性换成“该不该保护朋友”,再以定言令式加以考核;同理,在邓晓芒的那个问题上,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具体的“贪污”换作其背后的更具实质性的抽象内容,亦即“我该不该做损害无辜者利益的事”,而这一标准对委托人当然也同样适用。种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问题都可以被抽象化地表述成“有利”与“不利”的问题,然后再代入定言令式做一番道德考察。
但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又会面临新的问题:“利益”究竟是什么?又该怎样衡量有利与不利?
譬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做素食主义者呢?”将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两个人都学过康德哲学,但一个是佛教徒,另一个是基督徒。佛教徒(这里特指中国的佛教徒)自从梁武帝以来就秉承素食传统,基督徒则相信《圣经》的话,上帝在洪水之后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9:3)
不知道康德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他的确注意到“幸福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幸福概念所包含的因素全部都是经验的,它们必须从经验借来……幸福并不是个理性观念,而是想象的产物”,但是,在他看到了幸福的主观色彩之后,就转而寻找一种客观的普遍规则去了。而不确定的、饱含主观色彩的“幸福”,与“利益”会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