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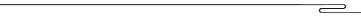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种种难题似乎不得不使我们期待神祇,因为若不引入神祇的话,我们对正义的寻求也许永远禁不起刨根究底的追究。不过,对神祇的引入也许并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会使问题变得简单——我们首先就会回到那个“自由意志”的两难的处境。
汉献帝建安四年,武陵郡有一位叫作李娥的妇人在60岁那年因病亡故,被葬在了城外。14天之后,李娥的邻居有个叫蔡仲的,偷偷挖开了李娥的坟墓,想要盗窃陪葬的财宝。蔡仲用斧头去劈李娥的棺材,突然听见李娥在棺材里边对自己说话:“蔡仲,小心别碰到我的头!”蔡仲惊慌失措,拔脚就跑,却偏偏被县吏看到。一番审讯之后,蔡仲供认不讳,按律当判死刑,并且陈尸示众。消息传开,李娥的儿子听说母亲死而复活,便从坟墓里接出了母亲,带她回家。
这个离奇的故事并非出自认真的史料,而是晋人干宝《搜神记》里的一篇。我们当然不必深究李娥的复活是真是假,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蔡仲的罪名——在古人的观念里,盗墓的确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对盗墓者判处死刑,乃至陈尸示众,这在古人看来确属罚当其罪,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故事还有下文。
武陵太守听说了李娥死而复活的消息,便召她来询问详情。李娥答道:“听说是司命召错了人,于是就要把我放还阳间。我在阴间正往回走着,不想遇到了姑表兄刘伯文,彼此不禁又惊又泣。我对他讲:‘我被错召到此,现在要被放还阳间,可我既不知道回去的路,又没力气一个人走,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同伴呢?再说从我被召来至今,已经十多天了,我的身体肯定已经被家里人下葬了,我就算回到阳间,又怎么出得了坟墓呢?’刘伯文便把我的苦处转达给了户曹,户曹回复说:‘现在武陵郡西边有个叫李黑的男人也该被放回去,可以叫他来做伴,再让李黑去找李娥的邻居蔡仲,让他去墓地把李娥挖出来。’就是这样,我才和李黑一起回到了阳间,还给刘伯文的儿子刘佗捎去了他父亲的一封信。”
武陵太守听罢事情的原委,感慨道:“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于是向中央政府呈递奏章,陈述本案始末,建议赦免蔡仲,因为他虽然有挖坟掘墓的事实,但确属鬼使神差,不是自己应该为此负责的。皇帝做了批复,认可了太守的意见。

故事叙述至此,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个疑问:假若武陵太守并不是一个太有好奇心的人,那么蔡仲一案就只有维持原判了,连蔡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如果说神祇的考虑从来都是周到的话,武陵太守必定会查清蔡仲的冤情,那么武陵太守的所作所为究竟又有几分是出于自由意志呢?
中国的传统神祇具有和古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一般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也许不足以承担为世间贯彻正义的使命,那么,若我们引入至善至公并且全能的上帝,总该可以了吧?
是的,即便在彻底的无神论者那里,看来也会认为有必要编织一种“高贵的谎言”,就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所说的:“即使上帝不存在,我们也需要创造一个上帝;即使你只统治一个村庄,它也需要上帝。”
然而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如果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连婴儿都是染有原罪的,那么我们所有人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很难和原罪脱离干系,但原罪理应归咎于亚当和夏娃,我们凭什么要为之负责呢?即便是最苛刻的社群主义者,想来也不会承认这种过于夸张的连带责任吧?
这是一种相当近乎人情的质疑,所以历史上总是会有神学家并不赞同为奥古斯丁所建立的原罪理论。所有的反面意见都可以归入两大派系,一是为了“善”而反对,一是为了“真”而反对。
康德就是前者的代表,他认为原罪理论势必削减人们的道德义务。康德的以下反驳颇有几分自由主义的精神:“无论人心中在道德上的恶的起源是什么性质,在关于恶通过我们族类的所有成员,以及在所有的繁衍活动中传播和延续的一切表象方式中,最不适当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恶设想为是通过遗传从我们的始祖传给我们的。因为关于道德上的恶,人们完全可以说诗人关于善所说的同样的话:族类、祖先,以及那些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我都不能把它们算作我们自己的。”

而在后者的代表里,奥古斯丁的著名论敌裴拉鸠斯是相当值得一提的。在他看来,人类始祖虽然滥用自由意志犯下了罪,但这罪“在事实上”并不具有遗传性,一个婴儿就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全新的开始,为了亚当和夏娃的罪而惩罚所有人类是不公正的,因而上帝不可能这样安排;那么,既然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瑕的、全新的,只要善用自由意志而行善去恶,当然就会获得拯救;人类的罪并不是被耶稣基督救赎了的,他只是为我们做出了善的榜样。
如果站在无神论的角度,我们会很轻松地把问题归之于“古代观念”——对于那些生活在公元前的古人来说,相信罪恶带有遗传性并不那么困难。荷马笔下的希腊世界就是这样,譬如显赫的庇勒普斯家族:
这个王朝的建立者,亚洲人坦达鲁斯,是以直接对于神祇的进攻而开始其事业的;有人说,他是以试图诱骗神祇们吃人肉,吃他自己的儿子庇勒普斯的肉而开始的。庇勒普斯在奇迹般地复活了之后,也向神祇们进攻。他那场对比萨王奥诺谟斯的有名的车赛,是靠了后者的御夫米尔特勒斯的帮助而获得胜利的。然后他又把他原来允许给以报酬的同盟者干掉,把他扔到海里去。于是诅咒便以希腊人所称为“阿特”(ate)的形式——如果实际上那不是完全不可抗拒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犯罪冲动——传给了他的儿子阿特鲁斯和泰斯提司。泰斯提司奸污了他的嫂子,并且因而便把家族的幸运,即有名的金毛羊,偷到了手中。阿特鲁斯反过来设法放逐了他的兄弟,而又在和解的借口之下召他回来,宴请他吃自己孩子的肉。这种诅咒又由阿特鲁斯遗传给他的儿子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由于杀了一只做牺牲的鹿而冒犯了阿耳忒弥斯;于是他牺牲自己的女儿伊芙琴尼亚来平息这位女神的盛怒,并得以使他的舰队安全到达特罗伊。阿伽门农又被他的不贞的妻子和她的情夫,即泰斯提司所留下来的一个儿子厄极斯特斯,谋杀了。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提斯又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厄极斯特斯,为他的父亲报了仇。

“阿特”(ate)显然就是一种具有原罪性质的遗传基因,中译者认为这是“指由天谴而招致的一种愚昧和对于是非善恶的模糊而言”。类似的观念在其他的文化传统里也不乏例证,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其中存在有任何的不妥之处,只是随着文明的演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才渐渐开始成为问题了。
所以,裴拉鸠斯对原罪的阐释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他的论敌奥古斯丁终于被尊为正统也不是什么不易理解的事情。今天我们还会面临这种时代观念上的“代沟”问题:沦为异端的裴拉鸠斯主义在今天看上去远比奥古斯丁的正统神学更加贴合我们一般人的朴素的道德情操,也是当代许多平信徒自然而然的信念所在;而奥古斯丁以自杀为喻,认为正如一个业已自杀的人不可能自己去恢复生命,人既然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也就从此丧失了自由意志,要想获得拯救就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

在与裴拉鸠斯的论战当中,奥古斯丁走向了预定论,亦即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出于某种我们无法窥测的理由决定了哪些人将被拯救,哪些人将受永罚。这样看来,贩卖赎罪券——罗马教廷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桩丑闻——反而很有一些积极意义,因为它鼓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宣扬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善行(即购买赎罪券)进入天堂。
如果我们固守文本的话,那么《新约》似乎确实有着预定论的倾向,强调恩典而非善功。在《马太福音》第20章里,耶稣做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主人请工人来干活,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但就在这一天里,他陆续请了好几批工人,越是后来的工人显然工作时间就越短,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位葡萄园主人却付给了每个人同样的工价:一个银币。先来的工人当然不满,但葡萄园主人理直气壮地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我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改革宗的《研读版圣经》对这段故事如此诠释道:“要得到神手中一切美善的东西,只能倚靠神的恩典。”
 这就像被误传为仓央嘉措的那首《见或不见》所谓的“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神并不会因为你多做善功或更加虔敬而给你更多一分的恩典。
这就像被误传为仓央嘉措的那首《见或不见》所谓的“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神并不会因为你多做善功或更加虔敬而给你更多一分的恩典。
预定论后来得到了马丁·路德与加尔文这两支新教大宗的宣扬,路德甚至提出,一个人是否相信上帝,连这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如果说这种论调不太招人喜欢,这应该是很可理解的。于是,路德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反复论战成为16世纪20年代欧洲世界的一大思想景观。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出于今天的朴素的世俗伦理,会很自然地站在路德的对立面上,甚至今日路德宗(即狭义的基督教)的平信徒也很难接受路德的“祖训”。但是,自由意志论之所以被定为异端,因为深究下去的话,上帝的全能就会受到质疑。因为,如果上帝的至公当真意味着他对世人的善恶可以精确地把握,并且精确地给以等值的回报的话,那么上帝就一定是完全依据理性行事的。这也就意味着,上帝的心思和行为是可以被人们以理性去预测的。即便我们不可能十分准确地预测,至少可以知道,只要我们行善,上帝就会奖励我们,只要我们作恶,上帝就会惩罚我们。如果上帝是可以被理性预测的,那么他就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至少是被理性限制住的。《西敏斯特信仰宣言》这样讲道:
3.5,人类中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神在创立世界根基以前,按照他永恒不变的目的,并他旨意所出的隐秘筹谋和良好关怀,已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永远的荣耀。这完全出于神无偿的恩典与仁爱,而并非是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或善行,或他们致力坚守两者其中之一;也不是受造物本身有什么条件或原因推动神拣选他。这一切都是为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颂。

7.1,神与受造物相隔实在太遥远,虽然有理性的受造物必须服从神——他们的创造主,但他们永不能从他身上获取好处,得到幸福和报偿,除非神主动纡尊降贵,用订定盟约的方法,来建立神人关系。

这似乎是西方神学与中国宗教理论的一大不同。尽管也感慨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诗经·大雅·抑》),不知道神祇究竟何时降临,不过在中国信仰传统的最高追求里,从来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基督教神学却极其在意理论上的逻辑一贯性,求真的精神不曾被实用主义彻底压倒。当然,实情也更有可能是:无关地域的分野,这是宗教领域里的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所必然会形成的区别。
上帝既然不可以受限于理性,所作所为就必须带有任意性才行。也就是说,一个人或者可能积德行善而受罚,或者可能无缘无故而受赏,上帝的旨意完全是不可揣摩的,给人的永生与永罚完全取决于他的“不测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