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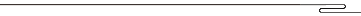
杀人如此,自杀亦然。涂尔干在《自杀论》里分析不同的社会背景对自杀者的影响,以统计数据说明,在有着极接近之文化背景的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社会里,新教徒的自杀比例最高,而后依次是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
涂尔干的分析是:“宗教之所以使人避免自杀的欲望,不是因为宗教的某些特殊的理由劝告他重视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也就越是具有预防的功效。信条和宗教仪式的细节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信条和仪式可以维持一种具有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因为新教教会不像其他教会那样稳定,所以对自杀不能起同样的节制作用。”

也就是说,集体生活的组织化程度对个体的自杀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那么,假定我们可以将同一个人复制成从身体到思想都完全相等的几个人,将他们分别放置在涂尔干所统计过的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那么我们就可以粗略预测出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的自杀概率。
那么,在其中当真有人自杀之后,我们在评定自杀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杀行为负责的时候,是否有必要把相应的概率计算在内呢?若是换到以自杀为风尚的社会环境,我们又该如何评定呢?——这些问题并非向壁虚构,至少古罗马社会就存在着这种风气,所以孟德斯鸠说:“在罗马人,自杀这个行动是教育的结果,同他们的方式和习俗有关系。”

又如作为文明人的我们抓住了古印度那个杀人越货的帮会当中某个成员,他杀了我们当中的一员,如果仅仅出于寻求公正的目的而处置他,他又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杀人越货的行为负责呢?养成杀人越货的癖好,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错呢,我们又该不该为了那些不属于他自己的错而惩罚他呢?如果主要应该为之负责的是那个帮会的全体(是整个帮会养育并塑造了他),那么在我们寻求公正的时候,是否应该向该帮会的所有成员复仇呢,尽管该帮会的其他成员丝毫不曾侵犯到我们?这样看来,“株连”反而比“罪止及己身”更加符合公平原则。
但是,株连的限度应该保持在哪里呢?这当然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一旦株连该帮会的所有成员,随即便会对每一名成员分别追溯其之所以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基因上的还是共同体文化传统上的,譬如生性暴虐的父母或从小接受的教育,然后再一代人一代人地追溯下去。
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该以同样的理由检查一下我们那个被杀的同伴,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无辜呢?是的,帮会为了抢夺他的财物而杀了他,但他的那些财物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就使得在我们讨论株连的合理性之前,这位看似全然无辜的受害者首先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检讨一下自己—可资借鉴的是西班牙剧作家何塞·埃切加赖的名剧《是疯狂还是圣举》(1877),剧中描写一位饱读诗书的可敬男子在意外得知自己并非已故父母的亲生儿子之后,毅然放弃了丰厚的遗产,他认为自己倘若不这样做的话,便无异于巧取豪夺的盗贼。于是,正如埃切加赖在剧名上所标举的问题:主人公的这一举措究竟是疯狂还是圣举呢?
好的,假如我们和那位受害者都看过了埃切加赖的这部戏剧,并且我们已经确认,受害者被匪徒劫掠的那些财物完全是他作为一名白领职员的合法收入,至于他本人,更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好人。但是,他所就职的公司在一个世纪前刚刚创立的时候,是因为大量使用童工才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同行挤垮,而确认他的收入“合法”的这个国家是靠着一连串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为才巩固了今天的局面,并且对那个古印度帮派野蛮的生存状况负有直接责任……
当然,古代施行株连政策的统治者们一般不是出于对公平的尊重,况且如此苛刻的公平条件也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情形而已。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准备攻伐纣王,誓师以声讨纣王的罪过,说他“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即无论判罪还是授官,都搞亲属扩大化。

这段誓师之辞即《尚书·周书·泰誓》,属于《古文尚书》。清代经学名家阎若璩考订《古文尚书》之伪,对于“罪人以族,官人以世”这一节文字,声泪俱下地痛斥伪作者的“不仁”。因为在阎若璩看来,古时本来并没有族诛之刑,人殉亦晚至秦武公时方才出现,就连以暴虐著名的有苗氏也不过止于肉刑而已,族诛之刑是秦文公二十年才有的,而这也仅仅见于秦国一地,源自戎人之法,很久之后才被中原文化接受。《古文尚书》的伪作者应该是偶然见到《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增篡至《泰誓》文中,使后世嗜杀的帝王有了文献上的口实,也使读者以为族诛之刑远在三代之时就已经有了。

阎若璩的意见到了今天又成为争议的焦点,张岩提出反驳说:“其一,考古学家已经解决用殉之事始于何时。其二,商代末期暴政中使用重刑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使用。如果殷纣荒淫残暴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何来诸侯联军(周、庸、蜀、羌、茅、微、芦、彭、濮)的兴师问罪,何来姬发‘恭行天之罚’,乃至周革商命。”

在人殉的起始时间上,阎若璩确实说错了,但他的论点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因为在张岩的第二点反驳上,“荒淫残暴”和“兴师问罪”显然不存在必然联系,毕竟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退一步说,即便确证了纣王的荒淫残暴,但也无法确证“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就是“荒淫残暴”当中的一项,这只能形成或然性的结论。
张岩继而将《泰誓》“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与《荀子·君子》中“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一段与对比来看,认为“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后者袭用前者,由于记忆不准,略有改动,失其原义”。

武王既然声讨纣王“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的乱政,周人理当奉行相反的政治原则才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派公孙青去卫国聘问,卫灵公称道公孙青有礼。齐景公很高兴,便赐所有大夫饮酒,说公孙青之所以赢得这样的名誉,都是各位大夫教育得好。但苑何忌推辞道:“如果大家因为公孙青的受赏而受赏,自然也会因为公孙青的受罚而受罚。《康诰》说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更何况在臣子之间。臣下不敢因为贪图君王的赏赐而违背先王的话。”
看来苑何忌并不认为自己对公孙青教育有功,觉得因此而受赏太过牵强。我们不妨把苑何忌的话引申为现代的一种个人主义观点:我就是独立的我,请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我只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无论是享有荣誉还是承担罪名。事实上,周人就算较少地“罪人以族”,却一直在“官人以世”,因为世卿世禄的制度正是周人宗法封建的一大核心,苑何忌的发言应当是因为过于特殊才被记录在案的。
另一方面,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古往今来都相当罕见,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天然的心理定势——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群体里来认识自己的。尤其在积极的一面,一个从未对本民族做过任何贡献的人也会欣然享受民族自豪感。人,在纯粹的世俗意义上讲,的确如马克思所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该不该,又该在何种程度上,为人的善恶承担责任呢?
那么,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该不该,又该在何种程度上,为人的善恶承担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