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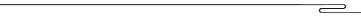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公平原则,或“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原则,存在一个难于确定的问题,即如何确定“等值”。在正义女神的天平上,寻求正义的一方该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多大的砝码才可以恢复天平的平衡呢?
试想有一个极度厌世的抑郁症患者谋杀了一个朝气蓬勃、热爱生命、前途无限光明的大好青年,那么,对杀人者的处决当真遵循了等值原则吗?正义女神手里的天平会不会不但没有平衡,反而倾斜得更严重了呢?就杀人凶手的个人感受而言,能够被处以死刑不仅算不上惩罚,简直就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福利。
也许这个杀人凶手本人也是一名受害者,甚至他才是这场不为人察知的阴谋中唯一被针对的目标。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老谋深算的杀人狂想要满足自己的杀人癖好,但他既不想被人寻仇,也不想被法律制裁,甚至不愿意接受旁人的道德谴责,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一对天生抑郁的男女,促成了他们的和谐而绝不美满的婚姻,看着他们生下孩子,看着这孩子不但继承了父母的抑郁基因,还整日被养育在挥之不去的忧伤气氛里。然后,杀人狂处心积虑地营造着这个孩子的生活环境,安排他住在最邪恶的街区,在一所地狱一般的学校里读一些比地狱更阴郁的书,灌输他悲观主义的信仰,激发他对乐观人士的仇恨与嫉妒……没有太大的悬念,这孩子长大之后,就成了那起凶杀案里的凶手,然后被捕,被判决,被处死。
的确,即便一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这孩子并不“必然”变成一个厌世的杀人凶手,但其或然性“必然”远远大于生长在阳光下的同龄人。那么,他为自己的谋杀行为所需要付出的“等值”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个例证的荒诞,然而事实上,这个看似极端的故事并不是完全向壁虚构的。1948年5月的一期《纽约邮报》刊载了一篇新闻稿,题为《男孩凶手早在他出生前就命该如此》,描述的是“一个12岁的男孩怎样因谋杀了一个女孩而被判入狱,以及他的父母的背景,包括酗酒的记录、离异、社会失调和局部麻痹症”。约翰·霍斯泊斯在《自由意志和精神分析》(1950)里提到了这个例子,进而问道:“我们还能说他的行为——尽管是自愿的,也确实不是在枪的胁迫下所做的——是自由的吗?这个男孩很早就表现出行为残忍的倾向,以此来掩盖他潜在的受虐心理,以及以此来‘证明他是一个男人’;他母亲的溺爱只会使这种倾向恶化,直到他杀了那个他所爱慕却冷落了他的女孩——不是仅仅在盛怒之下,而是有谋算地、深思熟虑地谋杀她。他的犯罪行为,或就那点而论,他生命中的大部分行为是自由的吗?”

霍斯泊斯继而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答这个颇为棘手的伦理问题——尽管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很不牢靠的道路,但霍斯泊斯的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还会把我们引入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领域,即人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一般取决于回答者的社会地位,权贵和富人喜欢“有付出就有回报”“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论调,穷人如果还不曾被话语权的垄断者们彻底蛊惑的话,往往会对权贵和富人们的侵略性姿态感到刻骨的仇恨和深沉的无奈。
事情总有例外,19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虽然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但也语重心长地劝告工人兄弟们:“我们很愿意认为,罪恶不是由任何一个个别的人和任何一个阶级产生的。我们很愿意承认,对于一个由于他无力判断的情况而偶然处于压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怀有一点点的敌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是,有哪一个压迫者不是“由于他无力判断的情况而偶然处于压迫者地位”的呢?一个人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成分绝对不属于“命运的安排”?
让我们再看看事情的另外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曾经流行过一种“矫治哲学”(philosophy of rehabilitation),它在相当程度上被贯彻到司法实践当中。持这一信念的人一般都会把人的罪恶主要看作身心缺陷或对社会的适应不良的结果,所以,我们对罪恶要做的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育,这才是监狱的最恰如其分的职能。
“劳动改造”就是矫治哲学的一种实践形式,至少在理论上或意图上是要通过劳动提高罪犯的思想觉悟。那么,教育和惩罚,哪种方式才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几大核心问题之一: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斯宾诺莎在他的名著《伦理学》里论证过一项经典命题:“在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灵之有这个意愿或那个意愿乃是被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同样为别的原因所决定,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苛刻一点来看,如果这一命题成立的话,该书题目所标明的“伦理学”也就无法成立了。
——苛刻一点来看,如果这一命题成立的话,该书题目所标明的“伦理学”也就无法成立了。
是的,我们之所以认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出于对自由意志的认同。
 对一个我所仇恨的人,而我又有着杀他的能力,那么我既可以杀他,也可以不杀,到底怎么做,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既然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就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但是,站在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人似乎是基因和环境的产物,那么我们真的拥有我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吗?假令我们没有,或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自由意志,又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所有的正义、公平、道德、伦理,又该在哪里找到自己立足的依据呢?
对一个我所仇恨的人,而我又有着杀他的能力,那么我既可以杀他,也可以不杀,到底怎么做,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既然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就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但是,站在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人似乎是基因和环境的产物,那么我们真的拥有我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吗?假令我们没有,或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自由意志,又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所有的正义、公平、道德、伦理,又该在哪里找到自己立足的依据呢?
有一句名言一直被归在古希腊哲学家留基波的名下:“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万物都是有理由的,并且都是必然的。”即便这句话的出处不那么可靠,但至少留基波的弟子,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者,坚信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依据自然律,沿着固定的轨道滚滚向前。从那至今的两千多年,西方哲人们对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争论始终纠结不定。
中国哲人在这方面关注得少些,但也不乏卓越的洞见,譬如《庄子》有两则耐人寻味的“罔两问景”的故事: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内篇·齐物论》)
众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庄子·杂篇·寓言》)
故事的大意是说,影子的影子问影子:“你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束发,一会儿披发,你怎么就没有个主心骨呢?”影子回答说:“我是因为有待才会这样的吧,我所待的东西也有它自己的所待,有光的时候我就出现,没光的时候我就消隐。我是谁的影子就跟着谁一起活动,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的缘起法。与庄子同为轴心时代的名人,释迦牟尼所悟出的道理,亦即使佛教区别于当时印度各大教派的核心理论,就是这个缘起法。简言之,就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就是因果律,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万事万物都陷在这个因果的链条里挣脱不出。所谓陷在因果律里,也就意味着人生是不由自主的,是受所谓“业力”主宰的。不由自主而想自主,陷在因果律里而想跳出因果律,受制于业力而想摆脱业力的束缚,这才有了真如实相、寂静涅槃等理论。
庄子虽然没有用论说的形式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却以寓言的手法把它形象地表达出来了。如果以逻辑推理的形式表述,其最精当者恐怕莫过于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1770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自然的体系》一书中的论断:“在一切都是彼此连结着的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决不存在的;而且,在物理世界中,一如在道德世界中,所有一切都是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本质而活动的种种可见的或隐蔽的原因的必然结果。在人里面,自由则只不过是包含在人自身之内的必然。”

因果律必然导致宿命论——所以霍尔巴赫继而讨论的恰恰就是宿命论的问题——而宿命论该如何与自由意志相协调呢?这也就说是,因果律该如何与自由意志相协调呢?
的确,要解决自由意志的问题,就必然绕不开因果律。因果律的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神学上都是一个经典的两难问题,不承认因果律当然会很麻烦,但承认了因果律一样会很麻烦。
首先是第一因的问题:有没有第一因,第一因是什么,没法解决;其次是承认了因果律就等于承认了宿命论,也就等于否定了自由意志,否定了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该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负责;但承认自由意志的话,就有把人置于上帝之上的嫌疑。——这是哲学与神学史上纠结甚久的一大经典难题,相关论述俯拾皆是,譬如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和裴拉鸠斯的论战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论战的结果是:主张人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做出道德决定的裴拉鸠斯被判为异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此失去了上天堂、得永生的资格。
饶有趣味的是,这场论战如果放在今天,许多基督徒一定会站在裴拉鸠斯的一边反对奥古斯丁,殊不知“预定论”是神学里源远流长的一套理论。2008年环球圣经公会出版的《研读版圣经》面对这个看似两难的问题,谈到“改革宗神学家在处理这个课题时,通常会把人的自由行为、人的道德自由意志和绝对自由做出区分”。但无论如何,道德的处境看上去总归不那么豁然明白:
道德自由意志就是当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有能力做出任何可能的道德选择。自第二世纪后,无数基督教神学家(例: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都主张堕落了的人类拥有这么一种意志。他们否定人类是受制于堕落了的道德境况,相反,却坚持堕落了的人类有能力随己意做出任何选择,包括凭自己的力量和意志选择顺服或信靠福音。这样的观点完全违背圣经。奥古斯丁及其后的改革宗神学家均准确断言,尽管人类在堕落之前拥有道德自由意志,原罪却使我们失去它。

这一观念在《圣经》当中的确有着明确的渊源,譬如《新约·罗马书》9:20圣保罗的一段教诲:“被塑造的怎可对塑造它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泥造一个用途尊贵的器皿,又另造一个用途卑贱的器皿吗?”
倘若严守《圣经》文本的话,我们可以确定,上帝至少没有赋予人类“完全的”自由意志。例证比比皆是,譬如摩西带领同胞们走向应许之地的路上,需要经过希实本王西宏的地界,摩西派遣使者好言求告,虽然答应摩西的请求看上去对西宏的利益不会有任何损害,但西宏执意不允,以至于事情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读者或许会责备西宏的不智,然而责任并不在—至少并不完全在——西宏身上,拒绝向以色列人借路并非出自他的自由意志。
“但希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申命记》2:30)肉眼凡胎之人可能看不出上帝在这一事件中的巧妙作为,误以为是西宏自己“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但摩西知道真相,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申命记》2:33-35)
这一模式在《旧约》当中不断重演,以至于益发使人怀疑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新约·路加福音》23:34)西宏的所作所为当然是自己“不晓得”,迫害耶稣之人的所作所为也属于自己“不晓得”,那么,究竟哪些人的作恶才是自己晓得的呢?罗素问过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你所爱的人们遭的不幸又当如何对待呢?试想一想欧洲或中国的居民在现时期往往会遇到的一些事。假定你是犹太人,你的家族被屠杀了。假定你是个反纳粹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抓不着你,你的妻子被枪毙了。假定你的丈夫为了某种纯属虚构的罪,被解送到北极地方强迫劳动,在残酷虐待和饥饿下死掉了。假定你的女儿被敌兵强奸过后又弄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保持哲学的平静吗?
如果你信奉基督的教训,你会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曾经认识一些教友派信徒,他们真可能深切、由衷地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讲得出来,我对他们很钦佩。

试想一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如果晓得了神意和宇宙的规律,晓得了天堂和地狱,那么只要他们没有彻底丧失理智,就没理由再做下任何恶事了。全能的上帝当然也有能力把任何人教育明白,而如果“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上帝也确实有理由赦免他们。按照中国儒家的说法,正是“不教而诛谓之虐”。
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西宏到底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置才算得上公正呢?
无论如何,在西宏故事的基础上,圣保罗经典的“器皿说”就是呼之欲出的了。这一基本神学教义经过奥古斯丁的发展,后来又被路德和加尔文带进了新教各派。恰巧庄子也做过同样的比喻——奄奄一息的子来豁达地说:“譬如一位铁匠正在打铁,铁块突然从炉子里跳出来,要求铁匠一定把自己铸造成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那么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之铁。人也是一样,偶然得了人形,就喊着‘我是人!我是人!’造物主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的。现在我就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大铁匠,随他把我变成什么样吧。”

庄子的铁匠在东方并没有像圣保罗的窑匠在西方那样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和影响,但庄子对“有待”的分析,很容易让人想起圣保罗那个窑匠的比喻,我们生而为人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通往天国的门票到底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引下自己争取来的,还是被上帝预先分配好的?神学界硝烟未定,哲学界又有莱布尼茨和柏格森继续对垒,直到20世纪70年代,J.F.里奇拉克仍然就这个问题撰述专书“力图澄清事实”,但对其结论,我们也只能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