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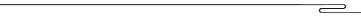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这种事情甚至还可以举出当代的例子,迈克·桑德尔就举过一个基于“自愿”的人吃人的案例:事情发生在2001年的德国,阿尔闵·梅维斯,一名42岁的电脑技师,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则征求自愿者的广告,希望那些想要被杀并被吃掉的人能和自己联系。大约有200人回复了梅维斯的广告,有4个人亲自找过梅维斯面谈,最后的“幸运儿”是伯恩德-约尔金·布兰德斯,一名43岁的软件工程师。布兰德斯和梅维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敲定了具体事宜,布兰德斯提供自己的生命和血肉,而梅维斯所能提供的东西除了这种匪夷所思的体验之外就再无其他了,尤其没有任何的金钱补偿。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绝对称不上一笔合适的交易,但是,布兰德斯接受了。
随后,梅维斯果然杀了他的这位客人,分割他的尸体,分装在塑料袋里放进了冰箱。直到被捕的那天,梅维斯已经吃掉了布兰德斯身上的超过40磅肉,主要是用橄榄油和大蒜烹调加工的。

桑德尔援引这一案例质疑自由主义的道德信条:两个成年人自愿缔结契约,互相也不存在任何欺骗,处置的是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那么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这种行为是没理由被禁止的,德国政府更不该对梅维斯判刑。
对梅维斯的判刑在社群主义的语境下倒是更容易讲通的,虽然这个案例看上去和海尔默斯所记述的巴厘岛人殉事件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一处关键的差异是:巴厘岛的人殉是被整个社会——无论观众还是死者——所欣然接受的,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社群文化的,梅维斯事件却大大有违于自己所在的社群伦理。从这层意义上说,梅维斯之所以必须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要对具体的那个被吃掉的人负责,而是因为他“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但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吗?这理由的背后实在是一种强权的逻辑:我们是多数,梅维斯是少数,仅此而已。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置身于海尔默斯所在的巴厘岛上,眼睁睁看着三位美丽而无辜的女子即将纵身火海,我们完全出于高尚的情操以及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挺身而出,施加“援手”,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否也深深伤害了所有巴厘人的感情呢,而他们又该以怎样的手段处置我们这些僭妄的渎神者呢?
当然,我们认为应当给人的生命以最大限度的尊重,我们会响应康德的主张,相信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但这只是“我们的”共识,我们之所以如此尊重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永生(即便许多名义上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否则我们很可能就会带有一些古老的达西亚部族的习气——这是图拉真治下的罗马帝国所遇到过的一个极其令人生畏的对手,“除了一般野蛮人所有的强悍和凶恶之外,他们更有一种厌恶生命的情绪,这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之说”。

这正是普世性伦理之所以难以成立的一大症结,只要人们对生命的本质存在歧见,只要今生与永生无法调和,那么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也好,无论是康德的定言令式或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也好,无论是功利主义的权衡计算或自由主义的行为通则也好,任何规则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除了无可奈何地接受那种令人生厌的道德相对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不妨以这个角度试探一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订立社会契约的初始状态,倘若参与者都是18世纪欧洲的正派的知识分子,罗尔斯似乎认为他们理应这样思考:“是的,在新世界里我也许会不幸‘投生’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可不希望因此而遭受迫害,所以我需要在契约里设计清楚,新世界不能歧视无神论者。”
但是,因为他们足够正直,所以他们更加合乎情理的思考方式应该是:“是的,在新世界里我也许会不幸‘投生’为一个无神论者,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啊!任何无神论者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唾弃,我不能因为自己有成为无神论者的可能而在这份社会契约里设计任何偏袒无神论者的条款。我是一位正派的绅士,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小人。”
中国的古典君子也会采取这种原则性的判断方式,依据孔子的教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如果畏惧在新世界里陷于“贫与贱”的处境而在“无知之幕”下动摇心中固有的道德原则,这还如何配称君子呢?
如果畏惧在新世界里陷于“贫与贱”的处境而在“无知之幕”下动摇心中固有的道德原则,这还如何配称君子呢?
即便出于对私利的考虑,对《圣经》怀有足够真诚的基督徒很可能会期待一个普遍贫困的世界,因为“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新约·马太福音》19:24,6:24),普遍的贫困至少可以消除自己在新世界变成富人的危险。这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在新世界里不幸生为一名富人,那么即便有幸听到福音,怕也很难割舍家业,而一贫如洗的人抛家舍业总会容易得多。甚至,他们不会希望在新世界里生为除基督徒之外的任何人,哪怕是专制君主或者富商大贾。同样地,对原始教义怀有足够真诚的佛教徒也很可能同样期待一个贫穷的世界,因为普遍的贫穷最有助于人们克制贪欲,而贪欲正是“三毒”之中最可怕的一项。

虔诚而刻板的基督徒甚至不会希望新世界里消除了奴役和压迫的现象,因为他们偏偏渴望充当受奴役、受压迫的角色,除此之外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欲的。一个由专制暴君统治的国度可能是非常理想的,因为所有人都要给这位暴君做牛做马,任凭生杀。虽然他们也有可能不幸在新世界里生为那位暴君本人,但在理性的人看来,如此小概率的事件实在不应该作为判断的依据。
更有甚者的是,如果让使徒时代的基督徒在无知之幕前与他人订立契约,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对于这些可敬的人士来说,殉道而死是人生最理想的目标,他们该设想怎样一种社会结构,以使自己无论成为这个世界当中的任何角色都会拥有较大的殉道机会?而满心世俗趣味的其他人,又会如何与他们达成妥协呢?
所以罗尔斯为无知之幕提出的一项预设是非常必要的,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大致相近。这在自然状态下是大致不谬的,却完全违背了“文明社会”的基本事实。
反驳者也许会说,罗尔斯还有一项预设,即协商契约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尽管不可能具备完全的理性,所以那些真诚的宗教信徒并不符合这项预设。——然而罗尔斯对自己所使用的“理性”概念是有过清晰界说的,简而言之,不过是对于不同偏好的合乎逻辑的权衡能力而已,除了一个例外(即“没有妒忌心”),完全符合社会理论对“理性”这一概念的通常理解。
 那么,依照这样的标准,让我们以一心殉道的基督徒为例,如果他们对殉道的追求并不是在某种特殊情境下突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在冷静的状态下经过审慎权衡之后欣然赴死,那么他们当然就是理性的。
那么,依照这样的标准,让我们以一心殉道的基督徒为例,如果他们对殉道的追求并不是在某种特殊情境下突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在冷静的状态下经过审慎权衡之后欣然赴死,那么他们当然就是理性的。
于是,凡此种种会很容易使我们倾向于沃尔泽的意见,追寻一种普遍的正义理论是不可能的,谁也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只要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吻合该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哲学论证来确立正义原则,而只有通过文化阐释。文化,我们知道,是永远摆不脱相对性的。
那么,按照沃尔泽的这个标准,我们看来可以认定巴厘岛虽然存在着令欧洲“文明社会”忍无可忍的人殉现象,但就其自身来说是完全合乎正义的。——这绝不是一个会令我们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的结论,就连沃尔泽本人也会感到踟蹰,所以他还提出了一个“弱的普遍准则”,认为存在着很少的一些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权利,是所有的社会都应该遵守的,譬如无论在任何社会,种族灭绝和奴隶制都是不正义的。

然而事实上,沃尔泽的这些“最低标准”恰恰使他落到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自己也不曾跳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是的,至少古代的雅典和斯巴达人不会接受他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也一定会起而与之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