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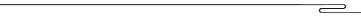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中国在汉朝初年曾经陷入一种“准自然状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时接秦之敝,诸侯并起,人民失去产业生计,饥荒流行,“人相食,死者过半”。于是刘邦下令,准许人民群众卖掉孩子,准许到蜀汉地区逃荒。可见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下,就连政府法令也对传统道德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自然状态”直到现代仍然是正义问题上的一个思考难点。1954年,英国作家戈尔丁出版了一篇寓言体小说《蝇王》,其情境设定是:一群男孩因为飞机失事深陷于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与获救。这样的设定似乎有意展开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但情节完全走向了相反的一面。最初,这群孩子推举了正派的拉尔夫作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理性的生活秩序,然而性格强悍的杰克以暴力和蒙昧拉拢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还发明了宗教仪式——他把飞行员的尸体误认为幽灵,便以猎杀来的野猪的头颅向这个“超自然力量”献祭。杰克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日益变得可怖起来,终于发展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杀人。他们发动叛乱,杀死了拉尔夫的助手,拉尔夫也在自卫当中杀死了杰克的人。人与人的厮杀就这样开始了,直到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发现了他们,把他们重新载回了“文明社会”。
戈尔丁的寓言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也许是的,但他至少在故事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一艘路过的英国军舰”。
在这部小说出版30年后,即1983年,戈尔丁发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为评论家们加诸自己身上的“悲观主义者”这个头衔进行辩解,辩词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内容:“我非常怀念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500多年前的挪威人朱莉安娜。她曾经被魔力控制,魔鬼将一颗胡桃大小的东西放在她的手心,告诉她这就是地球,还把地球上将会发生的千奇百怪的悲剧一并告诉了她。但在最后,她的耳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告诉她这些事都会过去,所有的生物都会安然无恙,地球上的一切都只会变得更好。”
这是一位步入晚年的伟大文学家的信念与希望,但是,让我们回到《蝇王》的故事:这个故事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并不是结尾处那艘终于来临的军舰,而是在军舰来临之前,在我们甚至并不确信最后会不会等来军舰的那段堪称“自然状态”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未来注定的“更好”并不会使过去的苦难变得云淡风轻——假如人们可以选择的话,至少有一些人宁愿从来不曾活过,也不愿去经受某些生活的苦难,而无论在这苦难之后会等来多大的幸福。
我们还有必要追问的是,在那艘军舰救出孩子们之后,当孩子们重新回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他们会如何反思自己曾一度陷入的野蛮与癫狂,又该如何、又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那段行为负责呢?这些问题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最单纯的表达形式:他们到底做错了吗?
在《蝇王》发表的5年之前,即1949年,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则假想的奇案,是说有五名探险者被困在一处山洞里,在水尽粮绝而又确知短时间内无法获救之后,一个叫威特莫尔的人提议抽签吃掉一个同伴以救活其余四人,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通过。但是,就在抽签之前,突然有人反悔了,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威特莫尔自己。他的反悔没能阻止先前的集体决议,其余四人还是把抽签进行了下去,而抽签的结果,那个“应该”被吃掉的人,天可怜见,恰恰又是威特莫尔。他们当真吃了他,而在获救之后,这四个人以杀人罪受到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富勒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分别体现了不同流派的法哲学思想。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构思,假想这一奇案在50年后再获审理,又有九位大法官各抒己见。
其中有一位福斯特法官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他的一项理由是:“当威特莫尔的生命被被告剥夺时,用19世纪作家的精巧语言来说,他们并非处在‘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自然状态’。这导致我们联邦颁布和确立的法律并不适用,他们只适用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我毫不犹豫地宣布,根据那些原则,他们不构成任何犯罪。”

福斯特法官所谓的“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就是所谓的自然律,即不存在法律与道德约束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规则,在这种自然规则下,人为了求生,杀人也好,吃人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事实上,在真正近乎自然状态的原始社会里——这是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最令人为难的问题是,当我们已经“文明化”了,有了“文明人”的道德与法律了,当生存环境由于某种原因突然退回到了自然状态,我们是应该坚守原有的道德,还是放弃这些,做一个道德上的自然人?
在这个选择之中,后者往往都不会令人愉快——试想当蛮族入侵,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秩序,使社会陷入一种自然状态,而你作为俘虏面临两种选择:被杀,或者投降并助纣为虐、屠杀同胞,你会怎么选择呢?福斯特法官又会怎么选择呢?
至于问题(3),如果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的、自愿的,吃人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呢?——在《资治通鉴》关于臧洪的记载里,有一处细节是不曾被王夫之提及的,即城中绝粮之后,臧洪知道守不住了,便对将吏士民发话道:“袁氏无道,图谋不轨,且不肯救援我的长官(张超)。我臧洪出于大义不得不死,但诸君与此事无关,不该受我的连累,不妨赶在城池陷落之前带着妻儿出城。”众人却都感于臧洪之义,不忍离去。这就意味着,臧洪并不能说“连累”了全城,大家都是求仁得仁罢了。
当然,全城的将吏士民都不顾自己与妻儿老小的性命而甘愿追随臧洪,这实在不近人情。但即便这段记载是有水分的,至少也说明了史官的价值倾向。只是,在臧洪杀妾的时候,那位爱妾是否也感于夫君之义而自愿献出生命和血肉,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当时,小妾的地位与其说更近于人,不如说更近于私有财产,她的意见被忽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这位小妾可不可吃,只需要得到臧洪的同意,并不需要得到小妾本人的同意。那么,王夫之所谴责的吃人之罪究竟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