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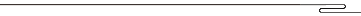
古罗马哲人阿波多罗斯承认自己在偶然的必要之时也吃人肉——他是在一本叫作《伦理学》的书里写下这个内容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吃人的伦理学家,他的书会受到读者怎样的对待。
历史性地来看,把吃人当作错事,这只是一时一地的道德观念罢了,是人类在“文明化”之后方才固定下来的一种认识,天真的野蛮人却并不都这么想。譬如阿兹特克人囿于见识,认为吃人是一项痛苦的义务,如果拒不承担这项义务的话,太阳就会失去光亮。
根据蒙田的未注出处的记载:“波斯国大流士一世问几个希腊人,给他们什么就可以使他们遵从印度人的习惯,把去世的父亲吃掉(这是印度人的习俗,认为把死人装进他们的腹中是最好的归宿),希腊人回答说,不管给什么,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大流士一世又试图劝说印度人放弃自己的做法,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把他们父亲的尸体火化,印度人的反应则更强烈。”

蒙田借此阐释习俗的力量,当然,吃人还有颇为现实的、功利性的理由。伏尔泰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在1725年,有人带了4个密西西比的野蛮人到枫丹白露来,我曾有幸同他们交谈过。其中有一个当地妇人,我问她是否吃过人,她很天真地回答说她吃过。我露出有点惊骇的样子,她却抱歉说与其让野兽吞噬已死的敌人,倒不如干脆把他吃了,这也是战胜者理所应得的。我们在阵地战或非阵地战中杀死我们邻邦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儿可怜的报酬去给乌鸦和大蛆预备食料,这才是丑行,这才是罪恶。至于敌人被杀后,由一个士兵吃了或是由一只乌鸦或一条狗吃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专门有“吃人的人”这样一个词条,所列举的事例之多令人不寒而栗,只是考虑到伏尔泰在引经据典方面一向缺乏足够的严谨,所以,这4名密西西比的野蛮人既是作者亲见,又有如此一种天真的口吻和乍看上去简直无懈可击的道理,所以尤其值得援引。他们既不是被严酷的生活逼到不得不吃人的地步,更没有表现出一点一滴的内疚感。
伏尔泰作为文明社会的精英人物,在吃人问题上和这几名密西西比的野蛮人看法一致。他在后文这样写道:
在克伦威尔时代,有一个都柏林的女蜡烛商出售用英吉利人脂肪做的上品蜡烛。过了些日子,他的一位主顾抱怨她的蜡烛不如以前那样好了,她就对他说:“先生,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英吉利人哪。”
我要问到底谁的罪过最大呢,是谋害英吉利人的那些人呢,还是这个用英吉利人身上的脂肪做蜡烛的贫妇呢?我还要问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是烹调一个英吉利人做晚餐吃呢,还是用英吉利人做蜡烛在用晚餐时照明呢?我以为罪大恶极的是人们杀害我们。至于在我们死后用我们做烤肉或做蜡烛倒无关紧要;一个正人君子对于死后还有用途并不觉得可恼。

看来伏尔泰应该能和墨子说到一起,而会被孔孟当作大敌。在推进理性以揭开启蒙时代的时候,理性已经走得过于极端,以致于不近人情了。任何一种思想主张如果想要深入人心,理性上是否圆融无碍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合乎人之常情。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吃人,乃至用人的脂肪做蜡烛什么的,比杀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在这个问题上,甚或在一切相关问题上,是情绪上的厌恶程度决定了道德的维度。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吃人逐渐被列为禁忌,人们对杀人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宽容。那么,吃人和杀人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呢?试想在一场反侵略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在绝粮的困境下面临两种选择:(1)饿死,随之而来的是亡国灭种;(2)吃掉俘虏来的侵略者,保存生命,继续与敌人作战。如果为了正义的目的可以杀掉敌人,或者摧残敌人的尸体以达到泄愤或威吓的作用,为什么就不可以吃掉敌人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一联脍炙人口的词句难道仅仅具有修辞上的感染力吗?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设计得更极端一些,把上述第二种选择中的“俘虏”换作“同伴”。那么,为了正义而吃人,无论吃掉的是敌人还是同伴,这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会有人质疑:一旦吃了人,原本正义的目标也就受到了玷污,甚至不再值得维护了。但这样的质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我们正在为“人吃人是错的”寻找理由,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又把“人吃人是错的”预设为前提。
吃人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例子可供辨析和思考。凯撒在围攻阿来西亚的战争中,被困的高卢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于是开会商量办法。据凯撒的记载,这些高卢人既有主张投降的,也有建议突围的,“但最最残忍得出奇、伤天害理到极点的,莫过于克里多耶得斯的一番话,颇值得一述”。这位克里多耶得斯先是以慷慨激昂的言辞唤起了大家的荣誉感,然后建议道:“我要求照我们的祖先跟钦布里人和条顿人战争时的样子做,虽然那次战争绝不足以和这次相比,但当时,他们在同等的饥饿压力之下,闭守在市镇里,就以那些年龄不适于作战的人的尸体维持生命,绝不向敌人投降。即使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先例,为了争取自由,给后世树立这样一个先例,我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件极端光荣的事情。”

不自由,毋宁死,也毋宁吃掉自己的未成年的同胞。这无论是在今天看来,还是在当时来自“文明世界”的凯撒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些野蛮而富于荣誉感的高卢战士,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到了万不得已的关头,也就只有采纳克里多耶得斯的这个建议了。
中国的一则吃人案例看上去要文明一些:在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张超固守的雍丘在曹操的围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了。张超对部下说:“臧洪会来救援我们的。”部下不解:“臧洪正在袁绍手下做事,袁绍和曹操却是盟友,臧洪怎么可能做出破坏袁曹联盟给自己惹祸的事呢?”张超答道:“臧洪是天下义士,不会背弃旧恩。我只担心他受到强大势力的控制而不能及时赶到。”
张超所谓的旧恩,是指自己当初对臧洪有过知遇之恩,是臧洪的旧主。张超所料不差,臧洪得知旧主被困,即刻向袁绍请兵,在被袁绍拒绝之后,臧洪又请求仅带自己所部兵马救援张超,但袁绍依旧不允。结果雍丘陷落,张超自杀,全族被灭。臧洪由此而痛恨袁绍,与之断绝往来,因此而招致袁绍大军的围攻。
臧洪守城守了一年有余,粮食已经吃尽,他便杀了爱妾给众将士吃。在无法抵抗的饥饿之下,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城池也终告失陷,臧洪被袁绍擒杀。
那么,臧洪到底是天下义士还是吃人狂魔呢?不少人是把他当作义士的,袁绍在擒获臧洪之后,决意杀他,臧洪的同乡陈容自幼便敬仰臧洪,其时恰恰在场,便向袁绍提出抗议,最后慷慨激昂地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袁绍连同陈容一并杀了,致使在座诸君无不叹息,私下议论道:“怎能在一天之内杀了两位烈士!”

东晋年间,刘裕讨伐司马休之,写密信给司马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要韩延之弃暗投明。韩延之在回信里痛斥刘裕对司马休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就算上天注定了灾祸不绝,自己也甘愿追随臧洪于九泉之下。刘裕收到回信之后,为之叹息,遍示将佐说:“做人家部属的就应该像韩延之这样。”

北周宣帝继位之后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带着棺材上朝谒见,面陈皇帝的八项过失。周宣帝大怒,要杀乐运,群臣无一人相救,只有元岩对人说:“连臧洪都有人甘愿陪他同日赴死,何况比干呢(元岩以比干喻乐运)。如果乐运被杀,我愿意陪他同死。”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王夫之就认为张超不过是像曹操、袁绍一样的人,臧洪之义不过是为了私恩。臧洪自己纵然可以为报私恩而奋不顾身,却奈何使全城的将士、百姓都为此而死。这只是任侠,称不上义举,吃人之罪更加不可饶恕。
王夫之把臧洪与张巡、朱粲相提并论,认为天下最不仁的事情未必不是始于道义的口实,在道义的大旗之下,人们便不再觉得残忍的行为有多么难以接受了。臧洪是出于任侠这么做的,张巡起而效法,出于尽忠也做了同样的事,后来又有朱粲这类人效法他们。每到末世凶年,在愚顽的百姓之中,人吃人的事情不断发生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吃人者连难过之情都没有了,把人看得和蛇、蛙无异,哪还有君臣道义呢?
我们不免会问:设若把王夫之换到臧洪、张巡的处境上,他会怎么做呢?想来他可能投降,至多会自杀,因为他这样说过:像张巡这样的情形,明明知道城守不住,自刎以殉城也就是了;而像臧洪这样的,就算暂时降了袁绍也不算是有辱名节。

以上这些议论又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1)如果整个社会风尚都赞同甚至崇尚某种吃人行为,那么吃人可不可以算作道德的?(2)在凶年末世,人类社会退化到自然状态,道德和法律是不是就不再、也不应该再具有约束力了?(3)如果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的、自愿的,吃人是不是就可以被接受呢?
问题(1)是一个针对社群主义的诘难,我将留待下文由沃尔泽提出的“弱的普遍原则”来做回答。至于问题(2),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譬如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在国际事务这种“自然状态”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弱国无外交”,道德或正义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诚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陈述的著名的国家理论,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第333节),所以国际纠纷只能、并且应当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黑格尔甚至认为战争还有一种“更崇高的目的”,即促进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第324节)。

黑格尔的论述是如此的义正词严,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感情上接受他的结论,当然有许多人在理性上也是这样相信的。那么我们以同样的逻辑试想一下,不是在国与国的“自然状态”下,而是在人与人的“自然状态”下,道理是否同样如此呢?